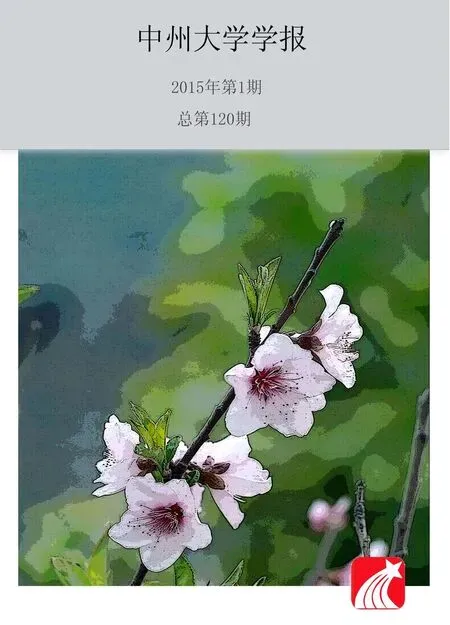法學中的“休謨問題”
——純粹法理論建構的邏輯起點
張世闖,鄭文革(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
法學中的“休謨問題”
——純粹法理論建構的邏輯起點
張世闖,鄭文革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
“休謨問題”自從提出之后,便被人們廣泛討論,對哲學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波及到法學之中。法學中的“休謨問題”所關注的是在實在法的正當性論證中,如何處理好事實和價值的關系。“休謨問題”指出事實和價值之間無法相互推導,自然法學和社會法學沒有考慮“休謨問題”,在實在法的正當性論證中,在事實與價值之間相互推論。凱爾森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避免事實與價值互推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在規范的領域論證法律的正當性,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不足,也遭受了許多的批評,但是這一有益的嘗試為法學的科學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休謨問題”;正當性;基礎規范
一、哲學中的“休謨問題”
在學問歷史的發展上,有時候提出問題比回答問題更重要,哲學上的“休謨問題”便是如此。“休謨問題”自從休謨在《人性論》中提出來之后,便為各位哲人所爭相趨鶩,試圖給出正確答案,但是至今也沒人能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①
1.因果關系問題
休謨在其《人性論》中用大量的篇幅對因果關系問題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我們的理性不能幫助我們發現原因和結果的最終聯系,而且即使在經驗給我們指出它們的恒常結合以后,我們也不能憑自己的理性使自己相信,我們為什么把那種經驗擴大到我們所曾觀察過的那些特殊事例之外。當我們知道了因果聯系、鎖鏈或功能只是存在于我們自身,只是因習慣而得來的那種心理的傾向,而且這種傾向只是使我們由一個對象推移到它的通常伴隨物,并由一個對象的印象推移到那個伴隨物的生動觀念,這個時候,我們該是怎樣的失望呢?”[1]105,293休謨認為,關系只存在于觀念之間,而實際的事實則無關緊要,任何“觀念的比較”都不能證明事實問題,而且事實之間的關系也從來不是必然的,因此,因果之間所謂的必然聯系乃是一種虛構的觀念。[2]290-291這樣休謨把因果關系描述成人們在主觀上的一種思維習慣,對因果關系的必然性持一種懷疑論的態度,否定了通過歸納可以得出關于事物之間必然性因果聯系的可能性。
康德對“休謨問題”的描述是:“休謨是從惟一的一個形而上學概念,即因果連結概念出發,并由此推論出:理性在這一概念上完全是在欺騙自己,它錯把這一概念視為它自己的孩子,而實際上這一概念無非是想象力的私生子。想象力憑借經驗而受孕,把某些表象置于聯想規律之下,并把由此產生的主觀必然性,亦即習慣,硬說成是洞察到的客觀必然性。”[2]3金岳霖先生認為:“休謨的辦法使得心靈非常之被動,使得因果律成為在經驗積累中被動地產生的聯想、被動的習慣,經驗中的因果關系不是必然的。康德的辦法是把這個統一割裂開來,他首先把客觀的材料稱為不可知的物自體,其次又把客觀事物本來有的規律性和必然性歸于心靈,讓他們成為心靈之所固有。”[3]通過人的心靈在主觀上的先驗范疇演繹,使主觀的因果關系客觀化,從而達到“人為自然界立法”,讓客觀符合主觀,而非通常相反的做法,通過這樣一個類似“哥白尼革命式”的方法,康德宣布自己很好地解決了休謨的因果關系問題,重建了科學和理性的權威。
2.事實和價值的關系問題
對于因果關系問題,休謨意識到了,并且破費筆墨進行討論,最終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即因果關系只不過是人們主觀的一種習慣性思維而已。在《人性論》中,休謨其實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得到了后世學者的廣泛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特別是在倫理學領域,并且在法理學中也是一個經久不衰,見仁見智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但是休謨在《人性論》中只是簡單地提到了這一問題,休謨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卻沒有像對因果關系問題那樣給予十分詳細的論證和分析,僅僅是在論證道德學體系中,用一段話簡單地提到,其后也并未給出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不知是休謨對此不感興趣還是感覺這一問題根本無法回答。但是這一問題卻為后世的哲學、倫理學和法理學等領域學者廣泛討論,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和學派。
在《人性論》中,休謨寫道:“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作者在一個時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進行的,可是突然之間,我卻大吃一驚地發現,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等連系詞,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系起來的。這個變化雖是不知不覺的,卻是有極其重大的關系的。”[4]505-506其后的一些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如摩爾、斯蒂文森、黑爾等,進一步發展了休謨這一并不成熟的思想,稱為“休謨法則”或“休謨律”,即價值判斷無法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5]
休謨的因果關系問題,在哲學的認識論中研究的較多。在倫理學和法學等規范學科中,對于休謨的第二個問題,即事實與價值的問題,探討的較為深入,并且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學派和觀點。作為規范學科,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規范(如道德和法律)的正當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規范的內容和效力來源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事實與價值的關系討論。休謨鍘刀使得事實與價值之間相互推理的道路被切斷,揭示了之前理論研究中的“自然主義謬誤”②,這給后來的規范學科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挑戰,即要在重新理清事實與價值關系的基礎之上,重建本規范學科的正當性和體系。
二、法學中的“休謨問題”釋義
法律是一種規范,法學是一門研究規范的學科,法律的正當性問題是法學理論研究中不可繞過的一個問題,法學中的“休謨問題”所關注的是,在實在法的正當性論證上,如何處理好事實和價值的關系。
現代學界公認的西方法學流派可以大體分為三派,分別是自然法學派、社會法學派和分析實證法學派,三大學派對實在法的正當性論證各有其法。自然法學派認為,人類實在法的內容必須符合自然法,無論自然法表現為自然規律、神的意志、人的理性、道德正義準則等,否則實在法就沒有效力,因為自然法的正當性是不證自明的,實在法要想具有正當性,必須符合自然法。社會法學派認為,法律是從社會生活中來的,是對社會中已經存在的習慣等規范的描述或確認,社會生活本身就是法,實在法的內容只有反映了社會本來的“活法”(埃利希語)或“客觀法”(狄驥語),才是有效的,這樣實在法的效力和內容都是源于社會生活的,其正當性也只能去社會中去尋找。自然法學派所犯的錯誤是,從“應當如此”的不證自明的自然法直接推出了“實際上如此”的實在法,是典型的從“應當”到“是”的推理。社會法學派則正好相反,從社會生活實際是怎樣的就推出了法律這一社會規范應當是怎樣的,這也是典型的“自然主義謬誤”,即從“是”推出了“應當”,同樣是對休謨定律的違反。自休謨定律提出之后,之前一些理論研究的謬誤也漸漸被人們認識到,事實和價值之間具有無法跨越的鴻溝這一之前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漸漸進入人們的研究范圍,很多學者為此殫精竭慮也未能給出滿意的答復,但是至少他們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可謂使得法學在科學的道路上前進了重要的一步。在法學領域,凱爾森的純粹法學首先給出了自己的嘗試和努力,盡管這些努力未必能夠完全盡如人意。
三、作為規范體系的實在法
1.純粹法理論的淵源
凱爾森對于法學中的“休謨問題”的論述是從邏輯的角度進行的,得出的結論是事實層面的邏輯三段論并不適用于規范領域。凱爾森認為,事實領域的三段論成立的原因是,結論已經包含在大前提與小前提中。例如,“所有人都會死,蘇格拉底是人,蘇格拉底會死”,此三段論實際上是指:所有帶有“人”的屬性者,皆帶有“死”的屬性,蘇格拉底帶有“人”的屬性,所以蘇格拉底帶有“死”的屬性。然而,“所有為承諾者應履行其承諾,某甲為一承諾,某甲應履行其承諾”,這樣一個法律上的三段論,大前提與結論里的“應履行其承諾”并不是“所有為承諾者”或“某甲”的屬性。大前提(規范)與小前提(事實)并沒有包含結論。[6]255這也是康德所說的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區別,例如“紅花是紅的”這個判斷完全可以先驗地作出來,不須任何經驗的支撐,這其實只是把已經包含在“紅花”中的“紅”給“分析”出來而已,而并未在“紅花”上添加新的知識;可是,“一切發生的事都有原因”這一判斷卻不一樣,“一切發生的事”這個概念中并沒有包含“原因”的概念,它表達了比本來固有內容更多的新知識,它并非“先天分析判斷”,而是“先天綜合判斷”。[7]255如何才能使得“一切發生的事都有原因”這一綜合判斷成立,康德通過純粹知性范疇的“先驗演繹”解決了這一問題,即所謂“人為自然界立法”,這一方法重建了休謨的因果性問題,在第一部分已經論述過。
邏輯三段論僅適用于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事實的分析命題的情況,對于這種大前提是應然的綜合命題,并不適用,因為前提的屬性中并未包含結論。那么怎么解決這一問題,凱爾森借鑒了康德的方法,要使“某甲應履行其承諾”這一結論成立,則必須讓“履行承諾”變成“承諾者”的屬性,這從事實中是推斷不出來的,休謨鍘刀斷了這一條路,那么唯有在先驗的概念中做這么一種預設,即在思維中先天預設了“承諾者”這一概念就內在地包含了“履行承諾”的屬性,不然就不是“承諾者”,這樣的話,原來的三段論推理就可以成立了,“某甲是承諾者”,則“某甲”也具有“履行承諾”的屬性,則可以理所應當地推出“某甲應當履行承諾”了。這樣的方法正是凱爾森純粹法學效力準則的理論基礎,可以說純粹法學是以“休謨問題”為反思法學的開端,以康德的先驗方法為杠桿,對法學進行重構,力爭使其科學化。
凱爾森把規范作為一種特殊的領域,既不同于自然法學所謂的價值,也不同于社會法學所謂的社會事實,甚至不同于其他實證法學學者所說的規則。法律是規范的集合體,法學是對規范的研究,作為一個獨特的領域,規范相對于“應當”的價值,屬于“是”的范疇,相對于“是”的事實,則又屬于“應當”的范疇,所以規范從不同的層面看,具有“是”和“應當”的雙重屬性。“是”與“應當”的邏輯二元論意味著從前一陳述,即某事物應當是什么或者某事情應當被完成,推不出后一陳述,即某事物實際是什么或者某事情實際被完成,反之亦然。[8]休謨鍘刀切斷了事實和價值之間的聯系,作為“規范”的實在法的正當性既不能從純粹的“應當”的價值中得出,也不能從純粹的“是”的事實中得出,那么從哪里去尋找法律的正當性,即法律的正當性何在?
2.實在法效力的正當性解決
凱爾森認為,他的純粹法理論是一種實證法理論,與自然法理論存在根本的區別,因為自然法理論認為實在法的效力和內容都來自于自然法,否則便是無效的,但是他的基礎規范只關注實在法的效力,并不關注其內容。實在法的內容完全由人的意志行為所決定,由人的行為所構成,并由作為法律創造事實的憲法所創制。[9]凱爾森認為,規范的效力只能從自身尋找,一個規范效力的理由始終是一個規范,而不是一個事實,探求一個規范效力的理由并不導致回到現實去,而是導致回到由此可以引出第一個規范的另一個規范。[10]174-175這樣一直追溯便會追溯到一個最高位階的規范,即“基礎規范”,這是一個先驗概念預設,是整個規范體系的終極效力來源,也是認識法規范效力必不可少的先驗條件。[6]265
基礎規范是一個具有康德主義色彩的概念,這一概念類似康德在解決休謨因果關系問題時所采用的時間、空間、原因、結果等先天概念,是思維的先驗預設,基礎規范的效力也是被預設的,用凱爾森的話來說即是,我們所說的“效力”,意思就是指規范的特殊存在,或者說是,我們假定它對那些其行為由它所調整的人具有拘束力。[10]65從基礎規范中只能推演出實在法律規范的效力,基礎規范只具有形式的特征,其功能只在于建立法律規范間的動態委托原則。[11]82基礎規范使得法律的效力決定基本上可以脫離內容的因素,而單純由形式的因素來加以決定,毋須訴諸良知或其他正義理念等,并且坦然接受“惡法亦法”之命題,在面對各種指責時指出:惡法亦法,但并不包含服從義務,在這種觀點下,我們反而可以更清楚地指出現行有效的法律其內容為何,而不至于將其與我們個人的道德信念相混淆。這種見解就理論品質而言,甚至較諸拉德布魯赫公式更加嚴謹一貫,既可以解決惡法的服從問題,又不犧牲法律效力理論的一貫性。[6]267-271
某一法律秩序基礎規范的內容是由什么來決定的?凱爾森認為,基礎規范的內容取決于構成特定秩序的事實,也即該秩序在多大程度上為人所遵循。人們的實際行為僅須大體上符合秩序即可,而不必完全符合。凱爾森舉例說,如果革命成功,民眾便不再服從已經喪失實效的舊秩序,轉而遵守大體上具有實效的新秩序,但是假如革命者所建立的新秩序沒有發生實效,那么革命的行為就不是制憲而是反叛,不是造法行為而是違法行為。[12]85可見,基礎規范的內容即是賦予某一主體以立法權威,這一權威是法效力的終極源泉。論理上,對于基礎規范不能再議論它的妥當性,因此它必須被認為是一種“基本假設”。例如,英國的基本規范是國會主權,納粹德國的是領袖的命令,土人部落的是服從巫師。[13]180從某種程度上說,基礎規范是歷史事實的反映,是權力向法律的轉變。所以,在理論上,基礎規范是法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渡橋,在實踐中,它則是合意、民意和其他各種現實向法律轉變的關鍵節點。[14]在這個節點之前,法律處于胚胎形塑過程,價值與事實可以施加其影響,可是一旦過了這個節點,法律即宣布降生,由此進入了規范的領域,在此領域內,規范是完全獨立的,不受事實與價值的影響。
凱爾森以休謨定律為指引創造了區別于價值和事實的但又兼具二者特征的“規范”概念,又利用康德的先驗哲學的方法創造了基礎規范的概念,在動態上構造了效力上自洽的純粹法體系,比較好地解決了法律正當性問題之一的效力來源問題。
3.實在法內容的正當性探索
規范秩序因其基礎規范而有別,換言之,規范秩序可依其最高效力原則分為兩類。一類規范因其內容而有效,即其內容具有一目了然之效力品質,故此規范所涉之行為乃理所當然之義務。而該規范之內容所以為然,則由其可回溯至基礎規范,后者囊括秩序中一切規范之內容,正如一般涵蓋所有個別。道德規范即屬此類,一切道德規范皆可藉演繹方法自基礎規范中推導而得,道德之基礎規范具有實質性與靜態性。[12]81-82在凱爾森看來,法律是不同于道德的動態體系,其在《純粹法理論》第一版中從未討論過法律規范間在內容上的聯系,但其在《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靜態和動態成為了看待法律的兩種視角,不再將有無靜態關系視為區分法律與道德的標準,法律規范間是不是也像道德一樣存在內容上的聯系,其實完全取決于觀察的角度。[11]104-105這樣凱爾森把法律和道德的根本區別界定為規范的動態體系,也即這一動態的效力體系是專屬于法律的,而規范的靜態體系并非二者的區別,言下之意即是道德可以有這樣的靜態體系,法律的內容同樣也可以用這樣的靜態體系進行演繹。如此,法律就具有了兩個維度,一個動態維度對法律的效力問題進行處理,一個靜態的維度對法律的內容問題進行處理。
凱爾森認為,在靜態規范體系中,規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為它們的內容具有一種保證它們效力的直接明顯的特性,或者說,這些規范由于它們的固有魅力而有效力。[10]176凱爾森舉例說,“你應該愛你的鄰人”這一規范,可在某個更一般的規范中找到回答,比如人們必須“與宇宙和睦相處”的準則,如果那個規范是我們深信其效力的最一般的規范的話,我們就認為這個規范是最終的規范,然后人們就會獲得一個整個道德體系可以作為依據的規范,這樣一個體系的所有特殊規范,只能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推論,才能得到。[10]176-177
盡管凱爾森的法律結構理論仍以動態性為特征,卻始終受到靜態理論的誘惑。[11]105凱爾森對法律正當性的考慮由原來的效力一個維度逐漸轉向效力和內容兩個維度,凱爾森在其早年的純粹法理論體系中并未采用靜態體系的正當化理論,但是在他晚年的《規范的一般理論》一書中,否定了規范邏輯的可能性之后,原來依靠規范邏輯所建立的動態效力體系面臨著崩潰的趨勢,所以其思想又有了向內容傾斜的趨勢。
凱爾森的純粹法學的任務就是在認識到“休謨問題”的前提下如何尋求法的正當性的一次努力與嘗試,其基本思路是在不能相互推導的事實與價值兩個領域之外新建一個兼具二者特征的規范領域,然后借助康德的先驗哲學方法預設了一個有效的基礎規范,以基礎規范為整個法律體系最終的效力來源的動態法律理論,解決了實在法的效力來源問題。在實在法的內容正當性方面,凱爾森雖未主張法律也可如道德一般進行內容上的演繹,但是其后期理論有逐步加強對內容和靜態理論體系的關注,這為其理論后繼者更好地處理法律內容正當性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方向性指引。凱爾森其實并未很好地解決實在法的內容正當性問題,但是對于某些內容上不正當的法律,他是通過區分法律的效力與人們對法律的服從來進行解決的,也即是法律雖然具有效力,但并不是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要對其服從。這就是修正后的實證法學的觀點,“惡法亦法”,但是人們可以有不服從的權利。
當然,任何理論都不是完美無瑕的,凱爾森的基礎規范理論也遭受了很多的批評,甚至凱爾森本人在其晚年作品《規范的一般理論》中把基礎規范作為一種虛構,這是凱爾森對康德主義原則的完全放棄。虛構與假設不同,它并不具有先驗的自明性,虛構之所以被應用只是因為其“有用性”。[15]凱爾森后來甚至否定規范邏輯的存在,從而使得純粹法理論的基礎發生了動搖。[16]無論如何,純粹法理論還是在眾多的法學理論中獨樹一幟,尤其是其對“休謨問題”。
四、結語
自古以來對于法律正當性的論證不外乎兩條路徑,一是求諸自然法等先天事物,另一是求諸社會事實,自然法學家和社會法學家沉迷于此,并未意識到此路不通。這些理論之所以被當做普遍真理,常常被搬出來,主要是因為其具有修辭的效果——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語詞的暴力和征服性。[17]5它們不是從更高一級的“上帝”那里獲取“真理”,就是抱著“一切存在即合理”的信仰,不加論證而想當然奉之為圭臬,振振有辭而不自知或不愿自知,直到“休謨問題”提出并被應用到法學領域,這一迷夢才被打破。純粹法學的理論前提就是以存在和當為的絕對區分為基礎,探求實證法的規范科學。[13]178凱爾森為避免價值與事實之間的互推,創造了一個特殊的規范領域,并在規范領域內對實在法的效力與內容正當性分別進行論證,這一方法立足于法律自足性,使法律免受價值和事實的影響,盡管其理論仍然具有諸多缺陷,卻為法學的獨立和科學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注釋:
①這其中代表性解決方案有托馬斯·黎德的“先驗法”,康德的“先驗綜合判斷法”,羅素的“公設法”,卡爾納普的
“概率邏輯法”,萊辛巴赫的“實用法”等。具體參見:周曉亮.歸納:“休謨問題”和后人的解決[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7(6).
②倫理學家摩爾提出的概念,意指各種根據實然推論應然的不當推理。
[1][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上冊[M].關文云,譯.鄭之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2][美]喬治·薩拜因,托馬斯·索爾森.政治學說史:下卷[M].4版.鄧正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金岳霖.從休謨、康德到羅素[J].哲學研究,1988(7).
[4][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M].關文云,譯.鄭之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5]孫偉平.“休謨問題”及其意義[J].哲學研究,1997(8).
[6]顏厥安.法與實踐理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7]鄧曉芒.康德論因果性問題[J].浙江學刊,2003(2).
[8]Hans Kelsen.What is the Pure Theory of Law[J].Tulane Law Review,1960(34):269.
[9]Hans Kelsen.On the Basic Norm[J].California Law Review,1959,47(1):107-110.
[10][奧]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沈宗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1]張書友.凱爾森:純粹法理論[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
[12][奧]漢斯·凱爾森.純粹法理論[M].張書友,譯.北京:法制出版社,2008.
[13]林文雄.法實證主義[M].5版.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
[14]梁曉儉.試論凱爾森基礎規范的合理性[J].當代法學,2002(2).
[15]劉蘇.邏輯適用于規范嗎:凱爾森后期規范邏輯思想初探[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
[16]陳銳.規范邏輯是否可能:對凱爾森純粹法哲學基礎的反思[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2).
[17][美]理查德·A·波斯納.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劉成賀)
“Hume’s Problem”in Law——Based 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re Law Theory
ZHANG Shi-chuang,ZHENG Wen-ge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Hume’s problem”,which is widely discussed by people since it has been put forward,has a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n philosophy,and this influence has also spread to law.“Hume’s problem”in law focuses on how to deal the relationships of fact and value when we justify the validity and content of positive law.“Hume’s problem”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no mutual derivation between fact and value,the natural law theory and social law theory do not take“Hume’s problem”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validity and content of positive law,and infer between fact and value.Kelsen puts forward his theory of justifying law in the norm province,although his theory has all kinds of shortages,and undergoes lots of criticism,this helpful attempt mak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tification of law.
“Hume’s problem”;legitimacy;basic norms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1.008
D90-059
A
1008-3715(2015)01-0036-05
2014-12-13
張世闖(1987—),男,河南商水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律文化、法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