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超時空意義
李寅萍
(淄博市商務(wù)局,山東 淄博 255000)
《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超時空意義
李寅萍
(淄博市商務(wù)局,山東 淄博 255000)
本文通過分析索爾仁尼琴短篇小說《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的內(nèi)容和藝術(shù)特色,指出小說主人公形象和他所過的這一天深層的哲理內(nèi)涵,并試圖揭示這部作品的超時空意義。
舒霍夫;一天;超時空;時代
1962年11月,由著名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主編的著名文學(xué)期刊《新世界》雜志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1](以下簡稱《一天》)的短篇小說。小說的發(fā)表立即引起了讀者極大的關(guān)注和廣泛的爭論:這是第一部直接描寫蘇聯(lián)國內(nèi)集中營真實生活的文學(xué)作品!小說的發(fā)表突破了蘇聯(lián)國內(nèi)當(dāng)時的許多禁區(qū),在此之前,在這個審查制度十分嚴(yán)格的國家里,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敢涉足這個眾所周知的敏感問題!它的發(fā)表在讀者中所引起的極大興趣已不僅僅是獵奇的問題了,讀者從這部作品的發(fā)表本身看到了思想和政治領(lǐng)域里的某種新鮮的東西。小說的作者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真可謂是一夜成名,正如雜志的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所說:“一個嶄新獨特,并且完全成熟的巨匠走進(jìn)了我們的文壇。”正如其所言,8年后的1970年,索爾仁尼琴在瑞典領(lǐng)取了當(dāng)年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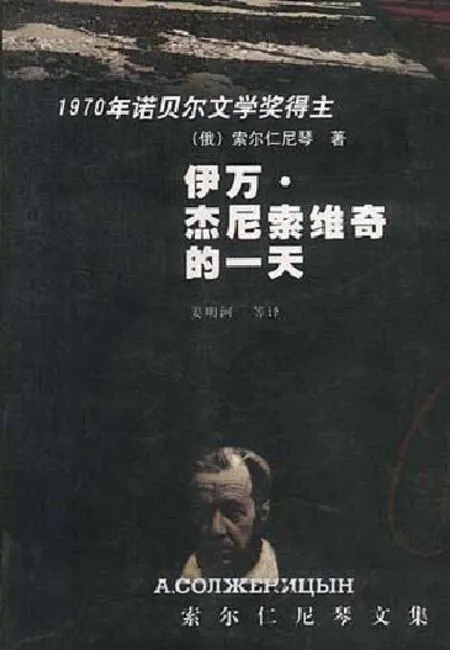
一
小說圍繞主人公舒霍夫在勞改營里從清早起床到夜晚點名整整一天的服役經(jīng)歷為主線,生動地展現(xiàn)了蘇聯(lián)時期國內(nèi)集中營生活的全景式畫面。舒霍夫是個勤勞樸實的普通農(nóng)民,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他離妻別子奔赴前線。在一次遭遇戰(zhàn)中被德軍俘虜,兩天后又僥幸逃了出來。結(jié)果逃出法西斯虎口的他們卻被“自己人”判為“法西斯間諜”。在反間諜機關(guān)里,備受酷刑折磨的舒霍夫被迫承認(rèn)了自己的“罪行”。因為他明白“不在口供上簽字,就只有死路一條;簽了字,也許還能再活幾天。”舒霍夫被判8年勞役,他在各個勞改營里輾轉(zhuǎn)顛沛,磨練了自己的意志,把自己“馴化”成一個溫順的,沒有任何奢望的“生命體”。
小說截取了了舒霍夫十年刑期中最普通的“一天”:當(dāng)早晨5點的起床號令 ——“鐵錘敲打著掛在勞改營指揮部旁邊的一截鋼軌”上- 費力地穿過“結(jié)有兩指厚冰層的窗玻璃”,若斷若續(xù)地傳進(jìn)營房時,舒霍夫的一天開始了。多年形成的按時起床的習(xí)慣與其說是自然養(yǎng)成,倒不如說是被環(huán)境所迫:起床晚了弄不好要關(guān)禁閉!然而,這天舒霍夫卻感覺有些不舒服,他多躺了一會兒,結(jié)果差點兒被關(guān)禁閉,最后幫看守打掃了衛(wèi)生才算了事。吃過飯,他還是去了醫(yī)務(wù)室碰碰運氣,想開一張病假條。可是他沒有那么好運,每天只允許開三張的病假條早被別人“捷足先開”了。
勞改營員們列隊去室外攝氏零下27度的嚴(yán)寒中干活,這已經(jīng)是司空見慣的平常事兒了:要知道,只有當(dāng)溫度計顯示出攝氏零下41度時,他們才不出工干活兒,可是這樣的天氣幾年也碰不上一次。在小隊長的巧妙周旋下,他們小隊最終沒有被派去修建“社會主義小城”——一項最艱苦的差使 —— 而是去砌磚墻。作為一個勤勞的普通農(nóng)民,舒霍夫能勝任各種工作,他在小隊中是一個出色的泥瓦匠。克服了種種不利條件的104小隊,在小隊長丘林的帶領(lǐng)下干得非常起勁:舒霍夫熟練地抹泥,碼磚,在凜冽地寒風(fēng)中,不一會兒就干得大汗淋漓了;干活兒上了癮的舒霍夫舍不得浪費最后一點兒灰漿,甚至在收工號吹響之后還在爭分奪秒地忙活,仿佛不是在服苦役,而是在自家的后院里蓋一座簡易小屋。在經(jīng)過冗長的反復(fù)清點人數(shù)之后,這支隊伍披星戴月地回到了營房。其間,舒霍夫巧妙地騙過了老看守的搜查,帶回來一小段鋸條,以便將來磨一把修鞋子用的小刀。舒霍夫沒吃晚飯就替同伴排隊領(lǐng)包裹,為的是多享用一份同伴的伙食,或者從他那兒得到些郵來的珍饈。晚飯后他還去了另一個營房,從另外一個營員那里買了兩杯心儀已久的煙葉。最后一次晚點名后,舒霍夫躺在自己的鋪位上,精心品嘗完同伴賜予的一小段香腸后,心滿意足地睡著了……
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過去了,他很滿意有這樣的一天,在這樣艱苦的環(huán)境中,處處都充滿了不可知的厄運和陷阱的勞改營中,能這樣平平安安、順順當(dāng)當(dāng)?shù)剡^去一天就是天大的幸福。
小說在最后寫道:“這一天他碰到了許多順心的事:沒有被關(guān)禁閉,他們小隊沒有被趕到‘社會主義小城’,午飯時還多得了一份粥,隊長把百分比算得很好,砌墻時很愉快,帶回來那截鋸條搜身時也沒被搜出來,晚上從采扎爾那里掙到點東西,還去買了煙葉。而且也沒有病倒,熬了過來。
一天過去了,沒遇到什么掃興的事,簡直可以說是幸福的了。
在他的刑期內(nèi),從頭到尾這樣的日子要有3653天。
二
據(jù)說,大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擔(dān)任《新世界》主編的時候喜歡以自己的方式給寄來的稿件更名。索爾仁尼琴對詩人這一嗜好很是不滿,他曾堅決反對將自己的《癌癥樓》更名為《病人和醫(yī)生》[3]。但我們不得不佩服特瓦爾多夫斯基對《854號勞改犯》[4]的這一更名,《一天》準(zhǔn)確地傳達(dá)出了作者想要表達(dá)的內(nèi)容,而且還有深化主題的妙用。“854號”是作者索爾仁尼琴在勞改營里的號碼,但是小說主人公舒霍夫的原型卻不是作者本人,據(jù)作者講,這個人物是融合了眾多形象的綜合體。他不是簡單的一個人,而是一個“群像”,至少他是作者本人和他曾指揮過的前線炮兵營的一名戰(zhàn)士的糅合。從這層意義上出發(fā),這“一個人”是有深有深刻內(nèi)涵的。
舒霍夫在小說中是一個具體的“個體形象”,正像上面提到的那樣,作者在塑造他時糅合了幾個現(xiàn)實人物的形象。從創(chuàng)作角度來看,他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個單獨的客體,而是一個“群像”,這個人物形象本身就是一個群體的“提煉物”;另外,從我們從他身上深深感受到他周圍營友的氣息,進(jìn)而延伸開去,他已經(jīng)不是小說中簡單的主人公了。這個普通的勞改分子其實是一個時代里一批群像的縮影。舒霍夫的話語權(quán)在這里發(fā)生了變化,他代表的正是蘇聯(lián)時期千百萬被鎮(zhèn)壓、被清洗的受害者。作者通過一個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農(nóng)民的不幸遭遇,展現(xiàn)給讀者的是舒霍夫背后更多的人。有關(guān)“大清洗”時期被鎮(zhèn)壓的對象,當(dāng)年的相關(guān)文件有如下的規(guī)定:“仍在繼續(xù)從事反對蘇維埃活動的前富農(nóng);反對黨的成員,如社會革命黨、達(dá)什納克黨、前白黨分子等;在監(jiān)獄、集中營、勞改營仍然從事積極反蘇活動的分子。”[5]擁有如此廣泛群眾基礎(chǔ)的被鎮(zhèn)壓分子,他們的代表性一定是可觀的。此外,“大清洗”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它應(yīng)該結(jié)束在1938年。然而這僅僅是個開始,那個年代以后清洗卻一直繼續(xù)了下去,各種鎮(zhèn)壓和迫害一直伴隨著蘇聯(lián)此后的各個時期,這也就有了后來舒霍夫們被投入集中營的情況。
我們采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就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小說中舒霍夫的單純個人的行為和話語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現(xiàn)實“話語”,針對于他的實際話語,我們發(fā)現(xiàn)他還有一系列的“潛對話”。這些潛對話隱含在舒霍夫的日常話語之間,構(gòu)成了一個潛對話場。恰恰是這個潛對話場才是作者真正要展現(xiàn)給讀者的主要內(nèi)容。
眾所周知,俄羅斯的苦役和勞役制由來已久,蘇聯(lián)時期國內(nèi)集中營的存在也是多年被回避的話題。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隨著蘇聯(lián)政府推行的“大清洗”逐步展開,蘇聯(lián)國內(nèi)集中營初露端倪,被鎮(zhèn)壓和遭到監(jiān)禁的人數(shù)不斷增加。至今有關(guān)“大清洗”時期受迫害的人數(shù)也沒有一個準(zhǔn)確的數(shù)字,有些說法是幾千萬,有些學(xué)者在經(jīng)過一番考據(jù)后得出了僅僅幾百萬的結(jié)論[6]。我們在此姑且不去考證受迫害者的準(zhǔn)確數(shù)字,只是強調(diào)這樣一個事實:在那個非常年代里,像舒霍夫這樣遭受冤屈而被迫服役的決不是個別現(xiàn)象。舒霍夫形象在此得到了升華,在這里他成了一個“符號”,一個象征,他是那個時代千百萬受害者的代表,成為他們的代言人。如此一來,我們通過舒霍夫這個個體,看到了一個群像;又通過這個群像,看到了一個非常制度下的特殊社會背景。
三
舒霍夫在集中營里所過的這么普普通通的一天,表面上看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這只不過是他十年刑期的三千六百五十分之一。然而,仔細(xì)琢磨一番,這一天可真不是“普通的一天”。
首先,這是舒霍夫十年刑期的一個寫照。作者選取了舒霍夫十年集中營生活中的普通一天,展現(xiàn)的卻是主人公十年如一日單調(diào)而重復(fù)的生活。在1995的采訪中,當(dāng)作者談到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動機時,他這樣說:“1950年的一個漫長的冬日,我一邊和同伴抬著擔(dān)架一邊想:該怎樣描寫我們整個的集中營生活呢?其實,只需要詳盡地描寫一個最普通的愛干活的家伙的一天就足夠了,這就能反映我們所有的生活。不需要注入任何的恐懼,也不需要這一天是什么特殊的,就是日常的,構(gòu)成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一天。”[7]這里充分表現(xiàn)了索爾仁尼琴高超的創(chuàng)作技巧,他恰恰抓住了舒霍夫這特殊的“一天”,把特殊的事物變成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從小處著眼,卻以小見大,以點蓋面,賦予了這一天豐富的內(nèi)涵。這不是純粹意義上的一天,而是作者把舒霍夫十年中的每一天綜合起來,加工提煉而成。這一天也可以說是他刑期中的任何一天,正如小說最后說的那樣:“在他的刑期內(nèi),從頭到尾這樣的日子要有3653天。”舒霍夫的每一天都是這樣度過的,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燈睡覺,他在集中營里的生活就這樣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地重復(fù)輪回,周而復(fù)始。這樣一來,我們很容易便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舒霍夫所過的這一天既是他十年刑期中的某一特定的“一天”,又是他三千六百五十三天里的任意“一天”,這“一天”成了舒霍夫十年刑期的一個縮影。
其次,這一天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用一天來展現(xiàn)整個時代,聽起來好像有點兒天方夜譚,但索爾仁尼琴的確這樣做了,而且也達(dá)到了他的初衷。我們知道,蘇聯(lián)時期從沙俄繼承下來的流放和苦役制度一直發(fā)揮著它獨特的作用,這也許是他們保存較完整的傳統(tǒng)之一。蘇俄政權(quán)建立起來之后,遂采取了一系列鞏固政權(quán)的措施,從最早的捷爾任斯基領(lǐng)導(dǎo)的“契卡”到后來的“克格勃”,他們一直致力于鎮(zhèn)壓所謂的“人民公敵”的活動,日益膨脹的肅反擴(kuò)大化最終演變成了1937年的大清洗。一時間全國各地的集中營真可謂是“雨后春筍”般冒出。里面大部分都是像舒霍夫這樣普通的蘇聯(lián)公民,他們被冠以種種滑稽可笑的罪名:“左”、右派,退化變質(zhì)分子,叛國投敵分子,“間諜”等,強行被執(zhí)行苦役流放,甚至是死刑。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人類社會的悲劇,更是對人性的摧殘和蹂躪。在阿格諾索夫主編的《20世紀(jì)俄羅斯文學(xué)》中還做了一個考據(jù)性的工作。他們“根據(jù)作家詳盡羅列的舒霍夫營友的服刑期限,可以推算出:第一任隊長庫茲明被捕于‘大轉(zhuǎn)折的’1929年,現(xiàn)任隊長安德烈·普羅科夫耶維奇·秋林于1933年入獄。”[8]從此可以大致估算出這個時代所持續(xù)的時間:它幾乎伴隨著蘇聯(lián)政權(quán)的整個歷史。
這樣看來,舒霍夫的“一天”的確不是普通的“一天”,這是濃縮了一個時代歷史的超時空一刻。在這個短暫的“一天”中,凝結(jié)了一個時代的歷史。這一天是短暫的,然而它卻比任何一天都長。
這樣從時空角度看,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就像是一滴露珠,透過它折射出一個廣闊的空間,歷史好像在這里凝結(jié)成了一時一刻,世界好像在這里濃縮成了一地一域。舒霍夫的一天是充實的一天,是濃縮了一個時代歷史的短暫一刻,也是一個時代的永恒存照。
歷史會記住這一天的,因為它是真實的。
[1]索爾仁尼琴,《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姜明河等譯,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年。以下引文均引自此版本。-作者注。
[2]《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142頁。
[3]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陳淑賢等譯, 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年,89頁。
[4]索爾仁尼琴投稿時這部小說的題目就是《854號勞改犯》,時任《新世界》主編的特瓦爾多夫斯基在刊登小說時擅自將小說改成現(xiàn)名。-作者注。
[5]參見吳恩遠(yuǎn)《蘇聯(lián)“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shù)考》,原載《史學(xué)研究》,2002年5期,104頁。
[6]最近的研究表明,以前的數(shù)字是有所夸大的。參見吳恩遠(yuǎn)《蘇聯(lián)“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shù)考》,載于《史學(xué)研究》,2002年第5期,102-112頁。
[7]《星》 1995年第11期。
[8]阿格諾索夫,《20世紀(jì)俄羅斯文學(xué)》,凌建侯等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517頁
I042
:A
:1671-864X(2015)10-00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