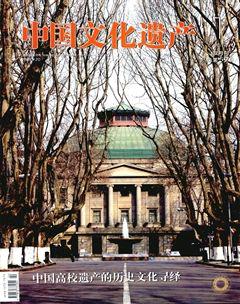匈牙利考古初印象
呂夢


飛機擦過低矮的云層,降落在布達佩斯郊區大片農田環繞的機場上。第一次來到歐洲,追著落日步入潘諾尼亞,一切似乎都如同千年之前羅馬人初入此地時的樣子,平坦的原野綿延至天際,星星點點的樹林,拂過溫暖干燥的風。
2012年夏,我們兩名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學生應匈牙利索爾諾克市Damianich Jannos博物館和羅蘭大學的邀請來到匈牙利,一個深藏于歐洲大陸中部的國家,參加為期一個月的發掘參觀活動。既不為李斯特的音樂盛典,也不為吸血鬼出沒的塞伊特城堡,我們的目標是更遠古時代的遺跡,帶著好奇與疑問,體會一次匈牙利考古的鑿空之旅。
他們怎樣進行考古發掘?
說到最讓中國人有熟悉感的歐洲民族,匈牙利必居其一。無論是他們姓前名后的命名方式,還是與匈奴人似有似無的親緣關系,都在歐洲大陸獨樹一幟。目前的學術研究認為,匈牙利所在的潘諾尼亞平原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至公元前一世紀末,羅馬帝國的軍隊所向披靡,將帝國邊界推至多瑙河,河南岸的廣袤平原成為潘諾尼亞行省。公元4世紀末,在匈奴人西遷導致的民族大遷徙壓力下,羅馬帝國崩潰,其軍團也撤出了潘諾尼亞平原。繼之而至的阿瓦爾人、斯拉夫人都曾在這個地區短暫停留。公元10世紀左右,馬扎爾人從東方草原遷至潘諾尼亞,并從此定居、建國,成為現代匈牙利人的直接祖先。歷史上的匈牙利是一個多民族交互的區域,被譽為歐洲的“十字路口”。來來往往的人群為這片土地帶來了豐厚的文化資源,目前匈牙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有8處,內容涉及村落、城堡、教堂、墓地等多種類型。
我們的目的地為匈牙利北部邊境一個名叫科馬羅姆(Komarom)的小城市,小城北鄰多瑙河,南望人平原,曾經是羅馬軍隊的駐地。四百年間的經營使守軍營地發展成繁榮的小鎮,直至蠻族的鐵蹄蕩平歐洲,大平原迎來一批又一批新的主人。民族遷徙與停留的痕跡一層層沉積下來,直至20世紀的考古工作者將其發掘出。科馬羅姆就是歷史沉積層的一塊,小城爾部保存有歲馬人到來前凱爾特人的定居點遺跡,公元紀年之后的遺址有羅馬帝國駐軍的居住遺址、大量的阿瓦爾人騎兵墓(cavalry tomb),以及馬扎爾人的城堡與教堂。
發掘地點是科馬羅姆市Szony地區的羅馬帝國居住遺址。這個地區的民居十分密集,但遺址所在區域卻是一片空曠的草場。羅蘭大學考占系已經在這里駐扎了20余年,將其作為羅馬時期考古專業的實習基地。一同發掘的克里斯蒂娜告訴我們,羅蘭考古的學生每年都需要參加田野實習,本科生為兩周,碩士和博士為一一個月,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理論實踐相結合”。
工地在遺址北部,開有12個4乘4米的探方,兩個探方為一組進行發掘,之間不留隔梁。根據勘探結果和前幾年的發掘經驗,這次的工作重點是找到居住遺址中的下水管道。我們在L15-L16探方中工作,這里的發掘工具并不陌生,鐵锨、鎬頭去除表土層,再用手鏟、刷子慢慢清理,發掘方法上和國內差別不大。但各項活計都要親力親為,對于習慣了民工大叔、大嬸幫忙的我們,實在是體力上的考驗。實習時需要自己動手——在歐洲的考古教學中是司空見慣的現象,老師認為這樣有助于學生深入了解地層結構,將來有工人輔助發掘時才明白如何指揮,我們只好在中歐夏季燦爛至極的陽光下揮汗如雨。隨著探方一點點加深,各種遺跡現象漸露端倪。探方東部出現一條南北向的溝,其西有一排排列整齊的磚,疑為建筑的墻基,溝則為遺址廢棄后人們取磚留下的痕跡;再向西發現大量磚瓦碎塊,清理后露出有黑黃色條帶圖案的堅實地面;這次發掘的重頭戲出現在探方西南,清理出一段羅馬時期的陶制下水管道,橫剖面為長方形,南北向鋪設,周圍發現大量直徑不足一厘米的磨圓石子;其他部分探方中也發現有墻基痕跡。探方中出現遺跡后,領隊老師會組織相關學生對其進行測量、繪圖、拍照。從20多年來的發掘總平面圖看,這次工作的主要成果在于補完了遺址東側長方形房屋的墻壁和排水管道,為研究羅馬駐軍居住遺址的布局提供了更多證據。
遺址的出土物較少,但很有特色。紅色陶片薄而光滑,有凸起的人物和野獸圖像,源于羅馬顯貴們使用的高級紅陶器;灰色陶片厚而粗糙,沒有裝飾,來自本地居民的日用陶器;出土的玻璃片極薄,內壁涂有指甲油一般的亮彩,在陽光下浮起乳白色的光暈;壁畫由紅黑兩色構成,雖然大部分已變為碎片,但仍然線條細膩清晰。遺址發現的獸骨和建筑殘塊也悉數收集,所有出土物放于一個收納筐中不做分類。
匈牙利考古在發掘方法上與國內差別不大,但在記錄理念上與我們有很大不同。這里似乎沒有明確的“地層”觀念。每一個探方的每一個新現象都按發現的先后順序給一個編號(SE),并填寫記錄卡。這個“新現象”可能相當于國內的“堆積單位”,它可以是一種顏色的土層,可以是一排墻基,也可以是一片瓦礫堆積。即使相同的現象延伸到不同探方中,也會因發現先后而有不同的編號。發掘結束后,負責人需要填好不同探方之間SE的對應關系表,繪制圖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圖。這樣,將所有堆積單位納入到同一個編號體系中,有利于減少推論矛盾與信息丟失,但同時要求記錄者能夠全面掌握工地情況,并保證不間斷記錄。所以,匈牙利工地上的全部記錄工作都由領隊完成,包括每天的日記、每個探方的總記錄、工地總記錄、SE關系圖等等,工作十分繁瑣辛苦,發掘結束后還要將記錄編寫成初期報告。與此同時,這里的學生,特別是本科生只負責發掘,沒有記錄任務,只在每周工作結束時才會在老師的帶領下“串方”,由每個探方的負責學生對該探方的發掘情況進行介紹,回答提問,最后老師再做總結。在我們看來,這種只負責發掘不參與記錄的考古教學方法可能會使學生的田野能力有所欠缺。
發掘期間,我們住在當地的青年旅社,三四個人一個房間,生活條件不錯,還能看到不少來此投宿的背包客。工地的作息時間與國內有所不同,為早晨六點至下午兩點的連續工作制,早飯也只能在探方邊解決。可能是因為匈牙利盛夏的氣溫很高,為了避開40多度烈日的炙烤,才把發掘安排在相對涼爽的早晨和上午。下午兩點以后,大家躲在涼爽的旅社里,羅蘭大學的老師會不定期地給學生們講一兩個小時課,聽不懂匈牙利語的我們則在房間里看書。晚上,大家一起烤肉、聊天,氣氛十分愉快。和我們一同發掘的學生有近20人,大部分是剛上大學的一年級學生,另外有五六個博士生。和中國的情況一樣,羅蘭大學考古系也以女生居多。不過,克里斯蒂娜告訴我們,歐洲的考古隊往往更喜歡要女生,因為女生有耐心,干活細致,這一點似與國內不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