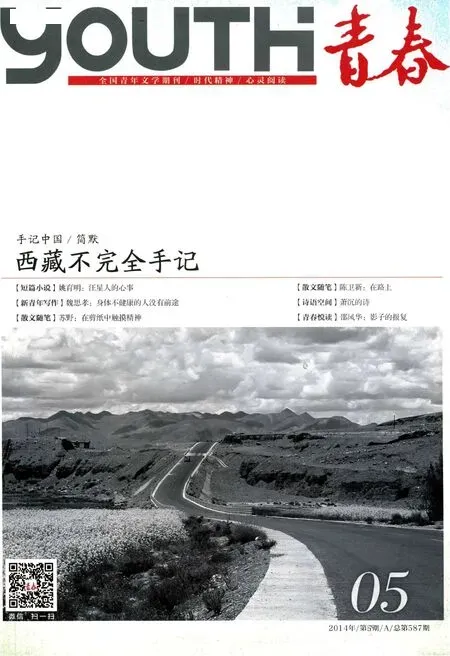在剪紙中觸摸精神——計建明的人生與剪紙藝術
蘇野

在《經過省察的人生:哲學沉思錄》這部探尋人生價值、充滿對人類終極關懷的“精神自傳”中,作為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最杰出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和哲學家一員的羅伯特·諾齊克,以普世而不乏自我反省精神的語調如此結束了簡短的“導言”:
很久很久以前,哲學曾經承諾給予人們比思想內容更為豐富的事物。“雅典的公民們,”蘇格拉底問道,“你們一門心思貪婪地積累財富,追求名位和聲譽,但卻從不思考和關心如何追求真理、智慧,如何讓自己的靈魂升華,難道你們不覺得羞恥嗎?”他談到了我們的靈魂的狀態,他讓我們看到了他自己的靈魂的狀態。(《經過省察的人生:哲學沉思錄》,羅伯特·諾齊克著,嚴忠志、歐陽亞麗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頁9)
這是諾齊克所擅長和喜歡的路徑:回歸傳統,以向蘇格拉底致敬的方式,在物質和精神、欲望和理性、智慧和無知的并置中,質詢一個人生存的精神根基。蘇格拉底曾經作過一個著名的論斷:沒有經過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雖然諾齊克覺得這種絕對的二元對立過于峻嚴和苛刻,但他無疑非常認同蘇格拉底論斷中的潛臺詞:一種審視和沉思人生的態度是必要的。諾齊克說:“當我們用經過自己深思熟慮的想法來指導生活時,我們所過的就會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過省察的人生:哲學沉思錄》,頁5)這種生活未必非得像蘇格拉底那樣建基于對邏各斯、真理、智慧、美德等的激情追求,但它一定包含了對未知事物、精神價值和虛無之物的信任,以及對人類創造力和超越性的熱愛,體現了超越生存的物質必需、感官欲望和庸俗道德的形而上向往。它肇始于個體對生命的沉思、自我的確認和對價值的甄別,經過汰洗與蒸餾,而結晶為對精神的皈依和修行。因而,它是本真、完整而自性、自在的,是值得信賴的,貫注著對物質的俯視和精神上的驕傲。我對古鎮同里剪紙藝人計建明的了解和認識與此接近。
2001年某日清晨,經營企業的計建明在同里退思廣場晨練太極拳時,發現一個老者的動作不合法式,上前糾正,從而結識了這位老者——南派剪紙藝人陳南君,其時他正寓居同里。在與陳南君進一步交往后,計建明迷上了精巧玲瓏而靈秀輕盈的南派剪紙,從此一發不可收。在說服家人后,他果斷放棄了對企業的經營,轉入對剪紙的學習和創作。這是一次勇敢的選擇,也是一次越軌和跨界的轉型,它建立在挑戰與背叛趨利避險、樂安厭危的人之本能的前提下。這意味著計建明首先必須退出安穩的生活狀態,喪失現實中的擁有之物,和一個可預見的、有確定碼頭的未來,從一無所有開始,摸著石頭過河,探入一個陌生、異己,蘊含未知風險的疆域。并非所有人都具備這種壯士斷腕、背水一戰、重起爐灶的決斷力,也并非所有人都有勇氣選擇承擔因命運未卜而產生的漂浮感、懷疑、焦慮、失望、卑微等精神重負。這個選擇同時也是智性的、精神的,具有象征意義,它至少喻示著物質的退隱、文化的浮出地表,喻示著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精神需求的撥亂反正,意味著一個人能夠對鄙俗物質和粗魯感官忽略不計,而去毫無保留地信任精神潛力和創造性。
大多數民間剪紙從業者都生長于一個剪紙文化已成思維定勢和條件反射的濃厚氛圍中,從小接受區域文化和家族傳承的熏陶,在耳濡目染中與剪紙逐漸血脈相連。剪紙是他們與生俱來、隨身攜帶的天賦和記憶,是天性和本能,更是他們自我人格和精神生活的天然成員。他們從眾多具有示范性、榜樣性的先輩的言傳身教中熏染了觀念和情感的教育,獲得了經驗傳承、藝術摹本和美學范式,以及看待世界的視角和原理。他們從活生生的、流動的、豐富龐雜的剪紙傳統中獲益良多。最為重要的,也許是這個歷經漫長時間、帶有歷史說服力的悠久傳統本身即擁有價值上的合法性,從而賦予他們的剪紙以正當的意義。他們沒有價值焦慮,無需為自己的行動尋找理由,他們對剪紙的熱愛是天然的。而作為剪紙生存根基的特定地理環境和多元化民俗生活也為他們提供了創作資源和用武之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些民間剪紙藝人的作品就像牢牢粘附在原生態民俗生活皮膚上的毛發,裝飾對象明確,功用廣闊,多數時候,他們無需為自己尋租廣告燈箱。
與這些成長于本真生活、生存于民俗母體的藝人不同,半路出家的計建明置身的并非一個剪紙習慣根深蒂固的環境,他從事剪紙只是一個偶然的物理反應之后判斷和選擇的結果,不但不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分娩,相反還是對原初文化環境的強行剝離。吳江、甚至蘇州,并非傳統意義上中國民間剪紙藝術的重鎮。從古至今,蘇州并不存在一個脈絡清晰可辨、同時深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剪紙傳統,從來沒有人把蘇州的剪紙藝術與河北蔚縣剪紙、山西中陽剪紙、河北豐寧滿族剪紙、浙江樂清細紋刻紙、云南潞西傣族剪紙、陜西安塞剪紙等列入世界非遺保護名錄的剪紙藝術相提并論,蘇州剪紙也遠不能與代表江蘇剪紙藝術成就、最常被人提及和贊譽的揚州剪紙并駕齊驅。這座江南文化的典范城市和偉大的策源地,也許迄今也未產生一位真正獨立,具有藝術范式、美學及情感輻射力的剪紙大師。在蘇州,公共輿論空間和文化生活的慣性所給予剪紙的關注極其稀薄,相對于東山磚雕木雕、桃花塢木刻年畫、刺繡、彈詞、飲食文化等,剪紙在吳地民眾的日常精神和深層心理中的分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它在蘇州城市文化結構中所占的比重,所得到的權力和資源的傾斜,以及嚴肅的藝術關注微乎其微,它幾乎從未在社會中為自己贏得任何認同感和美譽度。與蘇州類似,隸屬蘇州的同里剪紙藝術氛圍也極其淡薄,生存空間則更為狹窄。決定一門心思從事剪紙,對計建明而言,就是探險和拓荒,就是從無所憑依和一窮二白中起步,面對并承擔未知的風險、生存的考驗和意義的焦慮。
作為“試圖認識自己的獨特性的一個獨特的存在”(《人是誰》,A·J·赫舍爾著,隗仁蓮、安希孟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16),在伸張生命的過程中,為達成存在的獨一無二感和一種價值自信,獲取生命的自足與圓融,每個個體人都要通過“認識自己的獨特性”來尋求和建構自我,并落實與生存境遇相匹配的存在模式和精神內容。“獨特性”是個體生命現實身份、精神身份的脊柱和腳手架,它制造出幸福感、成就感和滿足感,撐持著日復一日的日常生命。所以美籍猶太神學家A·J·赫舍爾說:“對人的所有認識都源于自我認識,人永遠不能遠離他自己的自我。”(《人是誰》,頁10)如此,生命才能綿延至遠方,攀升至高處。智力勞動和文化創造則是自我“獨特性”的重要載體和容器。經由這種長久而專注的心靈修行,個體可以緩解與世界交往中生成的的“存在之難”(讓·科克托語)和痛苦意志,統一蕪雜的精神秩序,并構筑起一個內在、完整的價值世界,通過許諾它與一個悠久傳統的聯系而賦予自身以價值,從而安頓自我。對個體的自我認同來說,這是一種帶有超越性的定位,它使得個體僅憑自身充滿時間性的精神勞作便可以贏得存在的意義和藝術合法性,而不必依附于短暫脆弱的現實體制,因為它“涉及的是一事物的內在統一融貫性”,而“無需與另一事物——任何更大的事物——發生聯系以便獲得價值”(《經過省察的人生:哲學沉思錄》,頁151)所以,赫舍爾又說,自我認識,“就是尋求在平庸雷同和延續不斷的天性中找不到的純真性”,“尋找自己的命運”(《人是誰》,頁16)。
這樣來理解,計建明十年前作出的那個分水嶺式的勇敢選擇,不僅表現了他對剪紙藝術的強烈興趣,也不僅預示著他人生軌跡的轉向,它還包含著更重要、更豐富的意義和內涵,一定有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和迫切的需求主宰著計建明,使他勇于選擇白手起家和由此產生的挑戰。借用A·J·赫舍爾的觀點,我把它理解成是由心身統一的訴求而產生的自我和身份意識的覺醒,這種覺醒促成了諾齊克式的對人生的審視和反省。計建明意識到了,要力圖認識所從事工作的意義,并重新定義自我和自我的價值。而一個人只有借助于智力勞動和文化創造,返回到一個源遠流長的文化故鄉中,才能得到定位,擁有皈依感,具備持恒性,自我價值才能擁有超越時間的紀念性。與陳南君及剪紙的相遇,為計建明的人生省察提供了一個降落的機場,并使他將之落實成具體的人生行動。
從深有積蓄的工廠主到白手起家的藝術家,從物質上汲汲營營到精神上枯坐息心,這種斷裂式的轉折顯然不是幡然醒悟、浪子回頭的頓悟,而應該是時間帶來的禮物,是長期痛苦思索后行動的升華。在計建明結識陳南君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細節,一個類似鎖扣的中介:太極拳。它開啟了兩人的交往之門,并進而促成了計建明的轉型。在這一相遇中,作為太極拳指導者出現的計建明,本身就包含藝術人生上省察的態度、修煉的根基和漸悟的可能。同時,太極拳靜、定、慢、勻的儀軌也極其契合像剪紙這種手工藝術的精神氣質,其舒緩輕靈、剛柔相濟的動作外溢出的深遠韻味,以及取法道家洞悉陰陽動靜之理、盈虛消長之機的哲學內涵,又無不與藝術最高境界淡泊自持、寧靜致遠的神髓相通。可以這樣說,長期習練以虛、柔、圓、松著稱的太極拳,已經為計建明轉向剪紙藝術奠定了厚實的精神根基。計建明的轉型既緣于陳南君的偶然出現,也構筑在自身必然性的基石上。
按照卡西爾的看法,人是“符號的動物”(《人論》,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頁34),具有創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質就是其無限的創造活動。只有人才發展了“符號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符號是“人類的意義世界之一部分”(《人論》,頁41—42),帶著人類走向通往“理想世界”和文化世界的道路。沒有神話、宗教、語言、藝術、歷史、科學之類的符號系統,人就會生活在狹隘而凝滯的囚徒狀態中,就像柏拉圖著名的洞穴比喻形容的那樣。一個人從事智力勞動,既出于延展生命、擴大視野的渴求,也出于填補時間、充實精神的經營,而并非都如蘇格拉底那樣出于對真理、智慧、善、靈魂之類對象崇高而神圣的信仰。但無論如何,每一個不甘平庸而愚蠢的人,都通過他所從事的創造性智力勞動,不斷刷新著他的生活經驗,不斷更改著他對世界和自我的認知,從而讓自己的生命駛向了更為廣遠的天地,并賦有了精神的光華和人性的尊嚴。智力創造的過程,也即創作者的精神和命運展開的過程。智力勞動的創造性清楚定義了創造者本人,使得他的精神自我與肉體存在區別開來,也使得他的精神世界與別人的區別開來,從而賦予他以存在的價值。這時,他的精神勞動就是一種創世和命名,一種自我形象的生成和彰顯,并作為他的精神標簽而被別人所接受。在這個意義上,人確實如卡西爾所說是“符號的動物”,有賴于他所創造的符號來顯示存在,展現他所認為的“理想世界”,并進入歷史。對計建明來說,剪紙就是這樣展現精神、表達自我創造力和超越性的一個符號,一個標識。
計建明的剪紙以單色剪紙為主,兼備陰刻、陽刻,多為點綴裝飾的擺襯類剪紙,如喜花、供花等,內容涉及民間剪紙常見的人物、動物、植物及符號四大題材,既有祥花瑞草、飛禽走獸、瓜果魚蟲等表達祈福納祥、避邪鎮惡愿望的吉祥形象,也有自然山水、人生禮儀、民間傳說、現實物象、宗教信仰等蘊含剪紙人情感寄托及中國民眾心理積淀的文化符號,層次多變,意象繁雜,主題多樣。在題材上,計建明正以令人詫異的開闊視野、潛心修行和吸納、表達的能力,展現著自己內心的豐富性和孕育創造的潛能。他的剪紙大多輪廓清晰,構圖簡潔,提倡神似基礎上的寫實和有效節制后的優美,很少有豪放、粗獷的夸張變形,和放僻、邪侈的巫性思維,而是通過靈巧的布局、精細的刀工和秀美的線條,營造出契合日常經驗的飽滿造型和鮮明形象。從整體看,計建明的作品沿襲了中國南方人文傳統和剪紙藝術含蓄內斂、深秀婉約的地域精神,呈現出一種被馴化過的清新雅致、空靈雋逸的美學特征,和簡約云澹、蕭散通脫的人格境界,洋溢著精神與靈魂的自在之美。
與那些威猛厲獰、大樸不雕、原生態刻寫集體原型意象而呈現出原始文化野性混沌氣象的剪紙相比,計建明的剪紙更像一種散發著濃郁文人情懷和優雅藝術氣息的“雅文化”,這尤其體現在那些以同里自然景觀為摹本、旨在為江南山水的魂魄寫形造神的剪紙作品,和以古代正典的文化傳統為源頭而創作出來的作品中。于前者而言,計建明有一系列關于同里自然景色的剪紙作品,涉及退思園、珍珠塔、春雨亭、羅星洲、三橋、肖甸湖以及街巷里弄等,其中退思園還被多視角、多場景地反復多次表達過。這些以寫實為主,但又不乏巧思和提煉的作品是計建明最具代表性、創造性、最成熟的藝術成果。它們大多表現亭臺樓閣之類的建筑,以及環繞其周圍的山石水樹,構圖嚴謹,刻工精巧,各有創意,既有規整、謹飭之作,也時有飄逸之思,格調明快柔和,線條悠揚綿長,物象塑造精確,注重虛實、繁簡的對稱與平衡,繁密而不擁擠。比如,獲江蘇省民間文藝“迎春花獎”的《同里退思園》即為典型。這幅剪紙宏觀表現退思園的主要景致天橋、琴房、眠云亭、回廊及攬勝閣,繁復、宏大而又細膩、真切,展現出“世界文化遺產”的幽雅沉靜。難得的是,它還將五處景點勾連成一個整體,分別賦予琴、棋、書、畫、繡的不同意境,并分別嵌入琴、棋、書、畫、繡五個漢字的筆畫,將字體的書寫和詩意的畫面完美融合,線條流轉自如,分而不斷,思慮縝密,構想奇妙。而《肖甸湖》和一幅題為“江南水鄉”的剪紙表現的則是郊野之景。前者上半部分描述肖甸湖林蔭道一側的景色,一排樹,一個亭子,亭子中對坐憩息的三個人,遠處沿路走來的人,以及路邊的欄桿;下半部分則系剪紙中疊合、剪刻再展開后形成的倒影。整幅剪紙畫面粗放、簡略,注重總體輪廓的線條收束和伸展,尖刺狀的花紋和大塊大塊陰影的配合使畫面顯得粗豪,具備了一種視覺沖擊力,但整幅畫面上除此之外空無一物,大片大片的空白又使得全部物象似乎飄浮在虛無之中,中和了這種沖擊力,使整幅畫面具有了一種空靈之美。后者更像是素有煙霞之癖的中國古代文人表達隱居之樂的畫作,江水流貫整個畫面,遠處的山影、云彩、歸舟,中部的疏柳、拱橋、茅屋,近處的蘆葦、水草和垂釣者的專注,都渾然一體,自成一個超然物外的獨立世界。這幅作品借鑒吸收了古代文人畫的流暢線條、留白手法和寫意精神,講究神韻和情趣,著力表現隱居者寄身天地的安寧和清靜無為、寵辱不驚的氣度,以及崇尚自然而不凝滯于物的精神境界,充滿了行云流水般舒緩輕盈的韻律感和節奏感,有一種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安靜之美,體現出纖細精致的美學追求,營造了一個充滿詩意的文化空間。同時,作為與之耳鬢廝磨的日常經驗和對起居棲息的家鄉的摯愛之情的產物,這些作品又保有了自己的真實性,具備了一個藝術品在時間中生長、延續所必備的生活根基和情感根基,對類似語境、氣場中的有著相同情懷的人能夠產生共鳴共振的感動力。它們是對煙云水氣的江南山水和風流自賞的江南情懷另一種形式的藝術書寫。
于后者而言,計建明有不少以純正高雅的正典文化符號為表現對象的剪紙作品,如趙孟頫以楷、行、草相雜所書的陶淵明《歸去來辭》,北宋張擇端所作風俗長卷《清明上河圖》局部,以《紅樓夢》為藍本的閨居仕女形象和古人文人知識分子節操象征物的梅、蘭、菊、荷等。趙孟頫書法和《清明上河圖》局部剪紙均為臨摹,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摹本為旨歸。兩幅作品采用陰刻手法,運刀精微,刻畫細膩,纖細入微,盡管媒質不同,但在布局和細節處均與原作酷似神肖,方寸之間盡顯原作本色,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前者通篇雍容寬博,結體豐容縟婉,黑色質地恰如其分地體現出原作凝重厚實的底蘊和風神,同時又平和中見靈動,溫厚中顯英邁,結體嚴整,筆法圓熟,通篇宛轉流麗,徐疾有致,充分表現出趙孟頫書法遒媚秀雅、珠圓玉潤的美學特征和奔放自由、神完氣足的精神氣息。而《清明上河圖》局部剪紙則有多個版本,分紅色、青色兩個系列,內容均是原《清明上河圖》末段市街部分汴京的城市生活,表現出強烈的市井氣息和俗世生活永恒循環的常態性。我們可以以一幅紅色質地的作品為樣本簡析一下它們所蘊含的剪紙人的審美趣味、藝術努力和和剪紙的表現力。首先,在構圖上,這幅作品選擇的是原圖末段靠近汴河的一個弧形路口,既非首段的清冷蕭瑟,也非他處繁華熙攘的場景,而是兩者的一個中和,一個平衡的狀態,整體上平穩、舒緩的意境反映出的是經驗生活日常化的穩定、靜止,是平凡、穩當,而非我們對《清明上河圖》正常理解的物質生活的狂歡和放縱,選擇此而非彼,當然與小鎮文化人、太極練習者計建明喜靜不喜鬧的平和心境關聯甚巨。畫面上,街市占據絕大部分篇幅,汴河在右上角露出一角,從左上角到右下角,有三棵樹沿對角線陳列,繁簡不一,相互呼應,使全圖布局氣韻相通,連貫完整。圖中人物雖舉止神態清晰可辨,但剪紙特有的塊狀花紋使得他們略顯呆板、僵硬,缺乏那種內在的動勢,這一方面顯示日常生活永恒性的靜止,同時也表明他們并不完全是這幅剪紙的主體。在節奏和韻律上與人的靜止、疏遠不同的,是居于畫面中心的屋頂和右上角的汴河呈現出的繁密、復雜的特征和蓄勢待發的動勢。屋頂上細密而重復的水紋與傾斜的屋脊相互應和,蓄積著屋面向前推進、延伸的勢能,偶爾的壽狀花紋與縱向的立柱、門窗,又使得剪紙在構圖上增加了變化。汴河里的舟船和水流則塑造得更為繁復和立體,線性、塊狀、三角、圓形等各種線條縱橫交錯的拼合、銜接,使船只顯得異常逼真、細膩,水面上用于裝飾的舒展的云紋,造成汴河風生水起、波濤涌動的情態,與屋面遙相呼應。屋面和水面使用的各種紋飾,包括樹枝骨干式的枝條,都體現了剪紙藝術刀法上的特點。與筆墨相比,這是一種屬于剪紙的、主動積極而平緩適度的改寫與變形。這表明,剪紙人并不完全是亦步亦趨地摹寫原作,他在拓寬剪紙的表現空間,尋求其新的藝術可能性,并企圖用剪紙的語言重新敘述一個傳統。
至于其它正典文化符號類剪紙作品,如以《紅樓夢》為藍本的閨居仕女和梅、蘭、菊、荷等,構思上與《肖甸湖》類似,以陽刻手法為主,絕無背景裝飾,多用云紋、水紋構圖,通過刻畫人物或物象的動作和情態來表現個性特征,大多呈現出輕盈靈動的美感。仕女或端莊嫻雅,或黯然傷神,或優游閑逸,植物或冰清玉潔,或瀟灑儒雅,或孤標傲世,均帶有溫文爾雅、卓犖不群的君子之風和文人之氣。相比之下,山東剪紙藝人尹秀鳳所剪的紅樓夢人物像(尹秀鳳《實用民間剪紙藝術》收錄其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和妙玉四幅人物剪紙,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98—99)采用陰刻手法,大塊大塊的剪紙領土環繞著人物,像圍欄封鎖和限制了人物的活動空間,人物就像被圈養了一樣,嚴重束縛了觀眾想象力遨游的疆域,因而減卻不少輕盈靈秀之美。
當然,計建明也創作了不少傳承并體現剪紙藝術悠久傳統的作品,它們延續了這一傳統的造型觀念、表達程式、審美情趣,帶有強烈的民俗色彩和素樸的美學特征。比如說那些通過刻寫動植物,借助諧音、象征和表號的寓意手法,表現民間延年增壽、婚戀祈子、辟邪禳災、納福招財等主題的剪紙,和表現人生禮儀、節氣時令的剪紙。我常常著迷于計建明寥寥幾剪所呈現出的熊貓的憨態可掬、龜的溫和靈異、虎的威猛稚趣、龍的夭矯霸氣。我尤其鐘愛計建明“十二生肖”系列中那種樸拙天真而又不落凡俗的情趣,特別是鼠的形象,具有一種動人心魄的本真率性之美,令人久久難以忘懷。對《老鼠娶親》這樣的作品,我愿意盡情暢想其背后所深藏著的那個生機勃勃、歡快淳樸的民俗世界,以及人樂天知命的情懷,雖然不知有多少人多少藝術曾經表現過這些已不同程度消逝的世界,但對生活在破碎異化、道德失范、意義懸隔的現代世界的我們,它仍然保持著新鮮感和吸引力。毫無疑問,在這些作品中,計建明不僅傳承了古老的萬物有靈論,還以高超的構思和裁剪能力和一種盡脫塵滓的品位,將之表現了出來。通過它們,計建明給我們傳達出一個與剪紙有關的、逝去世界的氣息和氛圍,賦予它藝術的光芒,也帶給我們希望。只有通過身臨其境的想象以置身于過去,并深入體味其語境和人心,才能做到這樣。
在同一種審美向度上,計建明還剪過戲曲臉譜,剪過戲曲題材的西施浣紗、貴妃醉酒,剪過宗教信仰中的十八羅漢、道教八卦圖,甚至還剪過紅色資源,他有一幅剪紙剪的是馬恩列斯毛,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題材生僻,造型古拙,頗有情趣。這些作品的文本形象和對剪紙人的精神要求迥然不同,或審丑,或秀雅,或正統,或嚴肅,與那些民俗色彩、原始巫性思維濃厚的,最優秀的剪紙作品(比如甘肅鎮原剪紙大師祈秀梅的《抓髻娃娃》、《神虎護人》、《伏虎之神》等,見《剪紙民俗的文化闡釋》相關插圖,王貴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或陜西旬邑剪紙大師庫淑蘭的《剪花娘子》,見《再見傳統(4)》,呂勝中著,三聯書店2004年版,頁109)相比,它們的精神氣質和藝術品位并不遜色。然而,計建明視野的開闊和高遠的追求不僅僅止于此。在藝術創作上,他始終以一種開放嚴肅的精神,潛心修行的態度和勤奮自省的品質全力以赴,不斷拓寬自己的精神和創作疆域,從不故步自封,自我鎖閉。計建明的多數作品,即便是那些最符合剪紙傳統主流、以祥花瑞草寄托吉祥寓意的作品,都貫徹了他渴求創造、自我突破的追求。比如在桐廬國際剪紙藝術大展上獲獎的《大雙喜》,大大的“喜”字疊在花草紋樣上的立體式構圖,和畫面內部設置的六個圓形裝飾圖案構成的整個團花,以及環繞團花一周的半圓形裝飾花紋,構思巧妙,又契合圖案所蘊含的團圓、吉祥之“意”。又如十二生肖系列,計建明有多達幾十種版本的剪紙,有的刻畫各生肖不同的動作情態以表現不同性情,有的組合搭配別具新意,有的則將生肖置于道教八卦圖中,還有一幅甚至將十二生肖剪成統一的坐姿和相同的表情,造型之巧妙、想象之奇特讓人過目難忘。那些關于魚、龍、蓮的作品也呈現出這樣刻意求新、求變的巧心和追求。再如,民間剪紙中常有“百壽圖”、“百喜圖”、“百福圖”等通過反復堆砌、重疊將吉祥意愿推至極端的圖案,但計建明從不將已然存在的傳統當做成例,他恥于重復與雷同,他的類似圖案在字的大小、字體的選擇、排列方式上都有不小的變動。這雖不至于形成審美的沖擊和震撼,但至少表現出一個藝術家嚴肅認真的態度、起碼的藝術良知,和永不滿足的創造精神。寓意千篇一律,但形式千變萬化,構思精巧詭譎,這正是計建明進入剪紙這一行當十幾年來呈現在藝術上最突出的精神面貌。
我以為,這種精神面貌起源并昭示了一個深遠、復雜的文化困境。著名藝術史研究家石守謙曾經分析過十六世紀中國畫壇的文人畫風的變革、更替情況。當文征明出于失意文士消極遁世、避居山水的心智需要和情感訴求,而開創出清逸深秀的吳派山水畫風時,其作品確實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而當后起的新一代文士沿用同樣形式進行創作時,卻因缺乏深切經驗和真摯情感而剝除了原本真實的抒情內涵,而衍變成筆墨與物象虛實關系的游戲,衍變成紙面上的疊石理水,因此廣受新的審美趣味的排斥和抨擊,并最終被董其昌的繪畫革命取代。(《風格與世變:中國繪畫十論》,石守謙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297以下)形式雖然相同,但由于語境、主體和受眾的推移、變化,原先的創新卻演變成陳腐的慣例,抒情變成了煽情,原先高效的抒情機制變成了真情實感的桎梏和牢籠。這也正是現今幾乎所有民間藝術從業者的最大困境。類似剪紙的民間藝術原本生發于民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具有明確的功能性和儀式性,寄托著社會的物質需要和民眾的心靈需求,是民眾的悲歡哀樂、習俗慣性和廣泛民意的超強載體,擁有豐厚的生存土壤和勃發的生命力,富于那種在時間長河中反復淘洗而永不褪色的持久之美。而如今,土壤不再鮮活和必需,儀式變成符號或狂歡的借口,民間藝術成了利益的工具、表演的道具、博物館里的標本和虛妄的衣架,變得空洞而虛腫,骨質疏松,沒有血肉的支撐,缺乏感動力,遍布生存的危機。每一個文明社會中的人士從事原本屬于民間的藝術的人都會直面這樣的困境。除了完善技藝,修習精神,重新尋找變化和革新的可能,尋求自己的創作特色外,還必須將生命底蘊和精神灌注于作品中,賦予其以堅實的現實土壤和精神根基,在程式化的表達中,重新找回作品所能給予受眾的心靈的感動力和驚奇感,就像畫史上董其昌所做的。
如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計建明了,他大多數作品表現出的題材、手法和形式的創造意識,正是現代民俗藝術試圖突破困境的一種努力。這涉及到一個重要的藝術命題。當我們憑借一己之力、短時間內在本體上無法改變一門藝術時,變更作品形式也許是體現個人價值的一種出路,這至少可以部分吸引受眾。以古典文化符號諸如道教八卦、書法等類似元素為創作對象,既是廣采博收、吸納百川的精神修行與心靈積蓄,也是一種形式探索,而《清明上河圖》局部剪紙也許還是計建明擴大視域、追求宏大場面的嘗試。當然,計建明更意識到作品的精神和價值根基、以及它與受眾必須建立精神聯系的重要性,那些裁剪同里自然景觀和江南山水的剪紙正是他在精神上重新定位,并追尋價值根基的產物。他一直在積極尋求本土創作資源,以便為自己的作品取得更為穩固的現實和歷史支撐點。比如,他一直計劃要將同里宣卷、贊神歌、珍珠塔故事、蕩湖船、打連廂等傳統及民俗用剪紙形式表現出來,因為在同里,它們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體,包含了精神的價值。在這里,計建明又表現出了一個藝術家的敏銳、睿智和志存高遠的堅定,以及十年孜孜不倦修行而成的完整、深刻的精神內涵。毫無疑問,如今的計建明已經在剪紙中安頓好了那個曾經惶惑迷茫的自我,觸摸到了優雅純正而具有超越性的藝術精神。他正在慢慢展開自己的命運畫卷,裁剪著一個嶄新的自我形象。在同里,在吳江,他已經部分綠化了原本荒蕪的剪紙沙漠,書寫著新的文化版圖,創造出了屬于自己、屬于剪紙的藝術氣候。當然,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從藝十年的計建明還處于藝術的中途,一切都還不能蓋棺論定。但憑借著他已經展現出的創造力,憑借著他的開闊視野、藝術品位、敏銳的洞察力和精益求精的超越精神,假以時日,我想,他一定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剪紙大師。
言及于此,我忍不住要批判一種庸俗的觀點。一旦談及計建明的剪紙,那些心智鄙陋、目光短淺的傖夫俗子往往津津樂道于他技藝的嫻熟、作品數量的壯觀,以及曾經幾次在哪里哪里上過電視。幸好我在跟計建明閑聊時,他本人并未以此沾沾自喜。我以為,幾分鐘剪出一個逼真形似的作品,不過是長期浸淫于剪紙、熟能生巧、水到渠成的結果,只能證明剪紙人訓練有素,技藝扎實,在基本能力上達標了,具備了創造的前提,遠不能表明他已經登堂入室,抵達藝術創造的核心地帶,掌握了藝術的真諦。嫻熟是工匠的慣性和本能,是偽藝術品的征兆。在創作過程中,沿著根深蒂固的慣性和現成的摹本進行復制,是對自我和對世界的極其簡單的抄襲和嘔吐,卻并未創造出新的藝術品。一個人剪紙剪得再熟練,速度再快,剪出來的作品再寫實,再高度逼真,如果沒有創造性,沒有在作品中體現出他的情感、性情和精神深度,那也只是一個亦步亦趨、鸚鵡學舌的匠師藝人,是剪紙復印機,而非剪紙藝術家。沒有精神含金量的作品多,只能說明剪紙人曾經消耗的時間長度,但那些時間不會因此而沉淀下來,擁有存在的價值,更不能改變藝術平庸的本質。在藝術史的紀念碑上,真正能夠鐫刻名字的藝術家無一例外的都源于他的創造性,藝術品數量從來只是藝術品質量的可有可無的注腳。當然,恥辱柱或軼事留言簿之類的登錄得除外。而真正包含價值、耐人咀嚼的藝術品恰恰是在緩慢、艱難之中生成的,因為別出心裁、自成一格的嚴肅創造向來就是難產的。我很奇怪,那些藝術鑒賞上的淺嘗輒止、蜻蜓點水者,竟然始終不愿去弄明白藝術的真正價值在于表達藝術個體的創造力和人類無有止息的超越精神。至于把電視出鏡率、曝光率作為一種評價標準則更顯荒謬可笑,那是所謂明星的公眾人物作秀效果的衡量指標,只有那些寡廉鮮恥、靠別人眼球為生的伶人戲子,以及企圖從利益市場分一杯羹者才需要這種外在而虛假的幻覺支撐,時不時地撥一撥關注度的小算盤。以此來評價計建明,雖不無拔高知名度之嫌,但其實是對計建明的一種貶低和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