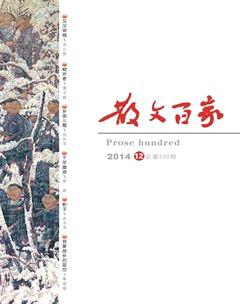鄉事三題
劉興華
借 糧
星星多,月亮少,借著歡喜要著惱。在農村人們最怕借口糧,自家都不夠吃,哪有借出去的米。
但怕嘛嘛來,正吃著飯呢,就有敲門的,吃飯的人心里一驚。
來人手里拿著一個粗瓷大碗,他嬸子、他大娘地叫著,說家里揭不開鍋了,有玉米面嗎?高粱面也行呀,先借一碗。
吃飯的這一家,假如正吃玉米面餑餑,喝的玉米面粥,再哭窮,說自己家也快揭不開鍋了,借糧的人哪里會信,還會被嚷得全村人都知道:“馬寡婦,憑什么一天天吃玉米餑餑呀,還不是仗著有個野男人往她家偷糧食呀!”
聽得人放下飯碗,把臉扭過來,連連說:“是呀,是呀,我就見村北的那個光棍漢子往她家跑過,身上的衣袋鼓鼓的,肯定裝得是糧食。一進去,好半天沒出來。”
村里有一幫嘎小子,晚上沒事,就跑到馬寡婦家的門前去,把大門的門吊掛到門鼻上,過一兩個小時再去看。如果門吊還在門鼻上搭著,說明沒人進去,如果門吊下來了,說明有人進去了。就會猜誰來了,是生產隊長,還是記工員。
農村人最怕人說閑話,舌頭下面壓死人呀。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不就是一碗玉米面嗎,心里雖然老大不情愿,還要盛冒尖的一碗。
臨走時,還要說,大妹子,先吃著,沒了再來呀!
借糧食的人好像自己也長了臉,因為人家給足了她面子。逢人也會說:“馬寡婦人實誠,看這碗裝得都冒尖了!”
聽得人也會說:“一個寡婦,拉扯著幾個孩子,不容易呀!”然后開始說她的男人,說在世時,是多么好的一個人呀,誰讓他幫忙,從來沒說過不行,好人不長壽呀,早早地扔下老婆孩子走了。然后就罵生產隊長,罵老光棍,欺負人家孤兒寡母,不是人,是畜生。
罵足了,罵夠了,說聲:“家里人等著做飯呢,我先走了!”端著碗哼著歌回家了。
農村人家都是一樣下地記工分,也是一樣分糧食。
會過日子的,知道算計著吃,夏天、秋天,地里的野菜多,野菜也新鮮,就去地里挖野菜,挖得多了,晾干了,放到冬天摻著吃。
不會過日子的,一看分了這么多糧食,就有柴一灶,有糧一鍋。飯做得多了,吃不了,就去喂豬。
有個婦女因不會過日子,丈夫和她離了婚,改嫁后還是不會過日子。
有一天我去她家玩,看到鍋里剩了半鍋粥。
我就問她:“大娘,怎么剩這么多呀!”
她聽了就呵呵地笑,說:“誰知道呀,做著做著就做多了。”
她家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都能吃,再加上她這么不會過日子,還沒開春,家里就斷了糧食。她和丈夫去集上賣木頭,賣了好買些糧食回來。中午讓孩子去大娘家吃。
這家在村西頭,孩子的大娘家在村東頭,到了中午,四個孩子去了大娘家,大娘家一家五六口正在吃飯呢,也不說讓過去的孩子一塊吃,就讓四個孩子眼巴巴地瞅著。一直瞅到刷了鍋洗了碗。然后攆著自己家的孩子說:“和你嬸子家的孩子出去玩吧。”
這家人吃得飽飽的,這邊的孩子還餓著呢,肚子咕咕的響著,快前心貼后背了,哪有勁玩,就回家去等。也不知等了多久,父母回來了,木頭沒賣了,父母一看孩子還餓著呢,做父親的一下子就火了,說:“以后你們再敢上他家去,我打斷你們的腿!”
放下木頭,就扶著墻根去找生產隊長,說自己家揭不開鍋了,老婆孩子餓得都快下不來炕了。
碰上隊長心情好時,開個條,讓找保管員借點糧食,等再分糧食時扣;碰到隊長正生閑氣呢,就會揮揮手說:“去去去,隊上哪里還有糧食,庫里只剩下種子了,等幾天吧,等幾天救濟糧就要下來了,到時多給你分點。”
那時我村還吃救濟糧,是上面撥下來的。一分救濟糧,村里就會敲鑼打鼓,高嚷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口號,提著口袋去分糧食。
借糧食的等不了呀,就求隊長,說:“你不怕我給咱村人臉上抹黑,就給我開個信吧,我領著老婆孩子去外村討飯去!”
那時去外村也不是隨便去,串親戚也要開證明信。隊長被逼不過,就撕條紙,寫上幾個字,讓借糧的人去找保管員。
借到糧食了,回家后大多還要吵一架,男人指著老婆說,再大手大腳,咱這日子就別過了。
挨餓的日子不好過呀,老婆也知道了糧食的珍貴,就天天省著喝稀粥,盼著救濟糧下來,再吃頓飽飯。
天上布滿星 月牙兒亮晶晶
忘記是一年之中的哪一天了,反正天已經很冷了,這時,村里都要召開一次憶苦思甜會。去時,天已經很黑了,凍得直流鼻涕,嘴里唱著一首歌:“天上布滿星,月牙兒亮晶晶,生產隊里開大會,訴苦把冤伸……”
開會時,會搭一個臨時的臺子,臺子用幾根木樁固定住,上面再鋪一層木板,上面再用蘆葦席罩起來,前面的兩個柱子上分別掛一盞氣燈。氣燈點亮前要往里面不停地打氣,氣打足了,點著時,燈會像放氣一樣“嗤嗤”地響著,那燈也就越亮。
會臺前方一般還要貼上用紅黃綠不同顏色的紙寫的會標,上面的字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訴苦大會開始了,總有穿得特別破破爛爛的人上臺發言,臺上講了什么,能聽到的不多,因為臺下人們不停地說話。說話的人多了,那聲音聽起來“嗡嗡”的。但有一件事我倒記住了,說一個放牛娃,冬天沒鞋穿,也沒屋子住,就住在牛棚里,為了給腳取暖,把腳埋進牛剛拉的糞便里。當然,還有一句最令人害怕的話:萬惡的舊社會,人吃人。
開完訴苦會,有人就開始往會場里抬干糧,開始抬來的是米糠做的,這是憶苦,其實當時有的人家連這也吃不上,見了糠餑餑就恨不能一口吞下去。姥姥拉了我一把,說吃一點算了,剩下的拿回家去吃。過一會兒,還會有白面包子吃。
包子也是用很大的籮筐抬過來的,也是隨便吃。說是隨便吃,人們就像搶一樣。一籮筐包子轉眼就沒了,手慢的就圍著送包子的人急急地問,包子還有嗎?我憶苦了,還沒思甜呢!送包子的人說,沒了,沒了,明年再來思甜吧。
那人聽了就很不高興地說,又要等明年,去年我就沒搶上包子,今年又沒搶上,我這真是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呀。
那天我搶到了兩個包子,一個給了姥姥,姥姥吃了一口,放進了懷里;一個我也是吃了少半個,剩下的要帶回家去,家里還有妹妹等著吃呢。
包子是素白菜餡的,鹽放得不多,油放得更少,一點油味也沒有。
回去的路上,一離開會場的燈光,什么也看不見,人們把這樣走路叫摸黑,大意就是摸著黑走路吧。可黑又不像墻壁能摸到,腿腳不好的就會摔跟頭。
快到家時,一條狗也許是看見我手里的包子了,兩眼發綠地追上來,沖我的手就咬了過去。我一躲,那狗沒有吞到包子,卻咬到我的手腕上。咬得那個重,感覺手腕子都要斷了。姥姥忙一彎腰,那狗以為姥姥要拾磚頭打它呢,掉頭跑開了。
回到家,手腕處已經不流血了。姥姥又燒了一團棉絮,燒成灰,敷在傷口上。后來傷好了,傷口卻留了下來,現在我挽起衣袖,都能看到那有一排狗的牙印,半圓形的,像個月牙。
等忙完了我的傷口,姥姥掏出懷里的包子,妹妹在燈下看了半天也舍不得吃。后來,她叫上姥姥,走出屋來,抬起頭,看著黑乎乎的天空,問姥姥,星星呢?姥姥說,星星睡覺去了。妹妹不依,非要讓姥姥找星星,她說要唱著歌吃那包子。
姥姥被妹妹纏得沒法,就說,你先吃了,吃了再唱,星星就被你吵醒了,它就會在天上睜開眼睛,讓你看它。
妹妹早餓壞了,多半個包子三口兩口就咽了下去。她還沒吃飽,就瞅姥姥。姥姥就問我那半個包子呢,我以為帶回來了,在家里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姥姥扭頭就往門外走,說,肯定是掉路上了,可別讓狗吃了去。
姥姥出去找那半個包子去了,妹妹跑回屋,湊到油燈前哼歌:“天上布滿星,月牙兒亮晶晶,生產隊里開大會,訴苦把冤伸……”
唱到這里她突然不唱了,問我舊社會什么樣。
我說,萬惡的舊社會,人吃人呢!
妹妹問,吃誰了?
吃誰了?訴苦的人沒說,我怎么知道呀。
但有一點我記得特別清楚,我丟掉的那半個包子姥姥沒有找到,我記得姥姥回來后總說那句話:“肯定是被那狗吃了。因為那狗沒跑開。”
還有就是第二天,下了一場雪,雪很厚,我家放柴草的棚子都被雪壓塌了。
姥姥看那那雪,就猛得嚷了一嗓子:“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抬頭老婆低頭漢
在農村有一句話,叫抬頭老婆低頭漢,說這樣的人最要強,最好別惹。
抬頭走路的婆娘見過兩個,一個是寡婦,另一個是村干部的老婆。
村干部的老婆相貌還算漂亮。那時的村干部權力大,什么記工分呀、分糧食呀、還有干什么樣農活呀、推薦上大學、當工人等,都是村干部說了算。誰不給村干部老婆一張笑臉呀。所以,村干部的老婆最有資格抬頭走路。
寡婦男人活著時,只聽說這個人嘴特別饞,經常自己偷著做好吃的。
人們上地里干活去了,就見她家的煙筒冒煙了。那煙淡淡的,不像做飯時那煙冒得那么濃,那么聲張。此時,那煙也仿佛見不得人似的,有點虛虛的,還有一點慌張,在風中一飄,就散去了。
有的就說,偷著做飯,不敢用大火,必須是小火,這樣煙筒才不會冒煙,或者少冒煙;燒火用的柴,也必須是干透了的。
農村人最瞧不起偷吃的人,所以就笑話她,說有一次趕集,她想去集上用雞蛋換油條吃,在褲兜里偷偷裝了兩個雞蛋,那時集上人多,擠過來擠過去的,等她擠到炸油條的攤前時,雞蛋被擠爛了,蛋黃蛋清流了一褲子。
聽她的鄰居講,等她男人上工走了,她做過面條,也攤過面餅。鄰居說,那香味從院墻那邊飄過來,就像長了小鉤子,香得勾魂了。
那時生產隊秋收時為了搶收莊稼,管飯,飯隨便吃。
選順風的一邊,把大鍋安到地頭上,這樣一是煙不嗆人,還可把飯的香味飄給在田里干活的人們,半上午就開始燒火做飯,快到中午那飯香味就濃了,隊長嚷一聲,加把勁,到了地頭就可以吃飯了,敞開吃呀。
那時管的飯就是小米綠豆干飯,也不炒菜,吃得嬌氣的會自己在家帶一點咸菜,下飯吃。
因為這飯是隨便吃,很多人就想吃一頓飽三頓。寡婦的男人吃撐了,人們用一輛平板車拉他去醫院,我在遠遠的地方看他在車廂里坐起來躺下,躺下又坐起來,難受得直叫。到了醫院,給他洗胃,洗了半天也沒救活。
那天,他的死訊傳回村里,村里的街上突然有一個旋風刮起來,一直刮到他家去了。有人就說,那是她男人的魂先回來了。
寡婦的男人我沒印象了,據說長得挺丑的,人們叫他丑四,大概是他身上的丑有四樣吧:眼上沒有眉毛蓋,門牙長到嘴唇外,胳膊短過褲腰帶,兩腿走路一腿邁。
人們都說寡婦懶,也有人說她身子有病才嫁丑四的。丑四死后,也沒留給她一兒半女,她又干不了重活,就去地里偷糧食。
偷糧食的人也不只她一個,還有其他人,那次大約捉到了六七個吧,就讓這些偷糧食的人帶上偷的東西在本村的大街上來回走。寡婦那天偷的是黃豆棵,也不知是誰把黃豆棵掛到她的脖子上。
別人在街上走時都是低著頭,盡量走在后面,她卻走在第一個,還說:“誰不偷東西呀,不能餓著等死!”
寡婦沒了男人,據說后來特能干,還能吃苦,也不偷吃了,把自己的家搞得比有男人的還氣派。
低頭漢只見過一個,常年穿一身黑衣服,走路靠墻根走,總低著頭,逢人也不說話,人們也不和他說話。
我忘記他有多大年紀了,我曾去過他家玩,也沒見到過他,也許那時他在家,躲起來了。
他的老婆是一個白白凈凈的女人,脾氣也好,好像還送給過我吃的,好像是紅薯。
他家老村宅子里有一棵很大的香椿樹,好像她還送給過我一把香椿,回到家剁碎,拌上鹽當咸菜吃了。
這樣的人怎么會最能干,最難惹呢?
只有一次我見他站在了很多眼睛面前。那天他家一只雞跑丟了,他老婆讓他去房頂上嚷一下,問誰家見到那雞了。他站在房頂子上就是不出聲,他老婆在院子里用一根手指指著他說:“你嚷一聲,還有人會吃了你呀!”
天很陰,風也刮起來了,人們說風是雨頭,怕是要下雨了。話音剛落,就有銅錢大的雨點打在人們仰著的臉上,接著就是一道閃電打在他的身上,他就一下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老蔫被雷劈了!”看熱鬧的像炸了窩似的,紛紛涌進院子里,搬梯子上房,把那個男人救下來。
還好,那男人被救下來還能喘氣,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那男人能說話了,說腳疼。有人把他的鞋子脫下來,發現他的鞋底被雷擊了一個洞,洞那兒有個鐵圖釘,有人就說是圖釘救了他,雷劈下來時,雷電通過圖釘導入地下了。
被雷劈過之后,他就更少出門了。
他家有兩個兒子,脾氣不隨他,學習也用功,恢復高考那一年,都考上大學了。一家同時出了兩個大學生,人們就猜他很少出門的原因是他看清了世道要變,在家教孩子用功學習呢。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是從大城市里下放回來的,肚子里墨水深著呢!
他低頭走路人們也找到了最好的注解,他是在想他的學問呢。真是深藏不露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