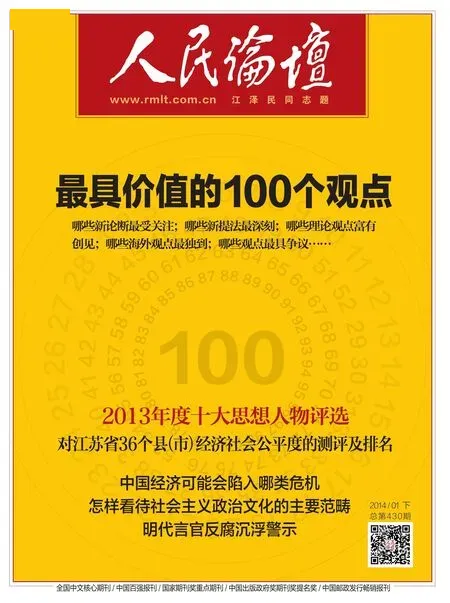西部農村社區建設需求分析—以四川省蓬安縣H村為例
李 梅 何代忠
H村社區建設的需求概況
生存環境(基礎設施和人居條件)的改善。據調查:95%的四川省蓬安縣H村居民強烈要求加強鄉村道路建設,認為交通不便嚴重制約了該村經濟發展,妨礙了日常交際活動;68%的居民希望房屋改造,告別老式低矮潮濕的椽木結構簡易房,住上寬敞舒適的磚混結構樓房;32%的居民希望美化現有住房,達到房屋封檐座脊,門窗刷漆,墻壁刷白,室內室外及院壩硬化,改造廚房(灶臺、碗柜、案板瓷磚化),廁所衛生化;100%的居民要求戶與戶之間通水泥板路;100%的農戶希望每戶擁有一口沼氣池;居住在平壩區的所有居民都希望使用自來水,居住在山區的農民都希望擁有一口手壓機井。
強烈要求提高自身綜合素質,特別是在農業科技實用知識方面。全村255戶居民中,有98戶(約占總數的38.4%)想成為養蠶專業戶;70戶(約占總數的27.5%)希望成為養魚專業戶;67戶(約占總數的26.3%)希望發展成為水果專業戶;20戶(約占總數的7.8%)打算成為養豬專業戶。所有居民都一致表明想進一步了解現行法律法規、政策方針等各方面的知識。
對社區健康文化生活的渴求。217戶居民(約占總數的85%)表達了對家庭及本社區文化娛樂活動的極度不滿意,非常想改變自己及家庭的“原子”態。該村幾乎沒有任何公共文化娛樂設施,只有一個村民自組織的、即將解體的鑼鼓川劇團;家庭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看無線電視,但接受到的電視頻道偏少,圖像、聲音效果極差,其次是打撲克或麻將,有的甚至賭博;走親訪友極少;也沒有電影可看。因此,該村居民強烈希望能夠安裝有線電視和程控電話;也希望隨時(特別是農閑)能夠觀看、參加健康有益的社區文化娛樂生活。
極為關注個人及家庭的未來發展,特別是子女教育問題。全體居民都想了解與“三農”有關的現行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都希望社區生產功能產業化,獲得比較豐足的物質基礎(貨幣),從而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接受良好教育,借此躍出農門,但該社區因絕大部分青壯年外出打工,而老一代由于自身文化素質低下,心有余而力不足,“隔代撫養”致使家庭教育缺位,年幼一代的綜合素質前景使人十分擔憂。
H村社區居民物質需求滿足的可行性分析
社區擁有的資金量少而不均,且以實物性為主。據《蓬安縣興旺鎮農村經濟情況統計年報表》(2001~2010年)的統計數據來看,該村沒有村辦企業,主要產業以傳統種植業為主,與之配套的畜牧業以蠶桑、生豬為主。H村2010年度的總經濟收入總額為250萬元 ,按收入行業來看,農業收入121萬元(占總額的48.4%),畜牧業收入105萬元(占總額的42%),二者合計占居民收入總額的90.4%;扣除生產費用及管理費用(總額為98.9萬元)以及農業稅等其他上交稅收(6.1萬元)外,居民凈收入總額為145萬元,再加上部分居民外出的勞務收入56.2萬元,以及其他轉移性收入0.76萬元,整個社區2003年度實際可支配資金總額為201.96萬元,該村人均純收入2198元,與全縣收入水平基本持平。不過,該社區居民內部有一定程度的階層分化,在全體255戶居民中,其中純收入625元以下的居民戶53戶(占總戶額的20.8%)、人口170人(占人口總額的18.5%)。
公共積累資金名存實亡。從經營形式受益來看,該村2003年度的經濟總收入(250萬元),居民家庭經營收入為249萬元,村集體經營收入1萬元,即99.6%的資金集中于社區居民手中,集體經濟形同虛設。自從1994年從經營形式受益來看,該村2003年度的經濟總收入(250萬元),居民家庭經營收入為249萬元,村集體經營收入1萬元,即99.6%的資金集中于社區居民手中,集體經濟形同虛設。自從1994年以來,我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及隨帶而來的“村財鄉管”,使得鄉鎮對村一級社區的財政控制的更緊了,鄉村社區的自主空間更小了。“分稅制”政策不僅加重了農民負擔,而且通過以“吸管”和“噴灌”為特征的公共財政將財力層層向上集中,越在上層越富足,但在支出上卻是逐級向下滲透,越是下級能得到的財力越小。鑒于以上原因,導致鄉村社區外在人文環境的急劇惡化。H村的外在生存人文環境概莫能外,村財政常年處于赤字狀態,目前債務累計總額為3萬元。
生產資料匱乏。以H村居民最主要的物資資源—土地為例(以蓬安縣的平均水平為參照標準),該村幅員面積1.3平方公里,只有該縣平均水平(2.6平方公里)的1/2;截至2003年底,該村實有耕地面積727畝(其中水田601畝、旱地126畝),人均耕地面積0.79畝,也低于該縣的平均水平(0.86畝)。據該村文書唐介紹:該村糧食畝產在400kg左右,只能基本解決吃飯的問題;養殖業都是在單家獨戶中進行,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要,沒有任何規模效益;蠶桑雖然是該村的主導產業,但零星分散,不集中成片,管理粗放,生產、管理成本過高,效益比較低下,并且全村現有桑樹(6萬株)中有3.1萬株已嚴重老化,急需更新優化品種。
H村進行新型社區文化建設的優勢資源
傳統鄉村文化中的理性成分保存較完整。雖說H村享受的物質生活水平較低,但民風淳樸。根據項目組采訪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以及村民的介紹,我們發現該村居民的農耕文化還比較濃郁,村民們從事著千百年來未曾改變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下地干活,養豬、養雞、養鴨、種桑樹養蠶;夜晚,有條件的人家看看電視,但由于電視的接收效果不太好,大部分農戶家中小小的黑白電視機往往只是個擺設。
梁漱溟對于中國鄉村文化的積極功能做出了精辟的概述,他認為中國是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的社會,在鄉村中從理性求組織有許多合適之處。第一,對農民的閑時自然的性情特征非常適合理性的開發;第二,農民一生面對的是生物,充滿了生趣,自然培育出活潑的性情;第三,農民常年種植的五谷必須與自然的時節相一致,急忙不得,所以養成一種從容不迫的神氣,他的從容來自于他對接觸的一切事物的感悟而產生一種有藝術味道的文化和人生;第四,鄉村通常以家庭經營模式來從事生產,自古以來培養人的性情和給予人安慰的最佳地方就是家庭,這與情誼化的組織密切相關。以上四個方面都與遵從理性而需求組織有關;第五,鄉村人有很濃的鄉土觀念,容易引起地方性公共觀念;第六,在鄉村仍然具有一些中國固有的社會特點,它是一種情誼化與倫理化的社會;第七,我們應將社會的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的重心放在鄉村,當然,講從鄉村人手,并不是完全拋開都市;第八,要養成新的政治習慣,應從鄉村著手,便于建成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
豐厚的傳統文化資源。一是濃郁的傳統文化背景。南北朝開始該地始設縣,名叫相如縣(公元507年),以此紀念漢代大辭賦家司馬相如,后置蓬州、蓬安縣。漢司馬相如、唐元稹、宋蘇軾、周敦頤等曾來蓬安,南朝梁肖拻、唐顏真卿、李瑀、明李道傳、清姚瑩等名宦曾被貶謫于此。加上一些開明官吏如宋王旦、清周天柱、洪運開、高士魁、龍旭等都注重倡學興文,造就了本地深厚的傳統文化資源。
二是可供開發的文化、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中傳統節目繁多,該村的傳統文化節目有:川劇、腰鼓、花鼓、金錢板、快板、京劇、嗩吶等文藝節目。文化資源分布結構合理,有會樂器的老人、會演唱戲曲的中年人以及對戲曲十分感興趣的小孩;有自發性文化團體,該村還自組織了一個鼓鑼川劇團,在本社區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文化資源開發較早,且卓有成效,據村民介紹,他們以前演過《沙家浜》、《丁佑君》、《智取威虎山》,還演過《奇襲白虎團》。除了到各鄉、各村去演出外,還到蓬安縣城去過。對該村進行文化建設有利的社會資源有:65歲的雷鋒戰友,考上大學、大專、中專的人家,外出入伍參軍的青年,在外地工作從小在村里長大的人們,更有開始回鄉的外出打工人員,還有從市人事局下派鍛煉的高素質村支書。
三是可以利用本地的文化資源。民間工藝美術資源豐富,如紙扎、剪紙、雕塑、刺繡、面塑等。民間舞蹈多姿多彩,主要有龍燈、獅舞、蚌舞、彩船、蓮宵、車燈、高蹺、火彈子等。戲劇資源也比較豐富多彩,主要是川劇(板凳戲、圍鼓以及傳統折子戲),其他還有木偶戲、皮影戲、燈戲、歌劇、話劇。曲藝主要有說唱兩種形式:說,包括評書、方言、相聲、對口詞、三句半;唱,包括四川竹琴、清音、盤子、花鼓、金錢板、蓮花落等。
潛在的自組織資源及其萌芽。該村潛在的自組織資源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最明顯的是,為了填補因國家文化機構在鄉村領域的撤離而造成的文化真空,該村居民自發組織自己的文化團體,在閑暇、節假日無償地給鄉親們增添一些快樂;潛在的自組織資源基礎雄厚,在全村255戶居民中,有98戶(約占總數的38.4%)想成為養蠶專業戶;70戶(約占總數的27.5%)希望成為養魚專業戶,67戶(約占總數的26.3%)希望發展成為水果專業戶,20戶(約占總數的7.8%)打算成為養豬專業戶,依托未來的農業的農協會開發積累自組織資源。
村民自治為村民的自組織資源的積累奠定了一定基礎、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H村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中嚴格依照《村委組織法》辦事,完全做到了由村民直選,得到督導組的好評,有利于該村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合作、自我服務等“公德”意識的提高,不斷消除傳統文化中“私德”等消極因素的不利影響。
比較寬松有利的鄉村社區建設環境。從整體水平來看,H村與絕大部分中國中西部鄉村基本一樣,都處于“吃的夠,穿的也有,就是缺錢花”剛剛溫飽狀態。人均土地面積較少,勞動量不大,閑暇時間相對較多(如果能夠系統合理地安排時間的話)。鄉村養殖業以及外出務工經商為該村能夠積累一定的現金資源。該村委會成員因由村民直選產生,具有居民認可的權威性;由于村支書是下派鍛煉的,素質較高,特別想把該社區建設好,村委會與村支書的目標一致,能夠為通過合作的形式培育該村居民的自組織資源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服務。
鄉鎮文化機構在市場經濟中全面癱瘓,鄉村文化生活出現真空。據該縣文化局的何局長介紹,雖說每個鄉鎮都有文化中心,實際上是廣播站合并了文化站,原有文化站活動場所蕩然無存,全縣共有文化干事28人,50%的人無任何文化專長,其主要精力放在駐隊上。也就是說,基層文化機構多數(包括興旺鎮)處于“三無”狀態(無房子、無票子、無專才),根本沒有能力來滿足解決溫飽后的鄉村居民不斷增長的文化生活需要,為民間文藝團體的生存發展騰出了巨大的擴展性空間。
通過文化角度建設H村的問題與建議
H村文化建設雖說具有一定的資源優勢,但一般都處于欠缺、萌芽或待開發狀態。由于該社區內部居民的綜合素質比較低,自我認識不到位,不能從整體、系統的角度來整合社區內部資源,需要借助外界力量共同進行社區建設。即由于缺乏居民合作參與性的人文背景,H村無法有效整合內部的文化、社會、經濟資源,建設新人文背景下的鄉村社區。
缺乏對本村生存、發展外在環境結構的深度理性認識。建議開辦鄉村文化活動室,培養學習習慣,重新整合當地居民的本體文化價值觀。在具體做法上,可以采用KSSP在印度克拉拉邦“人民科學運動”的某些做法。在社區建設自愿者的幫助下,在鄉村居民之間用他們熟識的語言來宣傳科學知識(關于人和社會規律的知識),先從講解、展覽、傳播科學信息等開始,然后建立科學知識協會,開展培訓促進居民間的互動式學習,后來再發展到對環境、發展、健康、教育等一般問題的討論和關注。認識到以市場文化為核心的“現代”社區建設模式的局限性,挖掘、整合傳統鄉村文化中的優秀資源,從而找到適合本社區建設的最佳途徑。
缺乏社區歸屬感,合作精神不足。首先,建議以鄉村經濟合作化(農業產業化)促進社區居民的合作意識。通過幫助該社區居民成立養殖業協會,再造該社區的組織機制,如發展老人協會、婦女協會、各種業緣、趣緣團體等,為該社區提供良好的合作機制和生活預期,讓居民以長遠預期取得短期行為,從而充分發揮民主自治的作用,增加居民的合作意識,提高他們的合作能力,通過生產生活互助合作,來提高他們單家獨戶提供不了或提供起來不經濟的、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合作方式還可以增加他們生產生活本身的樂趣,培養、提高“公德”意識。
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借鑒樂施會在云南省祿勸實施項目的經驗。H村可以建造文化設施及采購器材為載體靈活運用CO機制,即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采取一種“賦權”模式。賦權模式就是項目辦工作人員和居民一起商量文化設施該建在哪里,怎么建,建了怎么管,誰來管,這些事情都讓村民來決定,如果有分歧就多次討論、辯論,意見無法統一就投票解決。樂施會認為鄉村居民是解決社區建設問題的主體,各種機構只是社區發展的協作伙伴。只有以社區為主體的發展,全體社區居民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社區發展才有希望。因此,參與式發展模式才是有生命力的,包辦代替式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其次,建議充分開展適合鄉村居民生活趣味和欣賞水平的文娛活動和制作藝術作品。讓農民自編自演自我欣賞自己的文娛活動,開展與當地勞動生產密切相關的、農村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為村民享受自己生活的情趣和品味生活的意義提供一個平臺,積極組織并加以引導,增加農村生活的意義,提高村民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
最后,為鄉村節日或慶典建立專門的場所,促進村民形成主人翁意識,并且村民自己撰寫村志、村史,為居民在變動的世界中尋根,讓他們感到本體性安全,共建社區共同體意識。不僅可以大大提高鄉村居民行動的未來預期,有效限制本社區內部的不良行為,而且可以從本體上讓本社區居民感到安全,心靈上找到安慰,從而減少他們的擔憂與焦慮。
社會活動較少。建議開展大量的社會活動,提高社區居民的閑暇生活質量,使他們的農閑時間生活變得充實而有價值,生活本身蘊含的意義更加豐富。主要通過舉辦形式多樣的社會性活動(包含經濟型合作和文體活動)。例如,組織棋類比賽或歌詠比賽,不僅能有效提高競賽雙方內部的合作能力及組織能力,同時能提高村民的一致行動能力,而且會為優勝群體帶來集體榮譽感;又比如,組織不同村小組或不同群體之間的對抗性競爭游戲,可以為優勝者提供榮耀資本。讓不同層面的鄉村居民自己組織參與社會性競技活動,使鄉村民從溫飽生活中更快地進入到精神享樂和社會福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