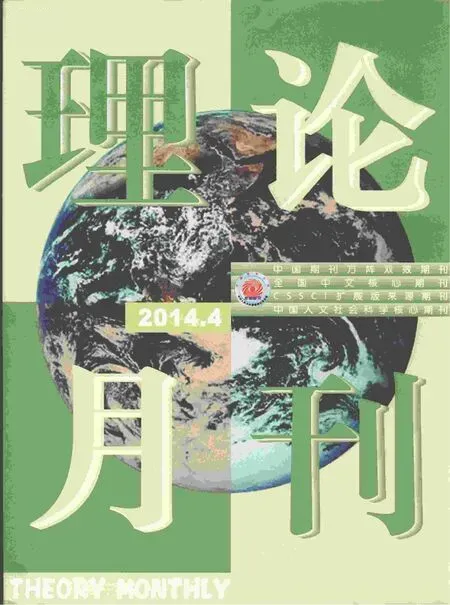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生成邏輯*
李國鋒
(山東師范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原始文明:人與自然“原生態性”的和諧
文明是反映人類社會發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水平與整體面貌。從二三百萬年前人類在地球上誕生起到一萬年前農業、畜牧業的出現,歷時兩百多萬年的時間里,或者說在人類產生以來的99%以上的時間里,都可以稱為采獵文明時期。在漫長的歲月里,盡管人類心智的發展已經可以借助于簡單的勞動制造簡單的工具,如骨器、石器、弓箭等,獲取其所需的生活資料,并利用某些自然力如火等,使人類獲得了一種不同于動物本能的生存與發展方式。但此時人類僅僅只是大自然整體中平等的一員,人類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主體地位,人的生存狀態和其它動物還沒有顯著區別。對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明確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1](P374-375)“我們連同我們的肉、 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2](P384)
在這種狀態下,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力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依靠自然界賜予的“現成產品”勉強維持生活。在這一時期,人類還基本上只是自然生態系統食物網鏈上的一個環節,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只是通過直接作用于食物網鏈而反饋到生態系統中。因此,那時的地球是“綠色”的,但并沒有真正的“文明”可言,人類社會還處于原始的野蠻蒙昧階段。人與自然的關系可謂是處于一種混沌同一的關系之中。因此,面對著錯綜復雜、變化莫測的自然界,人類既敬畏又恐懼,原始圖騰和自然崇拜就應運而生。人類把自然視為無窮力量的主宰,視為某種神秘力量的化身,通過采取宗教儀式來慰籍心靈、解釋自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說道:“在原始人看來,自然力是某種異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東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經歷的一定階段上,他們用人格化的方法來同化自然力。正是這種人格化的欲望,到處創造了許多神”。[3](P672)馬克思在談到人與自然關系時也敏銳的觀察到:“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1](P81-82)不難發現,在整個這一時期里,人類是非常被動的,對自然的認知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對自身賴以生存的食物生產過程也沒有多少干預,人們的消費水平也非常低,產生的廢物基本上能夠被自然系統自行消化,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
總之,在原始文明或漁獵文明時期,人類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統治,主要依靠采集和漁獵兩種物質生產活動,抵御各種自然力的肆虐,可以說,這一時期人類懾服于自然威力之下,是自然的奴隸。在人類的視野里,自然成了主宰,成了某種神秘的力量。對此馬克思談到:“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1](P81)人類的生存完全依賴于自然,歸屬于自然、融化于自然的混沌,人與自然之間形成了原始的協調、低層次的和諧關系。
二、農業文明:人與自然“合生態性”的平衡
人類并非簡單地歸屬于地球生態共同體,人類還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殊性:是唯一依靠理性知識生存的物種,唯一具有批判能力、具有自我概念、具有世界觀的物種。人類要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實現自身的生存和全面發展,必然要面臨和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矛盾,從而出現自然界的人化過程。
大約在一萬年前,隨著文字的產生,這種純粹“動物式”的關系慢慢注入了人化自然的主體因素。自然界不再是脫離人的實踐活動,人類不再僅僅從客體的、直觀的意義去理解的純粹自在的自然界。從自身的需求出發,人類通過大量的砍伐、焚燒森林和其他途徑來開墾土地發展農業,人類進入了農業文明時期,“農業是真正意義上的文明”。于是,作為“文明”進程的一部分,那種曾支持其文化壯麗的生態系統,被看作是“荒野”,需要被加以“馴化”,直至它們成為能夠為經濟發展服務的“自然資源”。正如美國學者弗·卡特和湯姆·戴爾在《表土與人類文明》一書中所說:“文明之所以會在孕育了這些文明的故鄉衰落,主要是由于人們糟蹋或者毀壞了幫助人類發展文明的環境”。恩格斯在描述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的生產活動時,曾這樣描述道:“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2](P383)這意味著人類的行動已經開始給生態環境帶來十分消極的影響,客觀上破壞了自然和環境,致使森林消失、河流污染、一些物種消亡,人類自身生存開始受到威脅。
綜觀農業文明,我們不難發現這時只是造成自然界的局部斑禿和傷痕,并沒有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從整體上講,農業文明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保持了人類與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這時的人類還是覺得自己只是諸多物種中的一員,他們仍然把自己理解為自然世界的組成部分,是 “地球母親”的孩子。因此他們只是“適應”了自己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許多人都力求避免以一種可能會破壞維持人類生活能力的方式來開發自然環境。其結果就是,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們以一種“合乎生態”的方式生活其中。當然,這只是一種人類能動性發揮不足與對自然開發能力單薄相聯系的生態平衡,此時的人類無法擺脫異己的、支配的“人的依賴關系”,因而不是人們應當贊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三、工業文明:人與自然的“反生態性”的疏離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喜歡將生態危機的根源追溯至遙遠的古希臘,認為那時的人與自然分離的思想就已經預示著:生態危機的產生乃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工業文明的興起,“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一起變革了整個自然界,結束了人們對于自然界的幼稚態度和其他幼稚的行為”,[4](P241)其結果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走向疏遠。換言之,在二元論哲學的影響下,這一時期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成為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人們不僅逐漸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感,甚至把自己變成了神性的無畏的“上帝”。
就工業文明的現實形態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疑是其典型代表。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論述大工業和大農業生產時,就揭露了物質變換過程對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明確指出:在人與自然之間,出現了“無法彌補的裂縫”,即出現了“新陳代謝斷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5](P878)“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所起的作用則微乎其微。”[6](P697)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也這樣告誡人類:“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2](P383)不難看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開端便使人作用于自然的實踐活動有了目的和形式的質的變化,致使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加劇了人和自然之間的矛盾。
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的視野中,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在本質上是對立的。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認為:“文明與自然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相互對立的兩個領域,這種對立不是表現在每一實例之中,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在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之中”。[7]詹姆斯·杰克遜在對“生態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進行闡釋時,也非常明確地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地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民主資本主義的經濟是與自然的保護不相容的”。而詹姆斯·奧康納則非常明確地指出在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中實際上存在著“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雙重危機,后者清晰地表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必然性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更近一步,“在高茲看來,生態危機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和重要特征,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讓位于影響范圍更大的生態危機”。[8](P17)這些學者從不同的視角,批評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反生態本性。究其根源,就在于資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場競爭的壓力注定導致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生態環境問題,而且必然導致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輸出”或“轉嫁”。
至此可知,工業文明雖然是在人類改造自然中逐漸生成的,然而其本身并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類活動的結果,這種“自然”狀態并不“必然”進入文明狀態。恰恰相反,工業文明中超越自然內在限度的生產活動在肯定人類在自然界中地位的同時也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加速了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異化和分裂,引發大規模的生態危機,不僅導致人與自然的關系漸行漸遠,最終會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
四、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追求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
關于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馬克斯·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中明確指出表現為“人類的理智戰勝迷信,去支配已經失去魔力的自然”。康德也以人類是否從“大自然”當中解放出來作為社會文明與否的標志,認為人類的“成熟狀態”就是“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人類為了永續發展,必須要超越傳統文明及其發展模式,探尋一條新的文明模式和發展道路,綠色、循環、生態發展正成為人類發展的新趨向。以謀求人類的共同利益、追求人與自然共同福祉的生態文明,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處共榮,樹立的是一種新的統籌兼顧的可持續發展觀,這是我們在后現代文明時代背景下對人類文明未來可能狀態的激情想象,是對以往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生產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這種超越意味著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轉向,指明了人類未來可能的發展道路。
如果說農業文明促進了封建社會的產生,工業文明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興起,那么生態文明“必然”而且“能夠”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面發展。正如美國生態社會主義者巴里·康芒納所言,“在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生態的迫切需要之間的基本關系方面,社會主義制度有超越私人企業制度的優越性”。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理念蘊涵著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關懷——生產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經濟建設是有計劃的而不是盲目發展——因而可以對工業文明時期資本與市場的擴張本性與經濟理性本性進行必要的限制,更能體現并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未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是追求人與自然共同福祉的文明,蘊含以下含義。
首先,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以中華傳統和諧文化為理論支撐。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中有關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思想至今仍閃爍著生態智慧的光芒,為實現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與思想源泉。對此,美國生態經濟學者克利福德·柯布認為,要想實現生態文明的目標,“東亞人擁有一個有利條件”,即“東亞人更關注整體,而西方人僅僅看重部分”,“這種特征已經由一種儀器得到證明”。[9](P184)中華傳統文化在價值理念上強調“天人合一”、“民胞物與”,把宇宙看作一個有機整體,在這個有機整體中,人類追求與天地萬物之間的和諧關系。《周易·條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即是“天”、“地”之間最偉大的事情就是愛護生命,人與自然萬物都是“天地合氣”的結果。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中談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這里“天”就是指的自然界,“生”是自然界的基本功能。如果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在此強調的就是自然界是人類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與天地本為一體,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相通、相類和統一。北宋的張載在《正蒙·乾稱》中認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認為人和萬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無阻隔,一切為上天所賜,主張愛一切人、一切物。”顯而易見,中華傳統的生態價值觀是一種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尊重自然規律、保護自然景觀及動物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因此,以中國傳統“和諧”文化為價值支撐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遠遠優于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生態保護,造成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態問題的工業文明,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
其次,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以社會主義制度為現實依托。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沖破“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對生態危機解說的藩籬,將生態危機難題歸結于資本主義制度。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總結道:“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把矛盾置于資本主義生產與整個生態系統之間的基本矛盾這一高度來認識”。[10](P273)印度籍德國學者薩拉·薩卡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指出“可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可持續增長”所依托的理論假設都不過是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確信無疑的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體系正在走向失敗”。不僅如此,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所說,“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11](P385)也就是說,無論是對于生態危機成因的解釋還是對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創建,都應始于一種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新型的社會制度。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包含著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從而使生態文明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屬性。
再次,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以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為價值引領。生態文明強調人是價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發展必須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強調以人為本,堅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倡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將人類的長久生存建立在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基礎之上,是在“解構”工業文明的范式中產生的一種新文明,實現了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原則的完美契合。以中國為對照,從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第一次使用“可持續發展”概念到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多次重申和強調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從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 “建設生態文明”到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號召“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這些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理念的一次次升華,不僅彰顯出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認識的深化,更凸顯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戰略高度。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倡導一種比工業文明更加符合生態規律與原則的生存生活方式,強調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與生態保護相協調,把發展的速度和生態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能創制不同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態環境難題解決思路與方式,能更有效地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難以克服的諸多生態環境難題。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8]Andrew Bard Schmookle.Fool’s Gold [M].New York:HarperCollins,1993.
[9]克利福德·柯布.邁向生態文明的實踐步[A].生態文明與馬克思主義[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10]Ager Ben.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Californian:Goodyear,1979.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