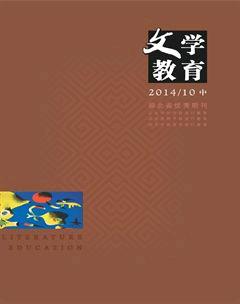中國文明的“物化標準”演變歷程審視
[摘 要]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各國考古學者都嘗試以某種物質實體的出現來衡量人類何時進入文明階段。這其中的主流就是試圖架構一個關于文明的大范圍適用的客觀物質判斷標準即文明的“物化標準”。時至今日,盡管有許多的標準被提出,但沒有一個標準能廣泛地為所有人認同。本文嘗試考察中國學界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所提出的文明物化標準的變化歷程,從而反映中國學界,尤其是考古學界對文明起源認識的變遷。
[關鍵詞] 文明起源;物化標準;考古學史
中國文明的起源對于學術界來說是一個永久熱門的課題。以具有西方色彩的,從社會發展角度所詮釋的“文明”詞義被引入中國以來,學界對此有過長時間的激烈討論。時至今日,無論中外學者均對文明起源這一課題有了較為充分的認識。故在詮釋時已多從文化、社會等屬于“人”這一形而上的層面切入,而對于物質層面的關注比較少,即使論及,也多是就事論事。當然,這并不是錯誤。正如一些學者所言,文明的發展是逐步的,很有可能根本就沒有什么明確的物質表現;或是各地環境不同,文明亦無統一標準;又或者文明的起源是復雜的,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所以單是以物研究文明會造成人類史、物質技術史的割裂……這些都代表了學界目前理性的思考結果。但具體到考古學語境中,由于是一種以物為對象的學科,首要的關注材料自然是物質。
究竟什么能標志人類邁入文明?對于中國來說,“文明”一詞的傳統意義在于文治教化,側重于對行為和舉止的“禮教”要求而不具有社會形態與技術進步的內涵,距離今日所謂文明的概念有所出入。而具備表示人類社會的總體發展階段意義的文明概念的出現,可追溯至英國17 世紀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于《利維坦》(Leviathan)中所提出的相對于自然主義的國家主義形態。由此可見現今的文明一詞更多是西方文化輸入的產物。所以,對于文明起源這一問題,中國學術界的科學思考顯然至早當在梁啟超、孫中山等人將西方文明觀傳入中國以后才正式開始。
而在科學考古學傳入中國前,在中國學界,對于可能是文明起源的這一時期的話語權是被古史學者所壟斷的。當然,他們研究的古代史籍本身就可作為探討此問題的一個物質標準,問題是,在當時由康有為所始的疑古之風盛行的學術背景之下,又有誰能對古史的性質做一個明確的判斷呢?既然無從判斷其真假,那么以史學典籍來作為劃分文明時代的標準的科學性就無從談起。所以這個問題納入科學討論還應該有一前提,即是中國科學考古學的出現與興起,尤其是殷墟等地的考古材料的重見天日。
當滿足了以上兩個條件,文明起源的定義隨之明晰,而材料也逐漸充實。這一問題即具備了討論的前提。在國內首先闡發對這一問題的考古學看法的人是郭沫若。在其1929年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郭沫若將商定作氏族社會的下線,遲至周,中國才建立國家邁入了文明時代。郭沫若的觀點默認了國家作為文明標志物在文明起源進程中的重要性,甚至是唯一的參照。但是應該注意到的是,其一,此時郭沫若提出的僅僅是文明的標準而非物化標準,其二,郭沫若在書中大量參照與引述了恩格斯《家庭國家私有制的起源》中的觀點。事實上,這些源于摩爾根、恩格斯著作的觀點,基本上影響了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學界對于該問題的看法。
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恩格斯就文明的標準提出的一套完整的體系:將歷史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最早是1877年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提出的,爾后馬克思為其做過專門研究并見于其筆記。隨后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筆記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于1884年完成《家庭國家私有制的起源》。因而恩格斯在一些地方,包括人類早期歷史的劃分上沿用并深化了摩爾根的觀念。具體到書中,恩格斯將氏族崩解,國家產生作為文明產生的標志。這一界定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它直接將文明同國家聯系在一起。但我們也應注意到恩格斯在表達在國家產生前的諸多變化,如第三次社會分工與商人的出現,奴隸制度完善等,也采用了“為文明所固有”的修飾語。所以,雖然恩格斯將邁入文明視為一個明確的節點,但他也承認存在一個特定的文明化進程。這些在國家產生前的諸多變化也應列入文明標準的考量。由于國家產生并不能直接的被考古學觀察到,在恩格斯論述的基礎上,我嘗試總結了與恩格斯所提到的與國家產生前的變化相對應的物化標準,主要:物質占有的極端不平衡,貨幣的出現,文字應用于文獻。
謝維揚先生將1974年二里頭遺址的發現視為國家起源探索一個重要的轉變。但是從關于二里頭遺址的著作來看,這個發現在當時的時間意義遠遠大于其所展示的不同以往的文明形態方面的意義。以至于僅僅在于它把中國國家產生的時代前推了一個朝代。對于文明起源物化標準依舊糾結于可見的等級分化與文字上。
而與二里頭遺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新石器陶文,尤其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的發現。這個發現一方面落在當時只關注可見的等級分化與文字的國內學界的視野內,又出乎意料地在時代上將可能的文明到來時間大大提前。這個矛盾性促使一些學者重新思考起原先已成不刊之論的文明起源問題。在1974年關于大汶口遺址的報告出版以后。1977年唐蘭先生發表《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雖然在衡量文明的物化標準上依舊沒有脫離傳統窠臼,但已經有不把文明起源同國家出現等同起來的傾向。蔡鳳書、邵望平對大汶口文化、牟永抗、魏正瑾對良渚文化的研究也將文明提到國家出現之前,主要是以文字為依據。而1979年黎家芳、高廣仁在《典型龍山文化來源、發展及社會性質初探》中將金屬冶煉、設防城址、體現奴隸主意志的饕餮紋列為文明階段的物化標準;孫守道、郭大順在其后的《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中將城堡與城市、文字、農業與水利工程列為標準;田昌五《中國古代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問題》將文字、歷法、冶煉金屬出現定為“文明社會即將到來的標志”。
80年代夏鼐先生《中國文明的起源》的發表對文明起源課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文中夏鼐把文明的物化標準定為都市、文字制度、金屬冶鑄技術。這個標準是參照克拉克洪、丹尼爾提出的文明三要素——文字、城市、復雜的禮儀中心;或是貝冢茂樹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所提出的青銅器、宮殿基址、文字已不能確定。但是毫無疑問,這是把中國文明起源的物化特征放在全球視野下進行比較的思考結果。
對于夏鼐先生所定的標準,許多學者如李學勤、鄒衡均表達了贊同的聲音,并在夏鼐的基礎上有所修訂。這是對于文明的物化標準所見最明晰的階段。但在這一階段,反對者與未得出結論的觀望者也不少。如田昌五。但這一階段,反對只涉及此三要素(或是四要素)與傳統的可見階級分化的關系上,而沒有提出其他的標準。
在此以后的80年代末,蘇秉琦首先轉變了這一情況。蘇秉琦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將中國文明的起源推進到紅山文化與大仰韶文化的晚期。這個轉變的必然打破了夏鼐提出的文明物化標準。根據蘇秉琦在文中的說明來看,之所以判斷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數枝已經誕生了文明的曙光,是因為紅山文化以“女神廟”和積石冢為代表的大型祭祀遺址,制作精良的玉器,在泉護村、陶寺墓葬中發現的帶有禮器性質的陶器。這也可以視之為一種物化標準,但是,他并不意味著文明,而是意味著“我國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發展已達到產生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
事實上如果我們綜合蘇秉琦的多部作品就能看出,他的研究并不是著眼于文明的具體含義的。比如他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概念,而不是沿用之前約定俗成的國家文明概念。他更著眼于思考文明產生的機制。所以,對于他的學說,所謂文明是一個內涵與外延不明確的概念,那么其物化標準更無從談起。但是與此同時,他對文明誕生機制的思考使他將文明的誕生歸因于“古文化的交流”,這是否意味著,這里包含著一個隱含的物化標準:即同時能體現這種交流與社會發展分化的物品或是物化現象?
在此,這個標準的變化引起了一個重要的討論——即文明的起源與文明的形成的辨析。在反對蘇秉琦觀點的學者看來,前推至紅山與仰韶時期的一個問題就是都市、文字制度、金屬冶鑄技術在當時都不成熟,而贊同者亦多沒有否認都市、文字制度、金屬冶鑄技術之于文明的重要性,只是文明不像摩爾根所劃分的那樣由野蠻一躍進入文明,而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從這一角度看,文明三要素只是文明化最終完成的結果。這個問題在蘇秉琦之前已被學界所意識到,但是卻從未將之明確的辨析。究其原因,還是在于之前把階級分化的物化表現同國家起源聯系在一起的緣故。盡管在接下來的時間中,學界又對文明的開端究竟是從它的起源算起還是它的形成算起存在分歧,但基本上都沒有超出此二者的認知。
蘇秉琦留給學界的思考導致了在他的之后,出現了一股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熱潮。這場討論經久不衰以至今日這個課題依舊是炙手可熱。在開頭已經說過,如今學界更傾向于討論這之中的“人”而不是單純的“物”。但我們仍然能夠從這些著作中歸納出一些物化標準,盡管它們之中有的已經不甚明晰。
在現今的學術界,以蘇秉琦為代表的觀點在辨認文明的起源時并不拘泥于具體形式,盡管可能會著重于大型祭祀遺址,制作精良,帶有禮器功能的玉器、陶器,不同規格的墓葬等,但背后體現的核心是文化的交流、碰撞與融合,傾向于以社會形態要素劃分文明。這也是學界較為主流的觀點。
而嚴文明在關于文明起源的過程與構架方面與蘇秉琦有別,這體現在他《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一文中。嚴文明在全面考察了B.C.3000年-B.C.3500年中國邁向文明的時期。提出多元一體的主張。雖然嚴文明在文中關注的物化表現與蘇秉琦較為類似。但是其關注的重點是人群社會分化的物質表現,他在禮器大型建筑以外還提出了中心聚落、城鄉分化、隨葬武器這些新的分化表現。將城鄉分化單獨拿出來作為物化標準的觀點也存在。持此觀點的學者更加看重其所體現的腦體分工這一社會現象對文明的意義。
就某一具體物象作為文明物化標準的看法雖然日漸式微,但是仍有學者以它為基礎提出了多樣的觀點。一些學者關注制作精良,帶有禮器功能的玉器、陶器以及宮殿、宗廟、王陵。同前者不同的是,這是更加明確的的公共權力象征。表達了這部分學者對于王權、神權在文明起源進程中的關注。也有學者仍以城市、青銅器、文字、禮儀中心為主要的文明標準,當然不同的學者也對這些標準做出了一些變通。如特別強調某項標準而其他相對較弱,或是增加玉器、漆器等標志生產分化或是禮制的器物。這一類學者傾向于把文明起源歸于某一特定的源頭。
還有學者將火的使用與人工制火,或是工具的使用作為文明起源的標志。這把文明產生的時間大大推前。從更加廣義的文明觀點看,這是一種“泛文明史”的看法。即所謂“一切人類史均是文明史”。與之類似,也有人主張以工具、藝術、火的出現或使用作為物化標準。
亦有學者提出以農業起源(或是畜牧業)作為文明的起源。以此為標準則將注意力更多放在生產力的方面考慮文明與經濟生產的關系上。
另外,一些學者主張無物化標準。即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糾纏,質變的那個點不會明顯的表達出來。不關注特定的標準,這同蘇秉琦的觀點在結果上有所一致,但是在指導理論上多有不同。如主張單一文化的漸進式發展等。這一類學者更關注文明進程的社會標準。
總而言之,文明史的研究歸根到底還是要歸附于“人”的身上,物化標準充其量是連接理論模型與實際材料的橋梁,它不僅反映了對文明概念的理解問題的,也反映了一個如何透物見人的問題。縱觀物化標準的變遷,其逐漸多樣化、模糊化的面貌正是對文明史的研究不斷朝活生生的人類歷史靠近的表現。當然,僅就考古學來說,后一個問題帶給我們的對如何把握考古材料這一問題的理論層面的思考也許更重要一些。
作者簡介:陸天舒(1990—)男,漢,籍貫:浙江省桐鄉市,畢業院校: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學歷:本科(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在讀),職稱:無,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專業,研究方向:考古學(新石器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