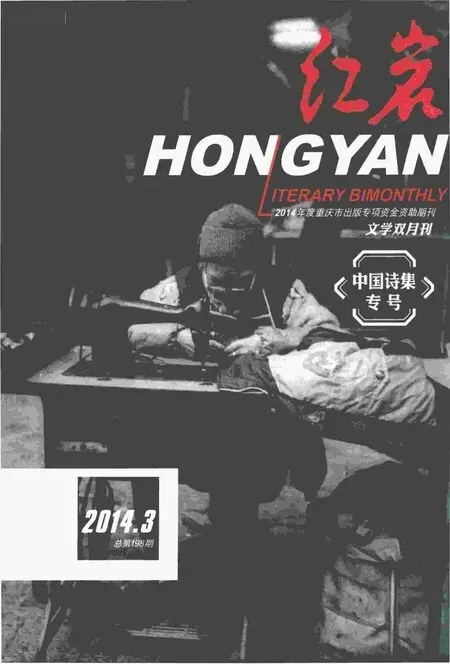下一步
2014-11-15 05:00:08宋煒
紅巖
2014年3期
關鍵詞:冬風
宋 煒
宋 煒
我曾經(jīng)對詩歌極其狂熱,快到要把自己蒸發(fā)掉的地步了,輕飄飄的,處處無從著落。那樣一種縹緲的樂趣顯然不能持久。于是我沉溺下來,低于生活,把自己局限在一只酒杯中。
只是這個過程頗不輕松。那段時間,我反復陷入同一個象征性夢境,直到它突然有一天自動通關了,才暫告一個段落。這個夢被我記在一篇叫《向下飛》的文字里。
在我離開不求滿盈的沐川,離開莫須有的下南道,進而從無所用心的成都到了大而無當?shù)谋本┖螅覊櫬淞恕斎唬瑝櫬涞眠€不夠。
所以,有段時間,我在北四環(huán)一幢丑陋之極的板樓里,反復做一個糾纏不休的夢,就是為了要讓墮落更徹底。像通常那樣,我安排自己在一道橫跨險峻深峽的獨木橋上行走,到了中間,無一例外地跌了下去。每次我都有點幸災樂禍地想,這次肯定完了,你狗日的死定了,卻又總是猛醒過來,一下子不知這樣究竟是好還是壞。很顯然,好的方面是我可以繼續(xù)茍活,但壞的方面則至少在那些天抵消了一大半茍活的殘余樂趣:我已持續(xù)近一個月,每晚被這個總是不能了斷的噩夢所輕薄。我表面上并不聲張,暗地里卻希求它給我來個痛快的,無論結果如何。不幾日,那個時刻到了。黑暗中,我再一次往下跌,再一次想,死了吧,死了吧,但毫無用處。我等了許久,根據(jù)經(jīng)驗,醒來的時刻早該到了,但那一次似乎將會被無限期推遲。于是我第一次放棄了這種但求一死的想法,轉而留心掠過耳邊的風聲,這才發(fā)現(xiàn)它并不急,不是最初那種鬼哭般的叫囂(跟隳突于北京惡心的板樓群中的冬風一樣),而是緩慢的、沙沙作響的輕風(更像北京三月天時運送著滿城揚絮的過敏性春風)。……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青年文學家(2025年1期)2025-02-20 00:00:00
當代作家(2023年12期)2023-03-21 05:53:55
邊疆文學(2020年5期)2020-11-12 02:29:46
小雪花·小學生快樂作文(2019年8期)2019-10-07 09:01:29
小學生必讀(中年級版)(2019年11期)2019-01-11 14:21:27
詩潮(2018年5期)2018-08-20 10:03:28
湖海·文學版(2017年4期)2018-01-09 07:27:00
文苑·經(jīng)典美文(2016年1期)2016-05-30 14:37:59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5年41期)2015-05-30 10:48:04
風采(2005年1期)2005-04-29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