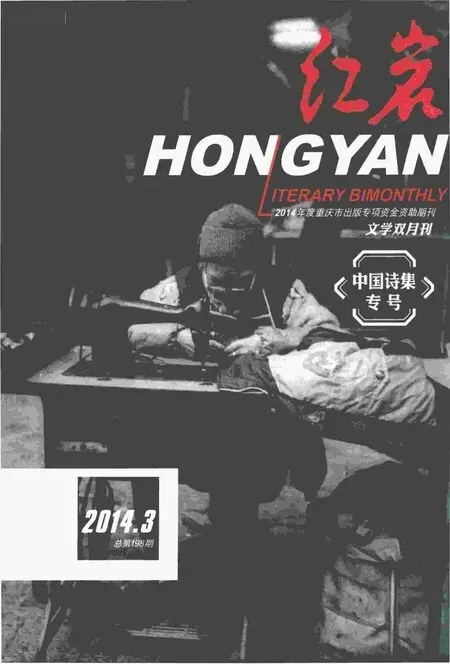唯美的刺點:媚人文來自駭人文
2014-11-15 05:00:08李商雨
紅巖
2014年3期
關鍵詞:文本
李商雨
一、兩種寫作:寫重要事物VS為寫而寫
在《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一文的開頭,蘇珊·桑塔格引瓦勒斯·斯蒂文斯的一句話:“最佳詩作將是修辭學的批評。”這句話為她論巴特一文定下了基調。羅蘭·巴特是一位符號學家,索緒爾的語言學因為巴特之手迎來了文學上的無上光榮;修辭學也因符號學的發展,在文學批評中,有了實質性的地盤。不僅符號學,巴特在文本理論方面,也產生了世界性影響。比如他從支持自己的高足茱莉亞·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到借助互文性和符號學,實現對結構主義的突破,構建了后結構主義文本理論;比如他的“文之悅”,建立了一種毀滅性的文本的色情學,將欲望與色情引入到寫作,引入到一種社會學的禁欲的文學語境,他讓寫作不再是真理、思想和觀念的販賣,而僅僅是快樂的肉欲享受與消費。巴特是一個形式主義者;然而,說到底,他是一個徹底的唯美主義者。
羅蘭·巴特讓寫作變成一種趣味。在他那里,“寫作”是一個不及物的動詞,他區分了作家和作者,在于前者不及物而后者及物。
“正像一位道德家(清教徒的或反清教徒的)會一本正經地區分性生殖和性快樂一樣,巴特也把作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寫重要事物的人(薩特所說的作家),另一類是不寫什么重要事物而只是去寫的人,后者才是真正的作家。巴特認為,動詞‘寫’(to write)的不及物含義,不僅是作家幸福的源泉,也是自由的模式。”蘇珊·桑塔格的這些話,其實道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分野:薩特一類的寫作和巴特一類的寫作的分野。……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甘肅教育(2020年8期)2020-06-11 06:10:02
藝術評論(2020年3期)2020-02-06 06:29:22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18年11期)2018-12-29 12:30:58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語文知識(2015年11期)2015-02-28 22:01:59
語文知識(2014年1期)2014-02-28 21: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