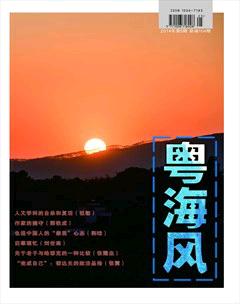彈《舌尖上的唐詩》
楊光治
以“注重文化品位,堅持精品路線”“以優秀與深刻為唯一標準”的文化批評雜志《粵海風》,是我最喜讀的刊物之一,今年第4期卻刊出了一篇令人大感意外的作品——《舌尖上的唐詩》(下簡稱“舌文”)。
“舌文”以“主持人”的一段文字開篇,說是由于“最近《舌尖上的中國2》又攜著讓人垂涎欲滴的美食重返了家家戶戶的熒屏”,由于“美食不僅是物質,也是美學,更是文化,讓人想起詩”,因此“邀請了幾位美食與詩歌同好,談談‘舌尖上的唐詩,組合成此文。所以,雖然“舌文”在文末鄭重表明,它是“江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用核心價值觀引領江西完善優秀中華傳統文化行動方案研究》、贛南師范學院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舌尖上的唐詩研究》階段性成果”,其實它是一篇以漫談的形式出現的作品。當然,文無定法,這種文體同樣可以展現學術研究成果,可是,筆者讀后卻如鯁骨在喉,不吐不快。
請讓我對文本作粗略的評析。
一、唐詩的“黍”。
談者提及《詩經》中的“黍禝重穋”之后,跟著談唐人王維的《積雨輞村莊作》中的“積雨空靈煙火起,蒸藜炊黍餉東菑”(“舌文”將“炊黍”誤寫為“炊火”),思路正常。然而,談者從王維這兩個句子想到的是“女子與丈夫一起在田頭野餐的情景,是多么有閑情逸致”,還表示希望今天也能“和心愛的人享受一番田園里蒸藜炊黍的美好時光”,認為這“不失為一種浪漫”,這就不大正常了!艱苦的農耕勞動汗水未干,即冒雨在野外就餐(連桌子凳子也未必有),此情此景何來“閑情逸致”可言?而且談者對王詩的理解也不大準確,“蒸藜炊黍餉東菑”并不一定是在田園里蒸、炊,而應當是在家里弄好后送到田頭去,此乃常識。事實上,雨中舉炊也“浪漫”不了。
更令人錯愕的是對孟浩然“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的闡述。孟詩的風格是“語淡而味不薄”(沈德潛語),此詩很有代表性。可是談者卻對“具雞黍”作如此想象:“老朋友把雞宰盡,切成小塊,再加上蒜、姜、辣椒等佐料,然后在大灶上添上很多木柴,把火燒得很旺,熱油略炒,加入鹽、酒、醋燜澆……”,這簡直是土豪歡宴,與全詩恬淡自然的情調大異其趣。
二、詩中自有魚滋味。
談者先耗費數百字從載叔倫、張志和的詩來談述魚多、魚美之后才進入“舌尖上”,枝蔓太繁了。其中一些觀點也有商榷之余地。如將“膾”理解為生魚片,未必恰當。“膾”,《說文》析為“細切肉也”,《辭源》也析之為“細切為膾”,都與“生魚片”無關。此外,劉禹錫的“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是表現捕魚的艱苦還是像談者所說的是表現漁家深夜享受魚宴的幸福?這問題還須認真思考。
三、相搭而生的美味詩意。
談者能緊扣“舌尖上”的題目,很好。可是他從杜甫的《贈張旭詩》“荷葉裹紅魚”之句,想到杜氏“即使身處亂世眼前也會自然而然地浮現‘魚戲蓮葉間這意趣盎然的一幕,讓人心曠神怡”一說,令人難以接受——將魚被荷葉裹著來蒸和魚在荷葉間嬉戲聯系起來“欣賞”,不有點冷酷嗎?
四、詩人的舌尖有甜也有苦。
談者的言論令人信服。他指出,孟浩然在故人莊所吃的,只是“尋常百姓家的粗茶淡飯”,“喝上口小酒”“吃點兒農家小炒”而已,這一理解,比上文寫到的“把雞宰盡……”的描繪切合詩意得多。他談論了李白對美酒的喜愛和楊貴妃吃荔枝的歡樂之后,轉到了舌尖上的苦,將“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視為“唐詩給我們后世留下的警句,也讓我們體會到舌尖上的艱辛”,這一來,“舌尖上的唐詩”就比較全面。可惜,“舌文”的《結語》對此無動于衷,只強調“甜”的一面。
筆者讀此文后還產生以下的疑惑:
學術研究忌模仿跟風。《舌尖上的中國》電視片中在民間風行,但其題目文理不通。可是現在連高校的學者也不考慮這一點,竟公然跟風模仿,從而定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課題,并視之為“創新訓練項目”,此舉不無諷刺意味嗎?按此思維類推,還可以“創”出一大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項目,如《舌尖上的宋詞》《舌尖上的元曲》《舌尖上的清詩》《舌尖上的〈紅樓夢〉》《舌尖上的蘇軾》《舌尖上的紀曉嵐》《舌尖上的和珅》……專門成立一個研究機構也大有可為。
“舌文”是“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用核心價值觀引領江西完善優秀中華傳統文化行動方案研究》”的成果之一,這已成事實,但是,這一課題是否真的“重大“?這個“關”是否需要組織幾位學者去“攻”?“核心價值觀”又怎樣“引領”他們去“研究”?我只是一名普通讀者而已,不懂得如今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及其有關的種種奧秘。本著對《粵海風》的喜愛而敲出此文,但可能全是謬論,請批評指正。
(作者單位: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