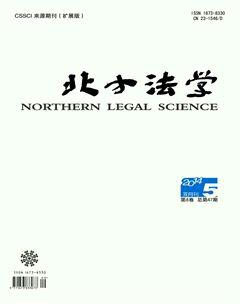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發展難題
張玉潔
摘要:從錯案追究終身制的歷史發展來看,其在防治司法不公上的作用非常有限。作為司法機關內部的一種責任追究機制,它也表現出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和明顯的制度缺陷。“錯案”界定不明、糾責范圍不確定以及職業風險終身性等問題的存在,導致法官采取各種方式來規避這種制度性缺陷,使得錯案追究終身制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一種逆向刺激結果。為了糾正我國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發展難題,司法機關應當以法律實用主義的理念重構該制度。
關鍵詞: 錯案追究逆向刺激制度重構
中圖分類號:DF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4)05-0153-08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的司法體制歷經三輪改革,①每一輪改革的方向均不相同,且缺乏長遠的目標規劃,致使我國的司法體制始終保持著“一步三回頭”的曲折式發展之路。近幾年,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聶樹斌案、匡增武案等“錯案”的持續曝光,又一次挑動了最高法院的改革決心。為了杜絕法官在案件審理中的徇私枉法、肆意裁量行為,我國司法機關又一次掀起了錯案責任追究的制度化改革浪潮。此次制度化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建立錯案追究終身制,②以期通過權責合一的方式來保障法官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但是,從錯案追究終身制的歷史沿革來看,該類制度并未在司法系統內形成高效的“錯案”防范機制,反而產生了諸多變異功能。
一、錯案追究終身制的歷史沿革及時代特征
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確立是一個歷時性的建構過程,它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錯案追究制、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錯案追究終身制。每一個階段都具有不同的特征。
(一)錯案追究制(1990年—1995年)
我國在制度建構上存在兩種路徑:一是中央主導、地方協同式的路徑;另一種是地方試點、中央推廣式的路徑。錯案追究制即是在后一種發展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最初由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人民法院創制,后經最高法院的肯定,吉林、浙江、山西等地各級法院也相繼建立了“錯案追究制”。總體說來,這一時期的錯案追究制度主要是一種裁判結果導向的責任追究機制,裁判結果的正確與否成為這一階段追究法官審判責任的主要標準。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頒布的《法官法》并未在法律層面上認定“錯案追究制”這一提法,而僅在第32條中規定了法官禁止從事的13項行為。雖然“徇私枉法”、“隱瞞證據或者偽造證據”、“濫用職權,侵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等法律款項均暗含“錯案追究”之意,但“錯案追究制”終因法律的不完備無法成為規范法官審判行為的長效機制。
(二)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1998年—2005年)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深入,司法機關開始審視正當程序在司法審判中的作用。因此,法官責任追究制度的重心開始從裁判結果導向轉向裁判結果與程序性審查并舉的責任追究導向上。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公布《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以下稱《追究辦法》)和《人民法院審判紀律處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處分辦法》),《追究辦法》將“錯案追究制”從單一的結果導向轉變為結果與程序并重的“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處分辦法》則將“違法受理案件”、“違反回避制度”、“違反證據制度”、“擅自干涉下級法院”等程序性違法(犯罪)事項作為法官責任追究的重點。由此可見,程序性責任的追究成為這一階段法官責任追究的重點。在《追究辦法》公布之后,上海、廣東、安徽、海南等省(市)司法機關相繼出臺“實施細則”,明晰了法官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的具體適用問題。2005年,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錯案追究制有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為由,率先取消了錯案追究制,代之以“法官不規范行為認定”制度。③暫且不論“法官不規范行為認定”制度的效果如何,僅從該法院對“錯案追究制”的否定而言,法官責任追究機制在審判實踐中必然存在亟需改良之處。
(三)錯案責任終身制(2008年至今)
現階段,司法機關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司法公信力不足、司法不公和司法不獨立。面對層出不窮的“聶樹斌案”和巨大的社會壓力,司法機關如何抑制司法腐敗、限制自由裁量權成為新一輪司法改革所需解決的重點問題。④在這種背景下,盡管錯案追究制飽受司法實務界和學術界的批評,但是一種“新形式”的錯案追究機制——錯案追究終身制逐漸開始興起。
云南省2008年出臺的《關于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實施細則(試行)》第17條明確規定:“違法審判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對有關責任人實行終身責任追究。”隨后,河南省在2012年出臺的《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試行)》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在審判、執行工作中,應嚴格公正司法,不得違反法律規定、法定程序辦理案件,對所辦案件質量終身負責。”經過對比可以發現,與云南省的實施細則相比,河南省在法官責任終身追究范圍上并不局限于“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違法審判案件,而是擴大至所有違法審判案件。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⑤將“錯案追究終身制”從地方推廣至全國,在國家層面得以確立。該意見要求:“建立健全合議庭、獨任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明確冤假錯案標準、糾錯啟動主體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
③參見黃海霞:《北京第一中級法院取消錯案追究制 認為有礙公平》,載搜狐新聞:http://news.sohu.com/20051121/n227555277.shtml,最后訪問時間: 2014年6月26日。
④我國對司法自由裁量權的限制應當是一種規則之治,法官“根據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據個人好惡做某事。自由裁量權不應當是專橫的、含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權力,而應當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規的權力”。[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頁。
⑤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1月出臺的《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27條規定:“建立健全審判人員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審判人員依法履行職責,不受追究。審判人員辦理案件違反審判工作紀律或者徇私枉法的,依照有關審判工作紀律和法律的規定追究責任。”《意見》只明確了“審判人員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并未明確規定錯案追究終身制。
值得注意的是,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發展過程始終伴隨著來自實務界和學術界的諸多批評,而且該制度本身的缺陷并未在歷史沿革中得到完善。由此,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確立仍面臨諸多問題。
二、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現實困境
(一)“錯案”界定標準不統一
從現階段的司法實踐來看,我國各級法院在錯案追究終身制的實施上存在諸多不統一之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錯案”界定標準的不統一。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行錯案追究制之初并未明確認可“錯案”這一稱謂,也未對責任追究的前提性條件作出其他形式的界定,從而使地方法院在制度適用中只能憑借各自的理解來界定“錯案”。河南省高級法院在2012年出臺的《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試行)》第3條中規定:“本辦法所稱的錯案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故意違反與審判執行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致使裁判、執行結果錯誤,或者因重大過失違反與審判執行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致使裁判、執行結果錯誤,造成嚴重后果的案件。”《內蒙古自治區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錯案責任追究條例》則將“錯案”界定為:“本省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及其辦案人員辦理的案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或者違反法定程序而造成裁判、裁決、決定、處理錯誤的案件。”雖然兩地法院均將“事實認定錯誤”、⑥“法律適用錯誤”、“審判程序錯誤”作為“錯案”的典型特征,但內蒙古各級法院所認定的“錯案”概念是以裁判結果為導向的,⑦而河南省高級法院對“錯案”的認定是以損害后果為導向的,即對于符合三類錯案特征之一的案件,只有在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才會被認定為錯案。換句話說,即使法官審理案件中存在程序性錯誤,只要未造成嚴重后果就不會因“錯案”而受追究。由此可見,最高法院在錯案追究的前提性條件——“錯案”概念未界定的情況下推行錯案追究終身制,必將導致地方法院在錯案認定和責任追究范圍上的不統一。
(二)責任除卻事由的主觀模糊性
為了防止各級法院肆意擴大錯案的范圍,錯案終身追究制在制度設計上除了明確法官責任追究范圍外,還規定了一種反向性的責任除卻事由,即在某些情況下,法官不會因錯案被追究責任。《處分辦法》第4條明確了三類不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案件:一是法律、法規尚未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的、因認識偏差產生的“錯案”;二是在法律適用中因理解和認識偏差造成的“錯案”;三是由于對案件事實與證據認定上的認識偏差引起的“錯案”。⑧在這三類免責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均將“認識偏差”作為免責的理由。但是,認識偏差既可能來自于法官自身的學識、經驗差異,也可能來自于其對事實和法律的故意曲解。由于“認識偏差”的主觀性因素太強,錯案是否因“認識偏差”而發生難以獲得客觀的證據支持。這樣,不同法官針對相似案件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決,何種判決是正確判決亦難以獲得明確的界定標準。因此,不同法官對相似案件作出的截然相反的兩種判決必然有一個為“誤判”。在此意義上說,由于主觀認識上的偏差,即便《處分辦法》及地方法院均將“認識偏差”作為法官的責任除卻事由,法官所作的判決仍面臨著被認定為“錯案”的危險。但是,除外事項并不能消除法官被審查的可能,法官在每一個案件中都必須承擔責任追究的潛在風險。
⑥弗蘭克認為,無論法律多么確定,判決仍然取決于事實認定。假如事實認定存在疑問的話,那么,案件的判決至少也存在同等疑問。參見[美]杰羅姆·弗蘭克:《初審法院——美國司法中的神話與現實》,趙承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頁。
⑦富勒從法經濟學的視角對錯案與損害后果做了比較,他認為:“為了確保一個判決正確無誤,我們必須消耗時間這種稀缺資源,而且,一個姍姍來遲的正確判決對被告造成的損害可能大于一項很快作出的錯誤判決所造成的損害,這個問題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面目。”[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鄭戈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07頁。
⑧除此之外,河南省、廣東省、彭州市等地方法院也將“法律與政策變化”、“新證據”和“當事人過錯”作為錯案責任的除卻事由。
⑨Ronald Dworkin,On Gape in the Law,in Paul Amselek and Neil MacCormick(eds.), Controversies about Laws Ont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p. 84.
⑩王晨光:《法律運行中的不確定性與“錯案追究制”的誤區》,載《法學》1997年第3期。
(三)責任產生的必然性與法官職業風險的沖突
錯案追究終身制的構建旨在為法官的審判權行使設定某種責任,以期能夠促進司法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但是,錯案追究終身制以錯案作為法官責任追究的前提,而且錯案又是相對于正確判決而言的,那么,這似乎意味著:在錯案追究終身制下,“一個法律問題實際上總有一個唯一正確答案”。⑨如果法官作出的判決不同于這一“唯一正確判決”,法官就要被追究責任。但是,有學者提出,“所謂的‘唯一正確的答案也不過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根據這一不確定性的概念確定的‘錯案的概念也就必然是不確定的。即便我們承認有某種不太確定的正確答案存在,在大多數案件中,與這種‘正確答案的距離達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錯案呢?……這種與‘正確答案的距離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參數。”⑩司法實踐已經證明,由于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確定性,B11案件之間總是或多或少地有所差異,“同案同判”在實踐層面必將遭遇“唯一正確解答”難以明確的難題。這樣,一種制度性的結果便產生了,即司法裁判作為法官的職業行為,其始終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錯案風險,“即使司法機關內每個工作人員都盡職盡力,不時出現一些司法決定上的偏差、錯誤仍然是難免的”。B12
責任追究的終身制則在追究時效上進一步增大了法官的職業風險。錯案責任終身制對于法官而言,主要產生兩種職業風險:一是確立責任承擔主體是法官個人,審判機關不再作為責任人,增加了辦案法官的責任感和危機意識;二是辦理案件終身負責,法官不會因調離、辭職、退休等原因而免責。B13這樣,錯案追究終身制就過分加重了法官的裁判負擔,一方面它無法消除錯案與“唯一正確判決”的二階邏輯悖論,另一方面又強化了責任追究的長期性,使得法官作為一個職業群體無時無刻不承擔著責任風險。丹寧勛爵就指出,“所有法官都應該能夠完全獨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需擔驚受怕。決不能弄得法官一邊用顫抖的手指翻動法書,一邊自問,假如我這樣做,我要負賠償損害的責任嗎?……只要真誠地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在自己的司法權限之內,他就不應承擔法律責任。”B14假設錯案追究終身制在制度建構上不作相應完善,最終只能導致法官在審判工作中畏首畏尾,影響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獨立性。
三、錯案追究終身制的逆向刺激結果
(一)以調解代替判決
以調解代替判決的現象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河北、廣西、河南等地甚至出現“零判決”、“零上訴”等現象。B15有資料統計顯示,2009年廣西各級法院共審結一審民事案件128284起,調解結案數為82673件,占結案總數的64.45%;一審行政案件調解結案數為718件,占結案總數的26.94%;執行案件結案數為43704件,調解結案數為21354件,占結案總數的48.86%。B16雖然最高人民法院認定“零判決”行為屬于地方法院對調解結案的誤讀,但以調解代替判決的現象并未因此得到改觀,“錯案追究終身制”甚至可能成為另一個“以調代判”制度。
B11對于案件事實的不確定性,波斯納的觀點是:“由于如此之多的法律原則看來都將思想狀況作為責任的一個重要因素,看來也許事實不確定性問題將會大大加劇。”[美]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頁。
B12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頁。此外,法國學者勒內·弗洛里奧也認為:“公正的審判是不容易的,最審慎的法官也可能把案子搞錯。”[法]勒內·弗洛里奧:《錯案》,越淑美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4頁。
B13云南省高級法院出臺的《關于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實施細則(試行)》第17條規定:“違法審判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對有關責任人實行終身責任追究。”河南省高級法院出臺的《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試行)》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在審判、執行工作中,應嚴格公正司法,不得違反法律規定、法定程序辦理案件,對所辦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B14[英]丹寧勛爵:《法律的正當程序》,李克強等譯,群眾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頁。
B15在司法系統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的快速發展也成為“以調代判”現象普遍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B16資料來源于中國法院網: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1001/17/391377.s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4年6月26日。
B17范愉:《從訴訟調解到“消失中的審判”》,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5期。
在錯案追究終身制下,法官的責任追究范圍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判決書;二是訴訟程序的合法性。在第一個來源下,法官所作出的判決結果不可避免地全部納入責任追究的審查范圍中去。也就是說,法官只要作出判決就需要承擔被追究責任的風險。每增加一次判決,受到責任追究的風險就增加一分。在這種情況下,法官為規避責任,必然尋求一種可以規避風險的糾紛解決方式,而調解恰能滿足這種需求。作為法院系統普遍認可的一種結案方式,調解無需制作判決書,也未納入法官責任追究的監察范圍之內。因此,以調代判既達到了“息訟止爭”的目的,又規避了錯案追究終身制的責任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錯案追究終身制只能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以調代判”制度。
現階段的司法改革旨在強化司法的獨立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強司法權威。而錯案追究終身制所引發的結案形式轉型——以調解代替判決——卻與司法改革的意旨背向而馳。它可能引發的危險是:“審判產出的公共產品不斷減少,司法開始脫離法治預期的軌道,社會的糾紛解決也會脫離法律的規制。盡管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些危險必然成為現實。但是,在肯定和解以及司法的功能轉變帶來的積極和合理因素的同時,確實有必要對其潛在問題加以充分關注和持續的觀察。”B17
(二)責任追究與“監督者悖論”
在錯案追究終身制下,法官是否承擔錯案責任是根據其所作判決的正確與否來判定的。河南省《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第13條規定:“錯案責任按下列情形區分責任:1.獨任審判造成錯案的,由承辦人承擔全部責任;2.案件承辦人未如實匯報案情,故意隱瞞主要證據、重要情節,或者提供虛假材料,導致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作出錯誤評議結論、討論決定的;或者遺漏主要證據、重要情節,導致錯案、造成嚴重后果的,由案件承辦人承擔全部責任;3.經合議庭作出裁決造成錯案的,案件承辦人、審判長持錯誤意見的,承擔主要責任,其他持錯誤意見的成員承擔次要責任,合議庭成員中持正確意見的不承擔責任,審判委員會改變合議庭意見的,合議庭成員中持正確意見的不承擔責任;4.主管領導、部門負責人故意違反法律規定或者嚴重不負責任,利用職權指示獨任審判員或合議庭改變原來正確意見導致錯案的,主管領導、部門負責人承擔主要責任,案件承辦人承擔次要責任。”此種責任承擔方式是司法機關消除司法腐敗與肆意裁量行為的一種折中,折中點就是以增加法官個人的責任來減少司法的制度性缺陷。
但問題是,“法官對法律問題應當有最終的發言權,不應當在法官之外、之上有一個評價法官行為合法性的力量”。B18況且,對法官個人責任的追究并不足以消除司法制度自身的缺陷,其理由主要來自以下兩方面:一方面,法官責任的承擔是以受到查處為前提的,而引起法官責任的違法行為往往具有隱蔽性,如受賄、故意規避法律、法定幅度內的有意輕判等。錯案追究終身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通過增加法官違法裁判的風險來抑制這些行為,但卻很難消除司法制度自身的漏洞。另一方面,錯案追究終身制無法脫離“監督者悖論”。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監察機構是法院的內設機構,這種制度設計不僅導致法院內部糾錯動力不足,還會造成監督機制的失效。
B18周永坤:《錯案追究制與法治國家建設——一個法社會學的思考》,載《法學》1997年第9期。
B19[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54頁。
B20有學者針對“何種情況下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這一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受訪法官一致回答:“當我需要有人替我挑擔子的時候。”吳英姿:《法官角色與司法行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頁。
《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第5條規定:“全省各級法院設立錯案責任追究工作領導小組,由黨組書記、院長任組長,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和分管審判管理工作的院領導、紀檢組長和政治部主任任副組長。紀檢監察部門、審判管理辦公室具體負責錯案責任追究工作的日常事務。”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出臺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及專門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引咎辭職規定(試行)》規定,法院院長、副院長對本院發生的嚴重枉法裁判案件,致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造成惡劣影響的,應當主動提出辭職。可見,錯案追究終身制的監察機構與所監察的對象部分重合,法院院長、副院長對本院法官違法審判行為的審查有可能導致自身同樣需要承擔責任。由此引發了一個問題:監督者如何自我監督。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移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B19但是,當監督者開始成為自身權力的監督者時,權力的行使就不再有邊界。因此,司法改革者試圖以“內部糾錯”的錯案追究終身制來消除錯案,結果只能陷入“監督者悖論”的怪圈。
(三)責任轉嫁
在錯案追究終身制下,法官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必然采取責任轉嫁的方式來規避風險。責任轉嫁是指法官通過“請示”的方式將案件判決結果交由審判委員會或上級法院裁定的一種責任分擔與轉移方式。根據《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的規定,在合議庭將案件提請審判委員會決定的情況下,審判委員會改變合議庭意見的,合議庭成員中持正確意見的不承擔責任。由此可以推定,當審判委員會同意合議庭意見時,審判委員會與合議庭應當就該案件的判決結果共同承擔責任。無論出現何種情況,法官對判決結果的責任承擔風險都將分擔或轉移至審判委員會。B20同理,法官向上級法院的“請示”也會產生責任轉嫁的結果。因此,法官責任的個人承擔和終身承擔重又回歸到“無人”承擔的局面上。
此外,責任轉嫁還將導致兩審終審制的制度性危機。在兩審終審制下,案件當事人對一審判決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內向初審法院的上一級法院上訴,上級法院就法律適用及審判程序問題進行審查,
并根據審查結果分別作出改判、維持原判以及發回重審的決定。但是,一審法官通過“請示”使得一審判決與上級法院之間產生了直接的利害關系。上級法院對一審判決的否定意味著自身需要承擔“錯案”責任。因此,上級法院為了規避責任,只能作出“維持原判”的決定,案件當事人在二審階段就很難獲得公正的判決,兩審終審制由此遭遇制度性危機。
四、錯案追究終身制的實用主義重構
完善的制度設計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制度,即那些不僅由規范確立,而且其功能也是創設和適用規范的制度”,B21它應當滿足三個首要標準:一是制度設計本身在于增進公民福利;B22二是這套制度對適用者來說具有吸引力,其能夠被良好接納;三是該制度能夠與其他制度較好的銜接。錯案追究終身制的建立就違背了這三個標準。司法機關將錯案追究終身制設定為防止“錯案”的制度性措施,從根本上來說就將法官置于一種“有錯”基礎情境之下。它只能增加法官裁判負擔,不會產生福利增量;只能引發法官的厭惡情緒,促使法官竭盡所能地規避責任、轉嫁責任;只能造成錯案追究終身制與《法官法》、《處分辦法》、《刑法》等法官懲處法律和制度的銜接錯位,造成司法系統的混亂。由此可見,現行的錯案追究終身制是從權力限制的角度來解決司法錯案問題的。這是一種法律實證主義的制度建構方式。“法律實證主義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是,這可以使法院審慎地行使權力,表明自我約束的態度,也就是說完全在其權限范圍內行使司法權力。”B23
然而法律實用主義認為,這種做法是不符合邏輯的。理由在于,錯案限制與責任追究本來就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法律實用主義從現實需求出發,強調法律制度的工具性和實踐性,主張法律制度“是引導人們的行為取得良好效果的手段,衡量其好壞的標準是看它們是否能夠有效地增進其適用對象的福利……法律實踐決定了法律制度、法學理論和法律觀念”。B24因此,在法律實用主義者看來,法官錯案追究制實際上應當被設計為一種能夠有效推動司法公正的權力運行機制,并且機制運行的結果遠比運行機制本身更重要。可以說,法律實用主義是一種結果主義導向的法律觀。那么,在實用主義法律理念下,我國的錯案追究制應當做何改進呢?慮及實用主義對法律實踐和立法連貫性的重視,B25筆者認為,錯案追究制的實用主義重構應當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B21[英]拉茲:《實踐理性與規范》,朱學平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頁。
B22哈耶克認為:“由于正當行為規則所能夠影響的只是人們努力獲得成功的機遇,所以修正或改進這些規則的目的也就應當是盡可能地增進或改進不確定的任何人所具有的這種機遇。”[英]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三卷),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221頁。
B23苗金春:《語境與工具:解讀實用主義法學的進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5頁。
B24秦策、張鐳:《司法方法與法學流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頁。
B25[美]波斯納:《法律、實用主義與民主》,凌斌、李國慶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頁。
B26[美]薩默斯:《美國實用工具主義法學》,柯華慶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代譯序,第9頁。
B27前引⑩。
第一,確立可操作性的責任追究的標準、范圍。現行錯案追究終身制的主要問題是法律規制層面的操作能力較差。這是與法律實用主義的制度建構理念相違背的。法律實用主義認為,“不管是現有的還是未來的法律或者立法,不僅僅要考慮該法是不是社會欲求的,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其能否操作實現”。B26因此,要強化錯案追究終身制的可操作性,首先應當對法官的責任來源前提——“錯案”加以定性。現行錯案追究終身制中的“錯案”稱謂,是文革時期“冤假錯案”一詞的沿用,帶有極強的政治含義。而且“錯案”一詞暗含“一個案件只能有一個唯一正確的判決,否則就是錯誤的判決”之意,B27嚴重違背我國的司法實踐經驗。因此,“錯案”名稱應當獲得更合理的稱謂。筆者認為,提升制度稱謂的合理性、合法性也是法治化要求的體現。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所言的“法官不規范行為”雖有些許不當之處,但相比于“錯案”,無論是在語詞歧義的消除,還是在制度的形式合法性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在尚未產生更為準確的語詞之前,錯案責任終身追究制可以用“法官不規范行為責任追究制”代替。
而責任認定標準與責任范圍是兩個密切相關的概念,認定標準的不確定或模糊性直接影響責任范圍的明確性。因此,錯案追究終身制可操作性的提升在于責任認定標準與責任范圍的明確、統一。《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將責任認定標準界定為“審判人員在審判、執行工作中,故意違反與審判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或者因過失違反與審判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造成嚴重后果”。筆者認為,這一標準既包含故意違法行為的界定,也包括過失違法行為的界定,符合我國現階段對法官責任追究的現實需求。因此,該標準應當成為我國法官責任追究制度的統一性標準。但是,該標準過于抽象,
不利于司法實踐中的實際運用,司法機關還應當明確更加具體的責任認定標準。
從現行法律體系來看,能為法官責任認定提供有效標準支撐的是證據制度、指導性案例以及法官對某類案件的主觀傾向。法官對法律事實的認定主要依賴于證據的證明力。B28相關證據鏈的證明力及法律事實推理的合理性可以成為法官明晰法律事實的有效工具。而指導性案例可以作為法官在類似案件判決上的參考,法官在作出判決時如果明顯違背證據指向和相關指導性案例的判決結果,該案件就有可能存在“誤判”。另外,法官的職業化使得其可以長期從事單一領域的審判工作。比如,民事審判庭的法官長期從事民事案件的審理工作,刑事審判庭的法官長期從事刑事案件的審理工作等。在這種長期的案件審理工作中,法官對某一類案件的主觀傾向會在判決結果中顯現出來。B29當該法官對類似案件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決結果時,法官責任監督機構就有責任展開調查。由此可見,抽象性的責任認定標準作為統一性的規范標準,宏觀上規范地方各級法院的責任追究標準和范圍,而證據制度、指導性案例以及法官對某類案件的主觀傾向可以作為具體認定標準,增強法官違法審判責任認定的可操作性。
B28蘇力認為:“在絕大多數案件中,司法實際上依據的是在法定范圍內認可的并為一些證據所支持的事實,即法律事實而決定的……雖然法律事實可能與客觀事實近似,但并不總是相等,甚至總是不能重合。”前引B11。
B29卡多佐提出,“在意識的深層還有其他一些力量,喜愛和厭惡、偏好和偏見、本能、情感、習慣和信念。”這些力量有助于形成法官判決的形式和內容。參見[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05頁。
B30葛洪義:《司法權的“中國”問題》,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B31前引B26,第78頁。
B32劉靜坤、張倩:《美國最新錯案報告(1989年—2012年)》,載東方法眼網:http://www.dffyw.com/sifashijian/jj/201310/33954.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3年10月20日。
B33謝茨施耐德認為,這是一種“沖突的私域化”與“沖突的社會化”之間的力量博弈。參見[美]謝茨施耐德:《半主權的人民》,任軍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頁。
第二,建構目標指向的內部與外部混合型監督機制。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錯案追究制到現今的錯案追究終身制,一直以內部監督的方式作為法官責任追究的啟動機制,外部力量始終難以成為監督司法系統的啟動方式。正如某學者所言:“司法越公開,被批評的可能性越大;人們越是批評,法院為了迎合大眾和逢迎上司,就越容易犯錯誤;法院的錯誤暴露越多,越受到批評。”B30所以,司法機關為了遮蓋自身的弊病,長期采用內部監督的方式來限制他方追責。但內部監督機制并不能消除“錯案”,也不利于樹立司法機關的公信力,因此,法律實用主義勢必對現行監督機制提出反詰:“現在能做什么來改變未來?與實質目標(來源于大眾的需求和利益)相關的是什么?哪些法律規則可以促成此目標?”B31
從當前廣為人們關注的幾起錯案來看,錯案責任追究程序的啟動皆源于外部力量的介入。如佘祥林案和趙作海案因“被害人重生”而啟動責任追擊機制、聶樹斌案因“真兇自首”而被人談及、匡增武案因人大對司法的監督而再審。美國的一項調查也顯示,“2009年至2011年間,(美國)共有154個改判無罪案件。無辜者項目推動糾正了其中的75個案件,包含43個基于DNA證據改判無罪的案件。檢察官和警察積極參與了其中42個案件的糾正工作,包括21個基于DNA證據改判無罪的案件”。B32由此可見,外部監督力量在糾正錯案上動力充足,也最容易為法院監督機構提供錯案線索,能夠有效促成制度目標的實現。因此,我國錯案追究終身制的制度構建應當以增進司法公正為目標,建立內部與外部混合型的監督機制,其中主要是外部監督機制的構建與融入。
所謂外部監督機制,主要是指依靠司法系統以外的力量來實現對法官審判權的監督的一種機制。司法系統以外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案件的利害關系人、社會團體、新聞媒體、人大等主體。監督的范圍主要是審判程序的正當性和裁判結果的合法性。監督手段以社會化監督為主、私人化監督為輔。B33監督手段的社會化是外部糾錯機制的核心,它是“權力—權利”沖突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早期的私人化監督手段主要是案件利害關系人通過上訴、申請再審、信訪等手段尋求公權力機關提供權利保護的一種“私域性”監督方式,兼有公民維權、問責、監督等涵義。相較于法官審判權的強大而言,案件利害關系人很難在“權力—權利”博弈中占據優勢。因此,這種監督方式對法官職權的監督作用非常有限。但在以網絡媒體為代表的信息傳播方式逐漸發達的情況下,案件利害關系人開始將案件的影響力擴大至社會層面,吸引更多的“旁觀者”參與進來,以此對法官的審判行為形成輿論壓力。“而司法,
作為國家公權力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有著相對封閉的特點,公民借助媒體力量,嘗試在司法過程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可能在與公權力的對抗中獲得更為平等的地位,從而有助于司法公平的實現”。B34所以,錯案責任終身制在追責機制的啟動方式上應當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外部的力量,將外部糾錯機制作為內部糾錯機制的啟動方式之一,同時輔之以追責結果反饋機制,使公眾看得見正義被實現。
第三,降低“行政化”傾向,并加強責任追究的程序性保障。法律實用主義在制度建構理念上遵循結果主義的進路。因此,實用主義法學家薩默斯認為,“造法者直接關注效果即可,根本無需追問其原因”。B35比如制定錯案追究的方案。如果立法者意在保證司法系統的公正性,那么,他并不需要以責任追究方式給法官戴上“枷鎖”,而只需要切斷造成司法不公正的來源即可。我國司法錯案產生的部分原因源于行政部門對司法系統的干預,其中既包括行政部門在財政、人事管理上對司法系統的干預,又包括司法系統本身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例如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具有同樣的紀律處分方式: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和開除)。可見,錯案追究終身制雖然是一種法院內部的追責機制,但帶有強烈的行政化傾向。“人們很容易并且也習慣于把法院僅僅看做是另一個政府機構,只不過是一個解決糾紛的機構,把上下級法院關系看做是另一種行政監督關系,把院長與法官的關系看成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B36這樣,法官的審判工作極易受到來自司法監督部門的行政化干擾,從而使司法的獨立性難以得到保障。所以,錯案追究終身制應當擺脫責任追究方式的行政化傾向,減少司法監督部門及上級法院的干涉。
B34趙利:《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的博弈》,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B35前引B26,第84—85頁。
B36蘇力:《中國司法改革邏輯的研究——評最高法院的〈引咎辭職規定〉》,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1期。
B37丁文生:《“錯案追究制”司法效應考——兼論我國的法官懲戒制度》,載《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為了保證司法的獨立性,錯案追究終身制的責任追究程序同樣需要完善。“在國外,法官的懲戒大致有兩種程序:一為彈勃程序,旨在對實施嚴重犯罪行為、不法行為或不當行為的法官進行罷免,這種程序啟動非常困難;二為懲戒程序,旨在對有違法失職行為的法官進行紀律處分,由獨立的委員會或法庭負責。美國一般是由法官行為委員會負責,德國是由聯邦、州法官職務法庭專門負責,而法國則是由高等司法委員會負責的”。B37反觀我國法官責任追究程序的啟動,除法官行為構成犯罪外,法官責任的追究一般不會觸及訴訟程序,而只能啟動違紀調查程序。根據《人民法院監察部門查處違紀案件的暫行辦法》的規定,我國法官違紀調查程序的啟動較為容易,各級法院監督部門對本級法官、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法官都可以啟動違紀調查程序,程序啟動“門檻”較低。因此,我國錯案追究終身制應當提高責任追究程序的啟動“門檻”,將啟動主體置于中級以上法院,明確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法官的審判責任追究職權;取消審判委員會對本級法院法官的責任追究職權,代之以提供錯案線索、配合上級法院調查取證的方式履行法官責任追究職能。
The Development Predicaments of the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for Lifetime: System Deficiencies, Adverse Stimulation and Pragmatism Reconstruction
ZHANG Yu-jie
Abstract:The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has played a very limited role in prevention of injustic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reover, as a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within judiciary departments, it has a strong administrative feature and several obvious system deficiencies. Such issues as the vagueness in defining the “misjudged-case”, the indefinite scope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 lifetime occupational risk have led the judge to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evade these system deficiencies. As a result, the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has produced an effect of adverse stimulation in practic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se development predicaments, the judiciary departments should reconstruct the system abiding by concept of the legal pragmatism.
Key words: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adverse stimulationsystem re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