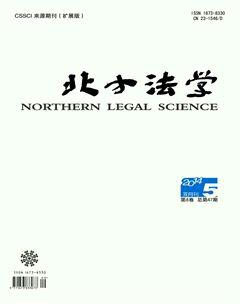作為法官裁量問題的“相當損害額”
潮見佳男+姜榮吉
摘要:1996年日本《民事訴訟法》新設第248條規定,在認定已發生損害的場合,因損害的性質對其金額的舉證極其困難時,法院可以基于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以及證據調查的結果,認定相當損害額。實體法層面上的損害觀念是該項規定的前提,而作為該損害觀念的損害事實說否定了差額說,并認為應將從金錢評估中分離出的事實作為損失。在介紹有關該條的學說以及適用該條的裁判例的基礎上,對該條在日本所起到的作用進行說明,并起到他山之石之效是十分必要的。
關鍵詞:損害差額說損害事實說損害金額評估證明度
中圖分類號:DF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4)05-0005-09
一、 對損害以及損害額的舉證責任
(一)傳統立場——被當作事實認定層面問題的損害額
在日本,一直以來就有將確定損害賠償額作為事實認定層面問題進行處理的傾向。通說認為,在損害賠償訴訟中,損害額也是主張與舉證的對象,而對此的主張與舉證責任在受害者一方。①此外,采取個別累計方式(個別損害項目累加方式)的場合,主張與舉證的主要事實應為每個損害項目(以及其金額),而非差額。②
相對于此,精神損害及撫慰金數額則沒有成為主張與舉證責任的對象,但是已經確立了如下的思路:法院進行該算定時不必逐一出示認定該金額的根據,即使受害方沒有對精神撫慰金的金額進行證明,通過充分考慮相關的各種情況可以作出賠償精神撫慰金的裁定。此外,法院在裁定賠償精神損失時,應予以考慮的情況也無限制,除受害方的地位與職業當然需要考慮外,加害方的社會地位、財產狀況也可在考慮范圍之內。③
(二)裁量說——作為法官裁量事項的損害金額評估
相對于上述傳統立場,20世紀70年代平井宜雄在指出損害額的認定并非事實認定層面(例如因果關系)上的問題而應是評估層面上的問題后,進一步主張損害的金額評估并非實體法問題,而是歸屬于法官裁量范圍內的問題。④這一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在損害賠償請求中,損害賠償額不作為實體法上的問題,而將其劃歸于法官專屬權限中的金額評估問題的見解,給損害賠償請求權在訴訟上的構造帶來了根本性的變更。即因為對損害事實進行的金額評估是由法官在審判中的裁量性、創造性的司法作用所決定的,所以從原告(受害者)的立場而言,請求內容中的賠償額僅能算作具有估算的性質。因此,即使法官判決的賠償額超過了原告請求的賠償額,也不應當認為是對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6條(文中《民事訴訟法》如無特別注明皆指日本《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當事人沒有請求的事項”進行的判決,原告也就沒有在損害賠償訴訟的訴狀中提示金額的必要了。這是現在的判例與通說。而且,判例與通說否定了請求損害賠償的原告對損害事實與損害數額負有舉證責任的立場,認為法官進行的金額評估并非是獲得對事實存在與否的心證問題,而是從數種金額算定的可能性中選擇其中一個的問題,因此,僅從這方面而言原本就沒有成立舉證責任這一觀念的余地。換句話說,這種承認金額評估具有創造性與裁量性的性質,并從對損害額的處理權主義以及舉證責任中解放出來的提案,是賦予損害賠償請求訴訟以非訴性。因此,根據這一見解,在判例與通說中有爭議的損害賠償額算定的基準時間問題,失去了實體法的性質,而轉換為法官金額的評估問題。⑤以上的觀點中,在算定損害賠償額的判斷過程中,區別事實認定問題與法官評估問題進行理解的部分,在學術界獲得了廣泛的共識,但是將金額算定歸屬于法官的裁量權限的部分,卻在學術界遭到了強烈的反對。⑥但在財產損害賠償請求訴訟中,這一觀點沒有使法官承擔巨大的負擔嗎?不缺乏法的安定性嗎?此外,對于這一主張還有如下批評:將金額評估歸屬于法官的裁量權限,即使原告認同法院判斷的金額,但攻防對象無法確定,對于被告而言極其不公平。⑦
可以說平井氏的主張是給如下所述判例實踐上總結的金額評估進行歸納——其實質,從其反方向來說是要為確立金額評估實體規范(金額評估規范)——進行適當的定位。判例實踐上總結的金額評估制度,是將通說嘗試通過某種技巧以期實現在實體法上的正當化的問題,比如算定幼兒、家庭婦女、無職業者或者外國人的逸失利益,精神撫慰金以及從公平角度出發規定賠償額減額的框架等問題,作為事實認定層面的問題處理以減輕舉證難度。
此外,平井氏認為,法官在進行裁量性、創造性的判斷時,以對于保護范圍內的損害在口頭辯論結束時,根據“全額評估原則”[盡可能回復與以前受害方(債權人)相同的經濟地位的原則。依據平井氏的主張,這一原則為實體法上的原則]進行評估為宜,因此,并非賦予了法官完全的自由裁量權。這與強調根植于損害賠償制度的原狀恢復理念的立場有近似性。
③ 大判大正9年5月20日民錄26輯,第710頁;大判昭和8年7月7日民集12卷,第1805頁。
④[日]平井宜雄:《損害賠償法理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第382、479頁。
⑤前引④,第382、479頁以下。
⑥前引②前田達明書,第351頁以下;[日]幾代通、德本申一:《不法行為法》,有斐閣1993年版,第134頁。
⑦[日]梅本吉彥:《爭端處理中損害概念與賠償范圍——對損害賠償請求與賠償請求額的確定》,載[日]加藤、木宮編:《汽車事故損害賠償與保險》,有斐閣1991年版,第7頁。
二、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中的“相當損害額”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規定:“在認定已發生損害的場合,因損害的性質對其金額的舉證極其困難時,法院可以基于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以及證據調查的結果,認定相當損害額。”這是1996年(平
成8年)新民事訴訟法增設的規定。⑧實體法層面上的損害觀念是《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前提,而作為該損害觀念的損害事實說否定了差額說(金額差額說),并認為應將從金錢評估中分離出的事實作為損失。⑨
有關損害額認定的規定,在1890年(明治23年)公布的舊民法證據編第8條中就已存在。B10其后,為了修改1891年實施的民事訴訟法,在日本司法省內設置的民事訴訟法調查委員會雖然在其制定的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244條B11也承續了這種規定,但是從此后承擔民事訴訟法修改任務的法典調查會完成的民事訴訟法草案起再未出現過這種規定。直至1996年(平成8年)才終于在新民事訴訟法中對有關損害額認定進行了規定。B12 不過圍繞著此規定到底是什么性質,存在證明度減輕說以及與之對立的裁量評價說等不同觀點。B13
(一)證明度減輕說
《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對此前一直困擾著裁判實務的損害金額評估,從正面肯定了可以由法院的裁量認定適當的損害額。此條的設定是為了解決雖然成功地對損害事實的發生進行了證明,但是對損害額算定的證明卻困難的問題。即此條是以在有關損害額算定的事實認定層面,減輕受害者的舉證負擔為目的。在已經證明了損害事實存在的前提下,存在有關損害額算定的實體法規范的場合,減輕認定事實以符合該規范的證明度。B14這也是法案起草者的見解。B15
⑧[日]青山善充等:《研究會 圍繞新民事訴訟法(第19回)》,載《法學家》1998年1130號,第85頁以下;[日]春日偉知郎:《“相當損害額”的認定》,載《法學家》1996年1098號,第73頁以下;[日]山本克己:《自由心證主義與損害額的認定》,載[日]竹下守夫等編:《講座新民事訴訟法2卷》,弘文堂1999年版,第301頁以下、318頁;[日]畑郁夫:《關于新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載祝賀原井龍一郎先生古稀論文集刊行委員會編:《改革期中的民事手續法——祝賀原井龍一郎先生古稀》,法律文化社2000年版,第505頁。對于從實體法的角度來看也有重要意義的《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從民法學方面也有必要加深對其的理解。同類規定有特許法第105條之3、著作權法第114條之5等。
⑨[日]平井宜雄:《關于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實體法學紀要》,載筑波大學大學院企業法學專攻十周年紀念論集刊行委員會編:《現代企業法學研究——筑波大學大學院企業法學專攻10周年紀念論集》,信山社2001年版,第473頁以下。
B10舊民法證據編第8條規定:“對于受到的損害、失去的利益或者其他原因沒有爭議,僅對應給付的價格的評估存在爭議的場合,法官可以在聽取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獲得進行評估所需必要的元素時,進行評估。”這一規定有以下兩個特征:(1)不僅損害額而且損害事實也成為了其對象;(2)并非從減輕證明度的觀點出發,而是將損害以及對其金額的判斷作為法院的裁量事項。
B11《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244條規定:“僅對損失額有爭議時,法院可以在考慮所有的情況的基礎上,以其自由心證作出判斷,但是法院能夠依據申請決定調查證據或者以其職權決定驗證或鑒定。”這一規定具有(1)以損害額作為規定的對象;(2)將損害額的認定作為應由法官的自由心證決定的問題等特征。
B12對于明治民事訴訟法以后的歷程,伊東俊明有精辟的整理。參見[日]伊東俊明:《對損害額認定的初步研究》,載《岡山大學法學會雜志》2011年61卷1號,第42頁以下。
B13也存在避免僅依存其中某一立場的見解。比如,伊藤真認為《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對應損害類型的不同,既有承認減輕證明度的場合也有承認裁量性評估的場合(作為折中說)。([日]伊藤真:《損害賠償額的認定》,載前引⑧祝賀原井龍一郎先生古稀論文集刊行委員會編書,第52頁以下、69頁。)后面提及的最近的裁判例(除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外其他各級法院的判決)有貼近這一見解的傾向。此外,伊東俊明認為損害額認定程序應分為①當事人對作為損害額認定基礎的事實的主張與舉證階段與②法院基于當事人的主張與舉證,評估損害額的階段,對于前者“并非是對損害額,而是須對作為損害額基礎的事實設定舉證責任,且以此即可”,而且主張與舉證的對象應是,成為損害額認定基礎的“線索事實”——此點是為減輕原告的主張與舉證責任,而對于后者則交由法院的裁量判斷。(前引B13,第57頁。)梅本吉彥認為:“特別是在基于不法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中的損害額計算,并沒有要求數學上的嚴密性,所要求的損害額證明應足以使法院進行公平且合理推定”,“本條規定做如下解釋比較適宜:當作為原告的受害者證明損害的發生以及對損害額進行的證明足以使法院進行公平且合理推定時,法院應基于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以及證據調查的結果,以經驗法則確定相當損害額”。([日]梅本吉彥:《民事訴訟法》,信山社2010年版,第798頁。)
B14前引⑧山本克己文,第318頁;前引⑧畑郁夫文,第505頁;[日]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0年版,第400頁。
B15前引⑧青山善充等文,第85頁以下柳田幸三的發言;法務省民事局參事官室編:《一問一答新民事訴訟法》,商事法務研究會1996年版,第287頁。
這一立場雖然能夠達到該條減輕證明度的目的,但將該條歸屬于法官的裁量卻并不合理。此外,屬于實體法適用的問題也不是該條的解決對象。
(二)裁量評價說
裁量評價說是將《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作為允許法院以裁量評估進行損害額認定的規定,B16也是在意識到通過前述裁量說顯示出的問題的基礎上,對該條進行解釋。
此見解的基礎是:(1)須顧及《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規定與高度蓋然性的損害額證明并不相容,即須顧及對于歸屬于個別損害項目的金額算定,無論怎樣利用蓋然性評估進行強化,但依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假定性與不確定性要素的影響;(2)原本損害額算定就不是傳統立場所主張的事實認定問題,而應作為法官的裁量判斷問題。
此外,該主張認為:第248條以損害事實說為基礎的場合,損害的金額評估從其性質而言應交由法官進行自由裁量,但是這里提及的裁量應認為是以判例法理上發展起來的實體法上的算定方法(在判例與實務上產生的“有關損害額算定的實體法規范”)為依據,且對應由此確立的程度,應認為是符合實體法上的框架的,“第248條是以明文規定向法官指示應以已確立的實體法上的算定方法進行金額評估,并且指示在判例法理尚未確立的領域,以金額評估這一實體法上的概念進行判決的規定”。B17
(三)類似的規定——與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的區別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與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的規定類似。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在規定了“當當事人對是否發生了損害以及損害額或應賠償的利益價值存有爭議時,法院在評估所有有關情況后以其自由心證進行判決”的基礎上,又規定“依據法院的裁量決定是否同意證據調查的請求或者是否決定依據職權命令鑒定人進行鑒定,以及決定在什么范圍內進行證據調查或者鑒定”。 B18
B16
前引⑧春日偉知郎文,第75頁;[日]三木浩一:《民事訴訟法248條的意義與機能》,載[日]河野正憲、高橋宏志、伊藤真編:《民事紛爭與訴訟理論的現在——追悼井上治典先生論文集》,法律文化社2008年版,第412頁以下;[日]高橋宏志:《重點講義民事訴訟法(下)》,有斐閣2010年版,第52頁以下。此外,新堂幸司盡管承認損害額算定最終與經驗原則無關,是僅需要合理理由的純粹的“裁量評估問題”,但也認為,“在實務上正確區分是允許加入部分裁量評估判斷的場合,還是因損害性質而造成其金額的舉證極其困難時僅需裁量判斷的場合,非常關鍵”。[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1年版,第606頁。
B17前引④,第464頁以下。
B18日文譯文引自民事訴訟法典現代化研究會:《各國民事訴訟法參照條文》,信山社1995年版,第295頁。
B19此外,對于有關損害金額評估的過失相抵等減額事由的判斷與第248條的關系,該條文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應做以下處理為宜:當受害人的過失助漲了權利侵害以及損害的擴大時,對于受害人的過失不應適用第248條的規定,而在承認受害者的過失后,在認定受害者的過失比例時則應類推適用第248條。對此而言,因為通說與判例從公平的觀點出發,在過失相抵問題上承認法官有廣泛的裁量權,只要以此處理現實問題,就不會出現問題。
但是,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與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有以下幾點不同:
第一,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不僅在第1項第1款的規定中減輕了對于對象事實的證明度,而且在該項第2款中明確規定了對于該事實的證據評估依法院的裁量進行。相對于此,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僅規定了“法院可以基于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以及證據調查的結果,認定相當損害額”。這也是圍繞該規定的性質產生了前述學說上的對立的原因。
第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不僅對損害額而且對是否發生了損害也交由法院的裁量進行判斷(同條第1項),此外對于當事人之間就財產上的債權額存在爭議的場合,也設有該種類的規定(同條第2項)。相對于此,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僅將損害額作為規定的對象。
第三,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的規定,在對債權額有爭議的場合中,只有被限定在“與債權有爭議的部分的價值相比,要判明與評估債權額的基準有關的所有事實,將會有與其價值不相符的困難存在的場合”才允許法院依其裁量決定損害的金額,而在對損害的發生與金額都有爭議的場合卻沒有這樣的限定。相對于此,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只有滿足“因損害的性質,其金額的舉證極其困難”的條件就允許法院依其裁量決定損害的金額。B19
(四)小結
法案起草者基于證明度減輕說設立了《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但是以判例與實務上采用的損害額算定的見解進行處理①評估嬰兒死亡時的逸失利益以及②評估精神撫慰金等兩類事件時,則難以用證明度減輕說進行說明。
這里的問題是,在上面兩類事件中發生的事實與法案起草者想賦予《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意義,產生了背離。B20即在處理嬰兒死亡評估逸失利益的事件時,名義上是基于具體損害計算的“保守評估”,而實際上是由判例與實務創造的實體性的金額評估(而且是以抽象的損害計算為基礎)。法官在損害事實得到證明而損害金額沒有得到證明的場合,不得不適用基于抽象損害計算的金額評估規范決定損害額。這種處理是與減輕證明度不同性質的處理方法。此外,在處理精神撫慰金的評估事例中,法官進行的精神撫慰金決定則是裁量性與創造性的體現。另一方面,法案起草者設立《民事訴訟法》第248條是為了以下的場合:即在與法官形成心證的關系上,減輕受害者在舉證活動中的負擔,即使沒有對損害額評估的基礎事實盡到主張與舉證的責任,只要對損害事實進行了舉證,就應實現受害者進行救濟的場合。
基于以上論述,并綜合證明度減輕說與裁量評價說的主張,筆者認為,在對損害事實進行了舉證,而對受害者具體發生的損害額度沒有進行舉證時的處理,應有以下三種:
1.以損害額的舉證極其困難為由,減輕證明度,由法官決定相當損害額。
2.基于抽象損害計算的實體法損害額算定規則原本就與基于具體損害計算的實體法損害額算定規則是異質的,法官在依據前一規則認定(適用同規則所必需的)主要事實的基準上,命令賠償相當損害額。
3.只要對損害事實進行了舉證,法院就必須依其裁量決定適當的金額。
這其中,1是基于《民事訴訟法》立法時第248條的宗旨,并充分顧及證明度減輕說的方法。而3是充分顧及裁量評價說的方法。2則是在各種事件類型(嬰兒逸失利益評估場合是其中一例)中,如何適用基于抽象的損害計算的實體法金額評估規范以及如何把握主要事實的問題,這本來是民事實體法上處理的課題。B21
基于起草過程時,對《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理解應以證明度減輕說為準,B22但是同時除3的場合外——已經制定的《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以外——還存在實體法規上的問題,即需要意識到,采用裁量評估說時3的場合,在處理有關《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問題之前,還存在著民事實體法上的問題。
此外,從證明度減輕說來看,《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因為是在具有損害事實的舉證而且損害額的舉證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涉及在法官心證形成層面的行為規范的條款,所以同條規定法官可以決定適當的金額。相對于此,從裁量評價說來看,即使在具有損害事實的舉證而且損害額的舉證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在一定的場合——采取一定措施)法官必須決定適當的金額。B23
三、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原本的適用范圍
根據上文見解,《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發揮作用的場合應為;存在損害金額算定(金額評估)的實體法規范(金額評估規范)的場合,在對符合該規范的事實進行認定的階段,雖然證據不足以證明該事實,但通過減輕證明度,應該給予救濟讓受害者的損害得以恢復。與之相反,以下情形不應包含在該條的適用范圍之內。B24
B20對此請參照前引⑧山本克己文,第313頁。
B21原本從裁量評估說出發,這一文句作為對法院評估規范的說明來考慮,也能夠融入《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中。
B22“其金額的舉證極其困難時”這一《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要件,從裁量評估說特別是平井宜雄的主張難以進行說明。這是因為不管金額的舉證是否極其困難,法官都要基于損害事實并依據確立起來的實體法上的算定方法進行金額的評估。
B23如后所述,最近出現了被認為是采用本文中所述后一種理解(即“必須認定”)的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
B24相對于此,從前述裁量評估說的立場出發,后記3與4包括在《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守備范圍內。在主張證明度減輕說、裁量評估說或者折衷說中又可細分成不同主張,對于如何理解第248條的射程,即使是歸屬于同一學說的不同主張之間,也可能各不相同。對于其差異參照[日]兼子一等編:《條解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1年版,第1388頁以下。
(一)損害事實認定的場合
如前所述,與德國《民事訴訟法》上的類似規定不同,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僅對“損害額的舉證”承認法官可以依其裁量進行評估,而對于“損害事實的發生”則不能適用該條款。而且,即使是屬于“損害額”的問題,比如“沒有寫明請求金額的損害賠償請求”在法律修改時雖然成為了討論事項,但最終沒有被采納。
但是即便如此,所謂第一次財產損害[被稱為純粹財產損害(reinerVermgensschaden;エコノミック·ロス)]因難以明確區分為“損害事實”與“損害額”,所以包括損害事實的發生在內都以第248條為依據進行處理為宜。因此,如過去在鶴崗燈油事件中的案情處理中,B25或者在不適用金融商品販賣法中的損害額擬制與推定規定時,無法根據第248條處理以有價證券報告書等的虛假記載為請求理由的損害賠償事件中,應能夠進行適當的損害金額的認定。B26
(二)少年與嬰兒、家庭主婦等專門從事家務者、外國人等的逸失利益算定的場合
對于少年與嬰兒、家庭主婦等專門從事家務者、外國人等的逸失利益算定,裁判實務以該受害者個人的具體損害為基礎,并在“保守算定”的名義下,根據工資統計數據與平均壽命以及其他客觀、抽象的基準,認定該賠償。即應認為在基于具體損害計算的損害額認定——應成為算定額基礎的事實認定方面上,應在減輕證明度或者在法官心證形成層面上做有利于原告受害者的處理,而只需提出以平均工資等為基準的、保守性的、抽象的、客觀的數值即可。
如上所述,從與證明度的減輕相結合,分析逸失利益的賠償問題的立場出發,少年與嬰兒、家庭主婦等專門從事家務者、外國人等的逸失利益算定與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規定的課題,就減輕證明度而言,可以認為具有同樣的性質。
但是,在裁判例不斷積累的過程中,學說(包括實務家的分析或者主張)逐漸開始在一系列的判例理論中發現,進行金額評估的實體法規范。并在有關少年與嬰兒、家庭主婦等專門從事家務者、外國人等的逸失利益,或者例如車輛、住房等有形物的損害賠償上,發現了以抽象損害計算為基調的損害論以及金額評估規范。B27在這里,裁判實務上的積累在學說層面上與探求金額評估的實體法規范的方向相互結合了。
B25最判平成元年12月8日民集43卷11號,第1259頁。該判決是石油制品的最終消費者,以石油加工販賣業者實施違法的價格協定而給其造成損失為由,要求石油加工販賣業者賠償損失的案件。最高法院認為,石油制品的最終消費者必須對以下事實進行主張與舉證。(1) 基于價格協議的石油制品的出廠結算價格的上升必須與經由對批發價格的轉嫁,造成了在最后的消費階段的現實零售價格的上升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對此作為受害者的最終消費者應負有主張與舉證責任。(2) 因加工生產業者實施違法的價格協議而給商品購買者造成的損失,是因該價格協議而不得不支出的金額,所以對于石油制品最終消費者要求的損害賠償而言,需要能夠說明如果不實施該價格協議,則與現實的零售價格(現實購買價格)相比價格應該低。這也是作為受害者的最終消費者應負的主張與舉證責任。(3)當然,假設沒有實施該價格協議而應形成的零售價格(假定購入價格),并非現實存在的價格,無可否認直接推算這一價格很困難,因此,允許使用根據現實存在的市場價格推定該價格的方法。而且一般而言,從價格協議實施時起到消費者購買時為止,只要作為形成零售價格的前提條件的經濟條件、市場結構以及其他經濟因素等沒有變化,則可將該價格協議實施之前的零售價格(實施前價格)推定為假定購入價格。但是從價格協議實施時起到消費者購買時為止,影響零售價格形成的經濟因素發生了顯著的變動時,則失去了進行上述事實推定的前提條件,因此,不允許僅以實施前價格推定假定購入價格,而是必須綜合分析包括實施前價格在內、該商品價格形成上的特性與經濟變更內容、程度以及其他影響價格形成的因素。(4)此外,既然假定購入價格的舉證責任在最終消費者一方,只要是主張實施前價格相當于假定購入價格,最終消費者仍然負有對支持該推定為合理的前提要件事實,即協議實施時起至消費者購入商品時為止,影響零售價格形成的經濟因素沒有發生重要的變化的事實關系的舉證責任,而如果不能證明上述事實關系,則不允許前述的推定,因此,對其他能夠成為用于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資料,如該商品價格形成上的特征與經濟變動的內容、程度以及其他影響價格形成的要素等,消費者負有主張與舉證責任。
B26前引⑧山本克己文,第318頁;前引B14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書,第401頁。
B27西原道雄的定額化理論是從結合差額說與具體損害計算的傳統立場出發,對于在交通事故賠償中被否定享有逸失利益的嬰兒、家庭主婦等無職業者的逸失利益評估,采用死傷損害說的理論。該理論對傳統損害論提出挑戰。在此,不可遺忘的是需要為抽象評估與計算人的價值,確立實體法規范。有觀點指出,賠償金額的算定并非事實認定問題,而應歸屬于法官創造性的工作范疇,如果是這樣的話,雖然可以理解為僅在金額評估中提倡法官裁量性,但更為適當的理解是:強調探索實體性金額評估規范的必要性。只有這樣,在此延長線上,提倡由法官裁量評估損害金額的平井氏,才能對那些(對平井氏主張中“裁量”的意義有不同看法并存在誤解的)學說,特別是批評性學說的誤解進行批評。即死傷損害說超越了交通事故的問題領域,在出現大量受害者的公害以及藥害等裁判例中,在一定時期內成為以“人的價值平等”為基礎的包括一律請求論(這也與抽象損害計算相結合)的支柱。
如上所述,在這些場合中,不應將具體損害計算作為主要原則后又不認為其為基于“保守算定”的名義而減輕證明度的方法。雖具有“保守算定”的外觀,但實際起作用的是適用基于抽象損害計算的實體
規范——而且,以此為前提明確實體法規范或者明確適用該規范的主要事實——的操作。B28如以該認識為準,則《民事訴訟法》第248條,正如在少年與嬰兒、家庭主婦等專門從事家務者、外國人等的逸失利益算定中看到的那樣,根據基于抽象損害計算的實體金額評估規范進行的評估,在出現問題的場合并沒有起到作用。
(三)權利以及法益的客觀價值的金額評估成為問題的場合
《民事訴訟法》第248條并不是基于依據抽象損害計算的實體金額評估規范,而在問題場合上起作用的規定。其不僅在少年與嬰兒、家庭主婦等專門從事家務者、外國人等的逸失利益算定成為問題的場合上,而且在所有權、知識產品以及其他權利或者法益的相當于其客觀價值的金額賠償成為問題的場合上,以及“最小限度賠償”成為問題的場合上也適用。在此意義上,同情并不在這些場合的守護范圍之內。
(四)精神撫慰金算定的場合
《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能否適用于精神撫慰金,也是一個問題。現在,對于將精神撫慰金的計算交由法官的裁量性以及創造性的活動來認定已無異議。此時,第248條并不和法官裁量判斷與法律評價有關,所以僅就此而言將精神撫慰金包括于同條的守護范圍內缺乏合理性。
當然,此前存在“精神撫慰金具有補全財產損害的作用”一說,即如果對財產損害的基礎事實要求嚴格的舉證,則會造成因舉證困難使賠償遭到否定,在此場合下,由此帶來的不合理由法官的裁量性判斷以精神撫慰金的名義進行補全與調整。這種在判例實務上實施的補全與調整,在學說上也得到了承認。可以說對于該補完部分,已經能夠無需借用精神撫慰金(包括“無形損害”構成)的名義,通過第248條直接作為“財產損害”承認賠償請求。
B28正如本文中所述,對使用統計數值計算逸失利益進行正當化中,有以下〔α〕〔β〕兩種內容不同的構成。〔α〕實損主義=在維持具體損害計算的基礎上,為了減輕證明度而使用統計數值。對于“具有蓋然性”的損害,以“保守”算定,能夠實現并兼顧過剩介入禁止、過小保護禁止等比例原則的損害恢復。這是判例上體現出的主張。〔β〕實損主義=雖然應基于具體損害計算對該受害者遭受的損害進行賠償,但與之不同的其他觀點認為,既然國家將某一權利作為權利進行保障,對于相當于該權利具有的客觀價值的金額,不管實際損害多少,如果不被承認為損害而獲得賠償,則失去了權利保障的意義,應被認作是給予最小限額賠償的損害,而承認其權利客觀價值的賠償。統計數據則可理解為,正是對應每種類型而顯示的權利客觀價值。這是基于死傷損害說的主張以及作者的主張。
B29東京高判平成14年3月13日判タ1136號,第195頁(不正當地終止租賃合同締結談判)。
B30東京高判平成10年4月22日判時1646號,第71頁(基于節稅目的,勸誘以等價交換方式進行公寓建設)。
B31大阪高判平成10年5月29日判時1686號,第117頁;東京地判平成14年9月25日2002WLJPCA09250012;東京地判平成20年11月18日判タ1299號,第216頁;大阪地判平成21年1月20日最高裁HP。
B32橫濱地判平成12年9月6日判時1737號,第101頁(對現房與土地配套販賣的不正當居民抗議活動)。
B33東京地判平成13年4月26日最高裁HP;東京地判平成15年7月31日判タ1150號,第207頁。
B34東京地判平成20年10月30日2008WLJPCA10308016。
B35參見東京高判平成21年2月26日判時2046號,第40頁;東京地判平成21年5月21日判時2047號,第36頁;東京地判平成21年6月18日判時2049號,第77頁;東京地判平成21年7月9日判タ1338號,第156頁;東京高判平成22年4月22日判時2105號,第124頁。
B36札幌地浦河支判平成11年8月27日1999WLJPCA08270006。
B37東京地判平成10年9月18日1998WLJPCA09180003(稅理士在遺產分割之前對有關繼承稅給予不適當的咨詢建議)。
四、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適用情況
(一)對象事件類型的多樣性
民事訴訟法現在被用在合同締結階段的過失(合同談判失敗、說明義務違法等)、B29不正當地終止合同及類似事例、B30各種不正當協作及不正當競爭行為、B31以不正當手段進行業務妨害、B32因流傳或者散布有關他人的虛假信息而造成的逸失利益、B33建筑師違反注意義務造成了建筑物的瑕疵、B34有價證券報告書等的虛假記載、B35理事或董事的利益相反交易、任意懈怠或者其他不正當行為、B36專家責任、B37建筑確認程序的懈怠、B38妨礙強制執行以及其他在執行與保全程序中的不法行為、B39因串通投標而給該地方政府造成的損害、B40倉庫保管商品類的損害行為、B41因爆炸事故而造成的店鋪內用具及烹調材料的損傷、B42采石權侵害、B43日照阻礙與日影受害、B44對他人所有物的不正當使用、B45擅自處理他人的過期商品、B46對他人資料的復制與販賣、B47專利權侵害及類似事例、B48產品相關事故、B49學校事故、B50醫療過失對特殊疾病患者造成的逸失利益、B51交通事故造成的停業損害、B52代用車費用、B53車的評價損失、B54不正當地拒絕再雇用、B55妨礙工會活動、B56工會內部糾紛B57等多種多樣的場合。
B38東京高判平成13年7月16日判時1757號,第81頁。
B39東京地判平成14年4月22日判時1801號,第97頁;大阪高判平成17年3月29日判時1912號第107頁。
B40金澤地判平成17年8月8日判タ1222號,第181頁;京都地判平成17年8月31日最高裁HP;東京高判平成21年5月28日判時2060號,第65頁;名古屋地判平成21年8月7日判時2070號,第77頁;名古屋地判平成21年12月11日判時2072號,第88頁。
B41神戶地判平成15年6月6日最高裁HP(古董)。
B42東京地判平成15年7月1日判タ1157號,第195頁。
B43最判平成20年6月10日判時2042號,第5頁。
B44東京地判平成10年10月16日判タ1016號,第241頁。
B45浦和地判平成11年11月30日判時1725號,第152頁(其他公司的瓦斯設施)。
B46東京地判平成12年9月28日2000WLJPCA09280012。
B47東京地判平成14年3月28日判時1793號,第133頁。
B48東京地判平成10年10月12日判時1653號,第54頁(西咪替丁制劑專利事件);最判平成18年1月24日判時1926號,第65頁。
B49東京地判平成11年8月31日判時1687號,第39頁(三洋電機冷凍庫火災事故產品責任訴訟判決。因火災造成動產消滅)。
B50東京地判平成21年12月17日判時2097號,第37頁(在家介護費用)。
B51東京地判平成15年4月18日2003WLJPCA04180007。
B52名古屋地判平成20年12月10日交通民集41卷6號,第1601頁;東京地判平成21年7月14日交通民集42卷4號,第882頁;大阪地判平成22年1月26日交通民集43卷1號,第23頁。
B53東京地判平成21年4月28日2009WLJPCA04288025。
B54東京地判平成21年10月20日自保雜志1819號,第93頁。
B55札幌地判平成22年3月30日勞動判例1007號,第26頁。
B56廣島高判平成15年9月18日最高判HP(不允許使用集會會場);福岡高判平成16年1月20日判タ1159號,第149頁。
B57東京地判平成22年10月27日2010WLJPCA10278024(不允許進入工會大會、妨礙參加干部競選)。
B58前引B48最判平成18年1月24日。此外,在該案的原判決中,對因不能取得質權而造成的“損害發生”一事進行了否定,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如本文所述,以對于損害額的認定有必要更深入地進行審理為由,發回原法院重審。
B59當然本文中的判決部分,不過是日本最高法院的預備性判斷。實際上,在重審判決基于鑒定結果對損害額進行了認定,并沒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知財高判平成21年1月14日判タ1291號,第291頁。
B60前引B43。
(二)最高法院對《民事訴訟法》第248條適用范圍的擴張
圍繞《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性質,雖然存在著上述見解的對立,但是最近日本最高法院在對同條的適用上,已經超越了證明度減輕的階段,朝著從正面肯定裁量評估的方向發展。從將同條理解為僅在法官心證形成的層面上減輕證明度的規定的立場出發,可以認作是日本最高法院對該條的擴張或者變形。
日本最高法院在專利權人融資者由于專利廳工作人員的過失,而不能取得以專利權出質的質權,向國家提起賠償的訴訟事件中做了如下判斷:B58“因為是由于專利廳工作人員的過失而不能取得本案的質權,所以必須要確定其損害額,假使損害額的舉證極其困難,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規定,也必須基于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以及證據調查的結果,決定相當損害額”。在這里,被質權擔保的債權遲延履行時,在該時間點的專利權的適當價格成為了問題,該問題不應被當做證明度減輕層次上的問題。另一方面,上述判例內容雖然與裁量評估說接近,但是本來在此案件中所涉及的是,在實體法層面上專利權具有的客觀價值的評估問題,這一問題由《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處理是否合適尚有疑問。B59
此外,日本最高法院以侵害采石權的不法行為為由要求損害賠償的事件中作出了如下判決。B60事件的概要是:X(采石業者)對“土地1”與“土地2”擁有采石權。因Y(采石業者)從“土地1”與“土地2”開采巖石,X以Y作為債務者申請禁止Y在“土地1”與“土地2”采石的裁定。該案件中雙方和解,在確認X對“土地2”擁有采石權、Y對“土地1”擁有采石權的同時,也確認該和解協議不妨礙雙方,基于至和解為止發生的采石權侵害,相互對損害提出賠償要求的訴訟。但是此后,因Y在“土地2”進行了采石活動,X以侵害采石權為由,對Y提起了損害賠償請求訴訟。
在此案中,原審基于在“土地2”上的采石權侵害,肯定了和解前與和解后的采石行為造成的損害賠償的請求。但是對基于在“土地1”上的采石權侵害的請求,則以Y在和解后在“土地1”上擁有合法的采石權為前提,而即使Y在“土地1”上和解前的采石量與和解后的采石量能夠有抽象的概念,卻也不能發現將其進行明確區分的基準為由,駁回該請求。相對于此,日本最高法院在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時,在認定了和解前基于Y在“土地1”上的采石權侵害而給X造成的損害非常明顯后,認為:“即使不能明確區分Y通過上述采石行為在本案土地1上開采的采石量,與本件和解后Y基于采石權在該土地上的采石量,而造成損害額的舉證極其困難,也必須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48條的規定,依據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與證據調查的結果,認定相當損害額”。
該事件雖然并不被認為是證明度減輕問題的典型判例,但能夠看出日本最高法院不僅通過確立以“即使在這種場合中,只要能夠認定損害事實已經發生,作為法院就必須認定其認為是合理的金額”為內容的規范(損害金額認定義務),又向裁判評估說前進了一步;而且對“因損失性質,其金額舉證極其困難時”(損害額舉證困難性)這一要件的要求進行實際性緩解。B61
《民事訴訟法》第248條規定的主旨是:在認定“相當損害額”時,應“依據口頭辯論的全部內容與證據調查的結果”。損害額的認定并不是交給法官任其完全自由地判斷。雖說如此,還是希望能夠在判例的理由中記載上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追加的基礎事實以及對該事實的意見。
B61這一問題的整理,參見前引B13伊藤真文,第41頁以下。
The “Commensurate Amount for Damages” under the Judges Discretion
——Centered on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48 in Japanese Civil Procedure Law
Yoshio Shiomi
Abstract:The Article 248 of Japanese Civil Procedure Law which was added in 1996 stipulates that in the case of identified damages, where the nature and compensation amount of damages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rove, the court can confirm a commensurate amount for damages based on all the parties oral defense and investigations of evidence. The concept of damages in the substantive law is the premise of this regulation, in which the theory on the fact of damages has denied the doctrine of balance of amount, and the fact itself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monetary evaluation as losses. Besides introducing theories and case judgment pertinent to this Article, the paper also aims to explicate the applicable effect of this Article in Japan for taking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
Key words:damagedoctrine of balance of amounttheory on fact of damageevaluation of compensation amount for damagestandard of pro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