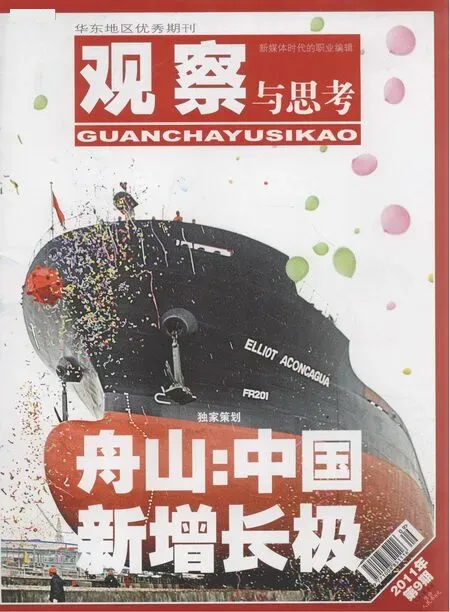應然、實然與必然:馬克思與歷史決定論問題
□王小章
應然、實然與必然:馬克思與歷史決定論問題
□王小章
有兩種含義的歷史“必然性”,一是指歷史發展之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均已被排除這種意義上的必然性,二是指某一事物的出現和存在必須具備某些必需的條件這一意義上的必然性,馬克思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論者,這種必然性與歷史決定論無關,相反,它既為基于某種價值目標的道德批判留下了空間,也以其對“必需的條件”的承認而限制了道德義憤或感傷的泛濫。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實然)的批判是從“應然”和“必然”兩個維度展開的雙向度批判,從這種雙向度批判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評判現實社會是否合理、是否正當的一般標準:一個特定的社會是否合理、是否正當,系賴于它作為人類實踐的形式,在既有的歷史條件下,是幫助促進了、還是阻礙限制人的自由的實現。
必然性 歷史決定論 自由
一
至少自從康德以來,“自由與必然”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如果歷史的進程是必然的,那么自由意志的位置在哪里?我們還能不能基于一定的價值立場對歷史上的各種社會形態、制度作出規范性的評價?如果人是自由的,則種種歷史規定性又作何解釋?社會科學的研究還有價值嗎?“必然論”常常被與“歷史決定論”聯系在一起,而“自由論”則常常滑向唯意志論甚至非理性主義。
在對馬克思的研究理解中,由于馬克思對于歷史進程中所呈現的“必然性”的重視,不少人因此都將馬克思看作歷史決定論者。著名的如卡爾·波普爾,他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著作中一再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看作是與自由和開放社會不相容的歷史決定論。①參見[奧]卡爾·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再如美國社會學家、新功能主義者杰弗里·C·亞歷山大與阿爾都塞認為在馬克思的著述史中存在著一個將馬克思的思想分成兩個大階段的“認識論的斷裂”②[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5-21、218-233頁。。亞歷山大也認為馬克思在早期階段的思想發展中有一個轉變,他用“從道德批判到外在必然性”來表示這個變化。不過,亞歷山大指出:“一般認為,自由與必然的關系是馬克思著作中的核心問題。在我看來,在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這種關系表現為一種矛盾,即:馬克思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信奉自由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從理論上論證個人行動要取決于外在的集體秩序。集體秩序的決定作用在馬克思理論中產生了一個悖論,這一悖論時隱時現并導致對其原著的不斷的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反意志主義(antivoluntaristic)的社會理論,但卻在意識形態上激發人們能動而自主地變革社會。無論如何,對集體秩序的合理結構的描述是馬克思最為得意的地方;而在他本人看來,正是他關于集體秩序的演變及其對個人和群體的必然影響的觀點使他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家’。”①[美]杰弗里·C·亞歷山大:《社會學的理論邏輯》(第二卷),夏光、戴盛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3-14頁。無論是上面引文中的“矛盾”,還是所謂“悖論”,都清楚地表明,在亞歷山大看來,必然性和自由是不相容的,強調外在必然性的馬克思和信奉自由的馬克思是不相容的。而由于馬克思“最為得意”的是“他關于集體秩序的演變及其對個人和群體的必然影響的觀點”,因而,(成熟的)馬克思沒有為自由留下余地,也沒有為對歷史上和現實中存在的社會形態進行規范性道德評價留下余地。但果真如此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必然性”的所指作進一步的明確和清理。事實上,存在著兩種含義的“必然性”。一是指歷史發展之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均已被排除這種意義上的必然性,即由A必然到B,不可能出現其他,由B必然到C,也不可能出現其他;二是指對于某一事物的出現和存在來說必須具備某些必需的條件這一意義上的必然性,即如果要出現或存在X,就必須具備什么什么條件,缺乏這種條件或這種條件不充分,X就不可能出現或繼續存在。顯而易見,第一種意義上的必然性確實與自由不相容,這種歷史必然性實際上排除了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任何主體性自由和價值選擇的可能性,從而也排除了對現實社會進行任何規范性道德批判的可能性。但筆者認為,馬克思并不是這種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論者。馬克思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論者。這種歷史必然性實際上是某種特定形態、特定內涵的社會,或特定的人類實踐,在既有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存在、展開或向某個特定的方向、目標發展的現實可能性,但是,它并不意味著社會或人的實踐只能以這種形態存在、展開,或只能別無選擇邁向這個方向或目標。打個比方,如果你想在某個地方種植某種植物,這個地方就必須具備一定的氣候、土壤、水文等條件,否則,即使你種下了,它也不能存活。但是,這并不表明在這個地方你只能種植這種植物。由此可見,這第二種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并不與自由不相容。也正因此,這種必然性既為對現實社會的基于某種價值目標的道德批判留下了空間,也以其對“必需的條件”的承認而限制了道德義憤或感傷的泛濫。
二
最容易讓人把馬克思看作歷史決定論者的,也許就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所做的那段經典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
但是事實上,即使在這段經典表述中,我們也看不出馬克思與上述第一種意義上的必然性論者也即歷史決定論者有什么關聯。相反,馬克思主要地恰恰是從一種社會形態、一種生產關系如果要出現和維持下去,就必須要有什么必需的條件和前提這一角度,來闡發他的唯物史觀的。確實,馬克思說人們會“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那只是說,人們的生產、生活活動脫離不了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 (也即,“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頁。),而這種關系是與一定的生產力水平相應的,但馬克思并沒有說這種關系的具體形態一定是什么或只能是什么。馬克思也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那也只是表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是其他一切生活的基礎和前提,但馬克思同樣并沒有說在這種基礎和前提下產生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別無選擇地一定是什么。馬克思還說“不是人們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但那也只是表示,人們的意識只有聯系他們的現實社會關系才能得到解釋和理解——這也正是后來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馬克思確實表示過,當生產關系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的時候,就一定會出現社會革命,但革命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否定性的行動或實踐。因此,馬克思借此表明的,無非是:當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得以存在的必需條件不再存在時,它就維持不下去了,但馬克思并沒有從正面說取代這種生產關系的,也即由革命所助產的,必定是哪種生產關系。最后,馬克思確實提到“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但那只是對歷史的客觀描述與回顧,并沒有試圖將它們論證為歷史發展之別無選擇的唯一可能的進程,這和后來斯大林所搞的五階段模式(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完全不同的。
由上述可見,馬克思固然重視并努力揭示歷史發展過程中那些基礎性的前提條件,承認一種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出現和存在有其必需的條件這種歷史必然性,但是,他決不是那種沒有為自由留下余地的歷史決定論者。當然,如果說,歷史決定論的含義是“由于缺乏某種必需的條件因而決定了某種事物不能產生或不能維持下去”,那么,我們也可以說,馬克思是歷史決定論者。
正因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既為自由、進而為堅持道德價值承諾留下了空間,同時又兼顧和承認“歷史必然性”,因而,馬克思對于現實社會的態度既不茍同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論調,也不僅僅是純粹從“應然”的價值立場出發而抒發道德義憤。馬克思對于現實社會之經濟體制、政治制度、文化意識等等的分析批判是一種將價值目標(“應然”)和既有的歷史條件所提供的現實可能性(“必然”)相結合的批判,是從“應然”和“必然”兩個維度對“實然”所作的審視評判。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論定現實社會形態是否合理、是否正義,不能僅僅依據在這種社會形態的經濟體制、政治制度、文化意識“規定”下的實踐是否符合“應然”意義上的價值標準,還要看處在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這個社會所既有的客觀物質條件(生產力)為這種應然的價值的實現提供了怎樣的可能性,而這個社會的各項制度是推動、促進了這種可能性的實現,還是阻礙、扼制了這種可能性的實現。因此,作為一種批判理論,馬克思的理論始終是雙向度的,它總是以現有社會自身的各種客觀歷史可能性或者說潛能,結合其關于社會發展的應然方向或者說價值目標,來測度評判這個社會。而之所以要堅持這種雙向度,要將基于價值立場的道德批判和基于科學診斷的歷史批判結合起來,根本的理據就在于:在“應然”和“實然”之間,還有一個“必然”。屬于“必然王國”的活動(對于人類活動來說,就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頁。)固然不屬于馬克思所說的嚴格意義上自由范疇,但在同樣嚴格的意義上也不屬于“異化”,因而也不是馬克思所批判的目標。
三
馬克思的這種雙向度的批判集中體現在他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擔綱者資產階級的分析批判中。一方面,馬克思憧憬人的真實的自由或者說解放,憧憬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在“應然”的價值取向上,馬克思將人定義為自由自覺的實踐者,而社會,作為人類實踐所必需的形式,“應該”是人的潛能在既有的歷史條件所許可的范圍內得到充分的、全面的發展的條件。②參見王小章:《從“自由或共同體”到“自由的共同體”——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與重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5頁。社會的最高成果應該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頁。)。另一方面,馬克思深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277、85頁。由此,馬克思對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擔綱者資產階級的批判就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歷史性的肯定和歷史性否定的辨證統一。
站在人類自由、人類解放的歷史性演進的高度,馬克思充分肯定資本主義及其擔綱者資產階級的歷史功績和地位,肯定它們“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既肯定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終結了封建制度下的人身奴役,確立了消極意義上、形式性的自由權利,更以無以倫比的激情、詩一般的語言贊頌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擔綱者所取得的物質成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277、85頁。資產階級所取得的這種成就之所以值得馬克思如此贊頌,就在于,它們既表征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成就,表征了人的力量、人的創造性,同時也推進了“實現真正的解放”所必須使用的“現實的手段”,從而為進一步趨近人的潛能的充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也即為進一步靠近自由這一理想目標提供了進一步的前提條件或者說現實的可能性。
但資產階級社會的根本問題恰恰也就在于,它一方面創造了如此巨大物質成就,從而為實現更大的自由、為人的解放提供了更大的現實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卻不僅不可能幫助將這種自由可能性最大程度地轉變為每個個人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反而在壓制著、窒息著、扼殺著這種可能性。換言之,作為人類勞動或者說實踐的形式,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包括其經濟、政治和文化)主要不是表現為人的潛能在既有的歷史條件所許可的范圍內充分全面發展的條件,而是表現為自由實踐的壓制性因素,限制人的實踐在業已具備的歷史條件下原本可以達到的廣度和深度。而之所以會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這個社會中,這些物質成就都是建立在剝削、建立在奴役勞動的基礎上的,是在分裂為階級的社會成員之間的沖突對抗中取得的,同時也表現為社會成員之間的對抗力量,而不是所有社會成員所普遍分享的聯合力量。由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對于絕大多數個體來說,這種物質成就不僅不是他獲得自由的前提條件,而是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和他離異:“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277、85頁。正因為“擴大了的生產力”是一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權力”,因而它構成的是他們自由的限制而非條件;也正因為這種“擴大了的生產力”或者說物質成就表現為社會成員之間的對抗力量,因而,對于與這種物質力量緊密相聯的自由來說,他人也就不是“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自己自由的限制”。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頁。這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以其物質成就為自由創造了更大的現實可能性,但在這個社會的制度,卻不是將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而是扼殺了這種可能性,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之不義的根本所在。
從馬克思之批判理論的雙向度,以及以此雙向度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批判,我們實際上可以得出一個評判社會是否合理、是否正當的一般標準,或者說一個進行社會批判的參照:一個特定的社會是否合理、是否正當,系賴于它作為人類實踐的形式,在既有的歷史條件即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所提供的可能性下,是幫助促進了、還是阻礙限制人的豐富潛能的全面發展,人的自我實現,人的自由?我想,這無疑也應該是我們今天審視現實社會時所應堅持的基本標準。
責任編輯:孫艷蘭
作者王小章,男,浙江大學社會建設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 31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