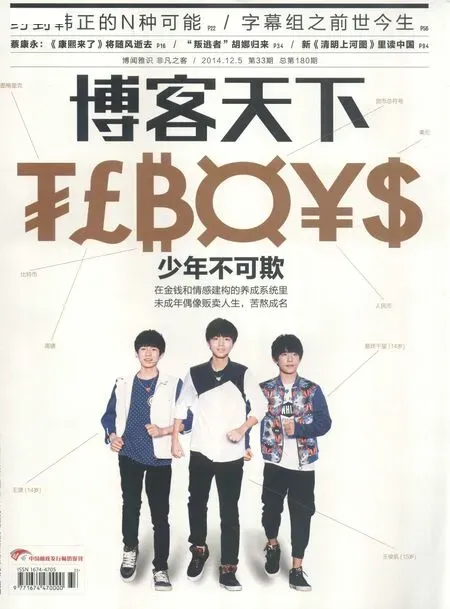墻是小說家必須打破的障礙
墻是小說家必須打破的障礙
小說營造的世界似乎只能帶來無力且轉瞬即逝的希望,然而每個個體擁有的想象的權利卻清楚存在:用一種安靜且持續的努力唱歌,說故事。
柏林墻倒塌已有25年,我初次拜訪柏林是在1983年。當時,這座城市依然被隱約可見的墻分成東、西兩部分。游客們可以進入東柏林(民主德國),但是必須穿過重重關卡,且須在午夜的鐘聲敲響前回到西柏林(聯邦德國),就像舞會上的辛德瑞拉。
那一次,我和一位朋友,以及我的夫人一起去看東柏林歌劇院的一場莫扎特的《魔笛變奏曲》,演出和氛圍棒極了。但是時鐘的指針無可避免地走向了12點。我清楚地記得急匆匆趕回查理檢查哨的路途。我們剛好在12點的時候趕回那里。在所有欣賞《魔笛變奏曲》的經歷中,這一次是最驚險的。
當1989年柏林墻終于倒掉的時候,我至今仍記得當時的自己感覺松了一口氣。我告訴自己:“冷戰結束了,毫無疑問,一個更和平、更積極向上的世界就在眼前。”我想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抱有同樣的想法。然而很遺憾地,這種放松的感覺并未持續很久。中東持續動亂,巴爾干半島上烽煙四起,恐怖襲擊接踵而至。當然,還有2001年紐約世貿中心發生的不幸。我們迎來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愿望被現實摔得粉碎。
作為一個小說家,“墻”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意象。在我的小說《世界盡頭和冷酷仙境》中,我描述了一個想象中的被高墻包圍的小鎮。在這樣的小鎮里,你只能進入,卻永遠無法離開。在我的小說《奇鳥行狀錄》中,主角坐在一個深井的底部,然后穿越厚厚的石墻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當我得到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我作了一個名為“高墻和雞蛋”的演講。我提到了墻,以及與之對抗的雞蛋。面對高墻,我們究竟有多無力?我作那次演講的時候,加沙正發生激烈的戰斗。

演講人
村上春樹
地點
柏林
背景
日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領取了德國《世界報》頒發的世界文學獎。在演講中他指出,盡管世界“至今還有許多高墻鐵壁”,但想象并試圖看到一個“沒有墻的世界”依然重要。
對我來說,墻是把人與人、價值觀與價值觀分隔的象征。在某些情況下,一堵墻能夠保護我們,然而為了保護我們,它也隔開了其他人。這就是墻的邏輯。一堵墻最終將成為固定的系統,拒絕其他系統的邏輯。有時候,這種拒絕是暴力的。
甚至我經常覺得,我們摧毀一堵墻,只是為了建造另一堵墻而已。這里的墻,可以是現實意義上的,亦可以是包圍我們思維的無形的墻。這些墻告訴我們不要遠離目前的所在,也告訴別人不要接近。當一堵墻最終倒塌的時候,世界看上去將很不一樣。然而當我們放松地呼出一口氣的時候,我們發現在世界的另一端還有一堵墻—一堵種族、宗教、不寬容、原教旨主義、貪婪以及恐懼的墻。我們能否在沒有墻的世界里生存?
對于我們小說家來說,墻是必須打破的障礙,別無他法。當我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們其實在穿墻而過。當然,是象征意義上的。我們穿越橫亙在現實和非現實之間、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墻。我們看見墻另一邊的世界,然后回來自己的這一邊,用筆描述這些我們看到的細節。我們不對墻的意義作評判,亦不對它的角色評頭論足。我們只是嘗試準確地描述看到的場景。
當一個人被小說感動或者為之激動的時候,他實際上和作者一起穿越了這堵墻。當然,當他合上書的時候,仍停留在原地。讀者周圍的現實絲毫未變,也沒有任何現實中的問題被解決。然而讀者仍能清晰地感到他打破了一堵墻,抵達了某些地方又復歸。他會覺得自己已經離開了起始點,即使這個距離微不足道。我一直覺得,這種感覺,是閱讀小說中最重要的體驗。這種能夠切實感受到的自由,這種只要你想,就能穿墻而過的感覺,是我無論如何最為珍視的。我將為之盡全力寫出更多的作品,并與盡可能多的人分享這些故事。
我們當今世界所面對的問題自然無法用這些閱讀小說帶來的感知來解決。小說,很不幸地,并沒有那種立竿見影的效果。通過小說我們能夠想象出一個生動的、與現今這個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現實的黑暗、暴力與諷刺面前,這似乎是一個無力且轉瞬即逝的希望。然而每個個體擁有的想象的權利卻清楚地存在:用一種安靜且持續的努力繼續唱歌,說故事,不失初心。
在一個到處都是高墻的世界,想象并在腦海中清晰地看到一個沒有墻的世界,會帶領我們將之變為現實。我將繼續相信故事所擁有的這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