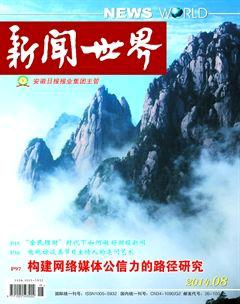解讀群體心理
熊一丹
【摘 要】本文對勒龐《烏合之眾》一書的主要觀點進行了歸納,并從批判性的角度對該著作的不足之處進行了回應。同時將勒龐、塔爾德以及弗洛伊德的群體心理研究進行了比較,工結合了網絡時代的特點,指出盡管網絡使理性的公民參與成為可能,但勒龐指出的群體的缺點仍然存在。
【關鍵詞】群體心理 勒龐 《烏合之眾》
18世紀歐洲社會的劇烈變革剛剛沉淀,法國大革命的塵囂還未散盡,而工業革命與技術的進步又為19世紀帶來了喧囂。正是在這樣一個動蕩與變革交織的背景下,勒龐對民眾的非理性行為有著直觀的認識,這構成了他思考與探索群體心理的基礎,而這種探索也體現著他對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大變革中呈現出的問題的深深恐懼與擔憂。
一、勒龐筆下的“暴民”
作為法國早期社會學的產物,勒龐的《烏合之眾》這本書開啟了群體心理學的大門,他試圖歸納出群體的心理特點,并為個人在群體中的心理異化尋找原因。在前言里,勒龐開篇即指出“群體的無意識行為代替了個人的有意識行為,是目前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之一”。①
在勒龐看來,群體能夠吞沒個體的特性,使聚合在一起的個體發生同質化的轉變,并作為整體形成新的特點。對于群體,無論作為個體是多么富有學識和批判思維,當他們聚合到一起形成群體時卻表現得智力低下,不受理性的影響,沖動易變,急躁偏執。在勒龐的筆下,群體(the crowd or the mass)已經成為了“暴民”的代名詞。
對于群體為何為表現出這樣的特性,勒龐給出的解釋是,首先群體從數量上具有壓倒性,“法不責眾”的心理讓群體中的人擺脫了制約感,因而也導致了群體的沖動與不負責任;其次,群體之間存在傳染性,從眾心理由此而生;第三個原因則是群體極易受到暗示,勒龐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暗示也是勒龐自己對于群體之間的傳染性給出的解釋。傳染性暗示的起點是群體中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幻覺);而群體受這種歪曲的暗示,形成了集體的幻覺。勒龐將集體狀態與催眠狀態進行了類比,從催眠的角度來解釋群體心理表現出的無意識狀態。
在探討領袖與群體的關系時,勒龐認為領袖與他人無異,也是群體觀念的使徒。一個人之所以能成為領袖,無非出于兩個原因:一是有狂熱的信仰,二是有堅強的意志或活力提供給大多數缺少這些品質的人,這些人因此感到興奮,服從的意志被激發。領袖甚至不需要足智多謀,不需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需要的是一流的操控能力,他能夠調動人們的想象力,善于言辭,只需掌握斷言法、重復法和傳染法就能動員群體。從某種程度上說,領袖充當的就是催眠師的角色。
總的來說,勒龐的理論核心就是“心智歸一法則”(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即當個人進入了群體,那么個體在平常狀態之下的個性就會因為群體之間的相互感染而被削弱,甚至消失,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漸漸地趨向一致,表現出非理性、低智商、情緒化的特征。
二、勒龐、塔爾德與弗洛伊德的群體心理研究比較
法國學者塞奇·莫斯科維奇在《群氓的時代》一書中對勒龐、塔爾德以及弗洛伊德的群體心理研究進行了梳理,在三者互相重復又充滿矛盾的學說中尋找一貫性,并為其中的矛盾尋找可以解釋的原因。
從這三位學者的研究中,我們能看到很多有趣的相似點,體現了三者之間的繼承與融合。例如,勒龐認為,群體呈現出女性化的特征,“群體情緒的簡單和夸張所造成的結果是,它全然不知懷疑和不確定性為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樣,一下子便會陷入極端。”②近代法國對女子教育的忽略使得女性顯現出更多非理性的特征,因而在勒龐眼里,女人往往理性不足,感性有余。而在塔爾德看來,如果說群體是女性,那么組成群體的則是服從、聽話、放棄男子本色的男人,群體組成對于男人來說意味著閹割。更進一步說,領袖與群體的關系就是同性戀者的關系。弗洛伊德則進一步發展了領袖與個人之間的聯系,在其著作《群里心理與自我分析》中,他認為領袖與個人之見是“力比多聯系”,是愛的聯系,這種愛雖然不是性愛,但是仍屬于性本能沖動的表現。③
盡管三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的學說也存在著不同的地方。塔爾德相對于勒龐的最大的突破在于,他分隔了群體和公眾這兩個不同的概念,認為交流是區隔兩者的主要因素。并且結合報紙這種媒體對社會的影響,討論了輿論與公眾的關系。他認為相比于直接接觸時的近距離暗示,大眾媒介帶給人們的是遠距離的暗示,這是一種“純粹的神合”。前者是屬于群體的,而后者則是在公眾中才存在的。而從領袖與群體的關系來看,新聞工作者在這里又充當的新的領袖,成為了新的催眠師。塔爾德還認為,相比于群體,公眾的行動更為緩慢,更為溫和,而且公眾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它助長了輿論的潮流。而弗洛伊德的學說雖然是對群體心理的研究,但是他將原因又歸于個人心理層面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待群體心理,例如他將無意識定位于人的力比多沖動。
然而無論是勒龐與塔爾德開創的群體心理學還是弗洛伊德對群體心理學的繼承及其個體心理研究,都告訴我們非理性因素對人的影響是強大的,而且在很多時候這種因素主導著我們的頭腦,解構著啟蒙運動以來歐洲的理性主義。
三、《烏合之眾》的得失
作為群體心理學的開山之作,勒龐的功勞在于為這門學科搭建了一個框架,指出了后人應該關注的重要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早期的學術成果,《烏合之眾》顯示出了諸多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勒龐使用的主要是經驗的觀察與總結加上假設與推斷,論斷較多,對現象的歸納與描述比較充分,但并未使用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因而從科學性方面來講,《烏合之眾》則顯得比較粗糙了。
在論據的選擇方面,勒龐也主要從法國大革命等轉折性的歷史事件作為參考資料。然而不得不說,在人類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平凡而節奏緩慢的,蕩氣回腸的只是其中間斷出現的幾個篇章。對于勒龐而言,他更關注的似乎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群體心理,即社會動亂、革命時期的群體心理,而非普遍性的規律。
另外在論證過程中,《烏合之眾》除了不斷發出各種論斷外,其它基本上是歷史材料的堆砌,現象的疊加,而缺少對原因的探討。
在閱讀《烏合之眾》時,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作者對于女人、種族、社會主義以及仍然以原始方式生活的族群有著嚴重的偏見。正如前文所說,對于群體暴露出來的種種缺點,勒龐均歸因于群體的女性特征,并將女性放在生命的“低級進化形態”類別中,并且認為女人是沒有主見,容易受暗示影響并走向極端的。同樣被劃入這個類別的還有兒童和“野蠻人”。在面對女人、拉丁民族、社會主義的時候,勒龐所做的是從自己立場與生活經驗出發去揣測,而沒有站在歷史的、社會的角度上去尋找這種差異的原因,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創造和領導文明的,歷來就是少數只是貴族而不是群體。群體只有強大的破壞力。”④從中也可以看出勒龐對精英主義偏好與取向。
另外勒龐對于群體的劃分并不十分清晰,盡管他將群體劃分為了一致性群體和同質性群體,但這兩類群體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在勒龐的劃分中,各類別的群體并不是窮盡且互斥的,例如身份團體就與階級、派別等存在著交叉。
四、網絡時代的“烏合之眾”
在勒龐的年代,盛行媒介的還是報紙,今天我們已經實現了從廣播到電視再到網絡的飛躍。互聯網背景下,群體是否發生了新的變化?有學者認為,網絡輿論已經顛覆了勒龐對群體的假設,網絡上的群體不再是一個情緒化集體,而趨向成為個體的相加……今天,網絡上的群體表現出了與勒龐筆下的群體不同的特征。大量的論壇出現不同觀點的激烈辯論,即使孤軍奮戰的網民也絲毫不加退讓,標新立異的網絡輿論傳播特征激發了個體的批判能力。”⑤人們認為網絡時代是一個公眾輿論崛起的時代,是“庶民的勝利”。這樣的看法有他的合理性,畢竟“如果公共觀點是在缺少爭論的情況下達成一致,與總有不同意見者不斷提出改進建議相比,人們就失去了接觸不同觀點的機會。因此,與開放的社會相比,在封閉的社會里,更容易出現普遍的無知。”⑥網絡作為一個平臺無疑為公共話題的充分討論提供了可能。
然而筆者認為,我們還不能忽視勒龐的“烏合之眾”理論。至少現在,我們常常看到的是一個不那么理智的網絡群體,大量重復性的言論和意見充斥其中,人們面對一個事件選擇自己的看法時,似乎更多的是從固有的觀念出發,而不是經過自己的思考。而這固有的觀念也并不是經過頭腦加工的產物,反而常常是在重復法、斷言法和傳染法的影響下悄悄植入的。在信息井噴的時代,人們反而失去對信息與觀念的思考能力。暗示仍然存在,集體的幻覺也常常出現,否則謠言也不會變本加厲地傳播,人們也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的常識。
勒龐的這本書首版已逾一個世紀,他所探討的話題卻愈久彌新。也許一部學術著作最重要的不在于形式的規整,優秀的學術研究應該開辟新的窗口為后來的研究開辟不同的路徑,或者應該將某一領域繼續向前推進。而勒龐的《烏合之眾》就屬于前者。憑借對重大問題的敏感性,即使是在如今新媒體環境下,勒龐的許多論斷仍然是適用的,這也證明了其敏銳的洞察力與預見能力。□
參考文獻
①④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1
②塞奇·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33
③劉瑾璐,《論弗洛伊德的社會群體傳播思想》[D].吉林大學,2009
⑤劉朋,《網絡政治輿論主題的特征:烏合之眾的反叛》[J].《現代傳播》,2010(11)
⑥第默爾·庫蘭:《偏好偽裝的社會后果》[M].長春出版社,2005:17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