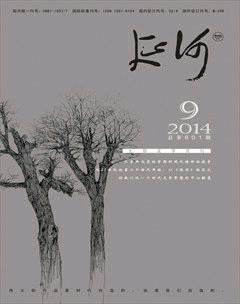鄉下的母親
甫躍成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你已步入正軌,
習慣生活的常規狀態,
不必擔心各種意外。
一切幸與不幸,都跟你保持
恒定的距離。你不必沒事找事,
聊閑天,也不必自己思考
下一步該怎么走。
所有環節都已安排妥當,
就等著你日夜勞碌,去成為
一個充實的人。
這個世界吵吵嚷嚷,
不住地喊著你的名字。
隨著喊聲,你東奔西跑,
甚至沒有時間
停下來,感到無聊,或者想想
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
這么多年,你忙得要死。
可是每次喝醉,你就開始失落,
抱怨自己兩手空空。
你的名字
在這個被寫滿的城市,
隨處可見你的名字。
我在一本書中,一句話里,
一張迎面撲來的廣告牌上,
無時無刻不會碰到它們。
三個漢字,像三個親密的姐妹,
遇上一個,就讓我想起另外兩個,
想起它們所共同代表的那個人——
那個人走了很久,除了這三個漢字
什么也沒給留下。從此,
這三個字,就預先抵達了
一切我所能抵達的地方,
好讓我無論走到哪兒
都要一遍又一遍地
跟它們相見。每次邂逅,
我總是假裝有事,扭頭避開;
有時多看了一眼,關于你的記憶
便鋪天蓋地地襲來。
鵲踏枝
獨上高樓,望江楓漸老,
汀蕙半凋,滿院子的敗紅衰翠。
望近處的人遠去,遠處的人更遠,
一條大江再不回頭。想象中,
你是謫居他鄉的詞客,細雨落花,
雞聲圓月,都令你百感交集,
對天地人生多有體悟。
電梯載你上二十八樓。
二十八樓,古人從未抵達的高度。
昨夜沙塵暴自北方襲來,
獨上高樓,望無數樓盤拔地而起,
遮斷天涯路。關上窗,你
和衣而睡,喇叭聲中你徹夜未眠。
庭院
庭院空曠。除了三月
別無一物,除了天氣更無消息。
花影凌亂,草木瘋長,
鶯的嗓門一聲高過一聲。
溫軟的風翻過柳梢,掀開窗簾,
捆住誰的腰肢,令她失眠,
咬著牙說不出一個恨字?
千里萬里的江山關在門外,
一寸一寸地柔腸結于腹中。
錦瑟年華,付與蘭舟、
秋千水榭,總是荒廢。
繁華街巷,誰的庭院如此空曠?
一個人無端遠去。
一個人再不歸來。
她怕黑
她怕黑。每個夜里,她想盡辦法,
仍難以入睡。她睜開眼睛,
只看見無邊的黑暗;她用被子捂住頭臉,
黑暗就鉆進了她的被窩。
她向左翻了七次,向右翻了八次,
最后平躺在大床的正中。
她聽見后腦勺的動脈,在這安靜的黑里
突突地跳動;她聽見無數只蚊子
在她的顱腔里亂轉,以此冒充她的耳鳴。
她忍無可忍,就坐起身來,
伸手摁亮了頭頂的吊燈。
黑暗驟然退卻,帶著它所包藏的恐怖
逃得無影無蹤。只留下四面墻
在離她遠遠的地方,不容置疑地白著。
白得教她害怕,白得像誰
空空的內心。
職員
她們兩眼發直,神情麻木,
收款,驗鈔,敲擊鍵盤,印制單據,
對于對面的男士,并不抬頭多看一眼。
她們很少說話,一旦開口,
必須得到確切的回復,
任何驚人的答案,都難以讓她們
為之一震,或者稍作遲疑。
她們也許剛剛結婚,度完蜜月;
也許正在為兒子
上哪個高中糾結不已;也有可能
正在等待醫院的電話,
為父親的高血壓憂心忡忡。
你不知道她們擰緊的眉頭
暗示著什么,也不知道
她們臉上的倦意,是由什么境況造成。
她們鉆進工作服,端坐如儀,
偷偷抽走真實的自己,
令窗口外的長龍,無法窺視,
猜不透她們復雜的故事,只留下一套
熟練的操作,呈現在世界的面前。
你習慣于咬著牙等待
你習慣于咬著牙等待,
懷著一個美食家的夢想,
卻不敢聲張。鍋碗瓢盆,
這些被我厭棄的發明,
在你眼中,有著致命的誘惑。
偷偷激動過后,你轉過身去,
將一盞邪火狠心掐滅。
你對日子有些隱約的構想,
無處講述,只是暗暗地熬。
慢工出細活,溫水煮青蛙。
暴烈的沖動、鉆心的疼
讓你有些失控,又總是被你
一次次壓在刀下。
可是你從不問我
一塊石頭如何煮熟,煮熟了
又如何當成一塊芋頭
整個兒吞下。多少年來,
你無辜地看著我,張了張嘴,
卻無話可說。
鄉下的母親
她的勤勞是一種癮,一旦養成
就難以戒掉。鄉下的母親
老實保守,永遠趕不上
城里人的時髦。她不扭秧歌,
不打牌,不提著鳥籠
到公園里亂轉;周旋于鍋碗瓢盆
與拖把之間。日漸縮短的睡眠
使她有充分的閑暇
取代保姆。買米買菜,這點活計
遠不能滿足她的需求;她搶過了
接送孫子上學的任務,后來,
她還學會了使用洗衣機。
一天二十四小時,二十三小時
她都已經安排妥當。
沙發已經整理了兩遍,
桌子已經擦了又擦。剩下一小時
她實在找不出該做些什么。
就像她飯后找不到一支煙的丈夫,
她站不是,坐不是,兩只手
不知是該揣進口袋里
還是放在膝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