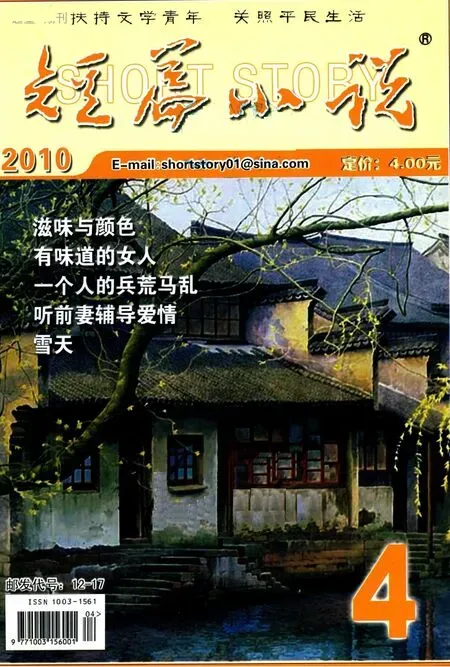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荒誕歲月五題》的人性思考
張 靜
《荒誕歲月五題》的人性思考
張 靜
當高爾基提出 “文學即人學”的命題之后,很多作家都嘗試著圍繞這一命題所蘊涵的人文內涵進行創作。在為世界文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文藝理論工作者也對此展開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雖然對這一命題的精確出處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文學即人學”的確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歷史走向,并一直延伸至當下的中國文學。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 “大寫的人”的消解以及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也成為促使我們認真思考這一問題的關鍵性外在因素,在市場經濟因素的主導之下,文學一度偏離了自己的發展方向,誕生了一批并不符合 “文學即人學”命題審美內涵的作品。
一、人學視野下的文學創作
筆者無意于深入探究高爾基是否提出過 “文學即人學”命題的真偽,它的客觀存在是無法否認的。正如錢谷融先生所說:“言 ‘文學即人學’,是以人作為文學描寫的中心,是以人作為評估文學的尺度。而人類文明史上以人作為評價事物的尺度并非自 ‘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始。”[1]正是由于在文學客觀存在的漫長歷史中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們秉承著以人作為評價事物的尺度不斷去創造新的作品,我們才能真正獲得如此輝煌的文學史,才會有如此厚重的文化底蘊。
由此可見,“文學即人學”是我們對于文學理解方式和創作原則的一種帶有總結、歸納性質的理論升華,它不僅可以涉及古典文學所包蘊的豐富情感信息,也囊括當代社會的復雜內容。當我們理解了這一點之后,在以 “文學即人學”的歷史命題重新審視小說《荒誕歲月五題》所講述的故事就會發現,作者所表現的正是一個 “人學”精神缺失了的時代發生的荒誕的故事。
小說由 “荒誕的夜”“魚宴”“逃離黃昏”“白菜地”和 “紅蘋果”五個部分共同構成。在前四部分中,作者所講述的故事主要以人性的缺失作為內容,通過展現小說中的主人公 “我”前后所經歷的各種或離奇、或荒誕、或恐怖、或憂傷的故事,向讀者展現了中國社會在20世紀60~70年代的特殊境遇。對于生活在當代社會的讀者而言,他們或許已經無法真正理解人性的缺失帶給人類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沖擊究竟是什么。但我們應該能夠理解在作者所講述的故事中 “我”是在怎樣的力量鼓舞之下可以盡情地摧毀“地主老財”的墳墓、棺材,當時的人們甚至可以直接用棺材的木料制作家具。
破 “四舊”的時候,我們專撿大戶人家的墳挖,因為我們覺得大戶人家肯定都是地主老財,只要看到這樣的墳,我們個個奮勇爭先,不一會兒巨大的墳頭被鏟平,黑漆或紅漆的棺木很快也露了出來。我們將棺木撬開,有的棺木已經朽爛,有的棺木依然完好,把棺木撬開后,將骨殖隨便扔在地上,再踩上幾腳,然后我們就揚長而去,再去挖另一座墳。
“我們”隨意踐踏著逝者的骨殖,甚至用 “大戶人家”的棺材去做家具。如此瘋狂的一幕僅僅是作者筆下人性淪喪時代的縮影,人們對于生命的敬畏、對于死者的尊重都徹底拋棄。他們所拋棄的正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 “道德性”,誠如康德所說:“樸素單純,(無藝術的合目的性)就是自然界在崇高中的,也就是道德性在崇高中的樣式,這道德性正是第二個 (超感性的)自然。”[2]當 “我們”徹底遺忘自身的 “道德性”,也就意味著自己在人性的視野中陷入到無法自拔的迷茫之中。
作者在小說《荒誕歲月五題》中所講述的故事正是生活在當代社會的我們從人學的角度去審視曾經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是如此的荒誕,甚至略顯恐怖,卻是發生在 “我們”身上最為真實的故事。作者的講述似乎是對歷史的反思和回顧,更多的則是希冀于生活在當下的我們能夠喚醒沉睡的良知,從人學的角度出發去認真研究曾經發生的一切。人學視野是我們嘗試著理解文學的一種途徑,對于生活在不同時代的讀者而言,是否存在著能夠穿越時空、跨越種族、超越文化的人學主題,始終需要我們去挖掘,作者是以中國的歷史作為參考,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理解文學文本的全新方式。
二、人生的多重變奏
當我們從 “文學即人學”的理論探討中走出來之后就會意識到,這一命題早已在中西方文學的漫長歷史中得到了無數次的驗證。讀者在接受這一命題的同時,依舊存在著這樣的困惑——為何是文學與人學產生了復雜的、特殊的聯系,而非其他層面的問題之間構筑起特殊的精神性內涵。對于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們而言,他們所面對的時代風氣并不存在著巨大的、無法超越的鴻溝,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和精神狀態卻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應該認識到,“生活之于人本無偏愛,特別是那些同時代、同命運的知識青年,一樣的苦難,一樣的歡樂;一樣的陽光雨露,一樣的草原;一樣的蒙古包,一樣的吃喝穿戴;一色的 ‘帽沿朝后,衣帽稀爛,歪騎著馬’。然而由于不同的人生觀使他們的內心深處爆發著迥然不同的裂變,令他們對生活作出了不同的選擇。”[3]
出現在小說《荒誕歲月五題》中的人物正是一群經歷同樣的時代、感受著同樣的生活、體驗著同樣的人生的人。在他們走過的人生道路上,曾經的相似都成為歷史迷霧中被遺忘的存在,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最終做出的選擇究竟是什么?我們看到 “荒誕歲月”中的 “我”得到了逝去者的寬恕, “白菜地”里的“我們”卻和 “老趙”一起哭了起來,前者獲得了寬恕、后者獲得了理解。這都是人性迷失了的時代中最為寶貴的經歷。至于 “魚宴”中的家人在吃了魚之后卻一無所知的反映,正好說明了當時的人們對于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毫無察覺,他們甚至成為這個時代的附庸。
漫長的人生道路在開始的時候并不能夠引起人們的重視,我們在盡情地揮灑了青春之后,終于感受到了生命的寶貴。這時的我們就如同作者在小說《荒誕歲月五題》中描寫的人物一般,蜿蜒曲折的人生道路已經在我們的腳下,無論是曾經走過的,還是即將面對的,對于小說中的人物是如此,對于生活在現實社會的人們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出現在 “白菜地”中的 “老趙”已經多次遭受了他人的傷害,但他都堅強地忍受著周圍的一切。只有當他意識到和自己相親的僅僅是白菜時,他才像孩子一般放聲哭了出來。他所釋放的不僅是自己內心深處復雜的情感,更是他們對于自己的侮辱、傷害。
對比之下,出現在小說最后一部分 “紅蘋果”中的 “我”就幸運得多,“我”在一次緊張的勞動中始終關心著獲得一個蘋果,而這樣的做的目的僅僅是獻給自己心儀的陳螢。讀者在閱讀這篇小故事時感受到了久違的人性光芒和情感燭照。或許有一天 “老趙”也將迎來自己生命中的 “陳螢”,在作者所展現的人生篇章中充滿了變數。人生路途中的變數帶給人們的不僅會有意外的驚喜,更有人們在前進道路中可能面臨的苦難時鼓舞自己的希望。人生的多重變奏深深地影響著我們,使得我們更多地看到了美好的明天。當人們感到困惑和艱難時,并不是因為前進的道路沒有希望的曙光在照亮他們前行的方向,而是他們正處于起起伏伏的人生下落期,并沒有感受到來自于生命的希望而已。
三、同時代人的精神溝通
當我們將關注的視角再次投向 “文學即人學”的命題時,還需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人可以生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而文學則是跨越歷史的精神性存在。將二者之間的關系簡單地抽離為等同的關系,事實上承認了文學存在一以貫之的精神內涵,并且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曾斷絕和改變。對于生活在后世的人們而言,理解前人的文學唯有借助于文學文本。“文本在世界中。文本只有被閱讀才可能在世界中。不被閱讀的文本是現成狀態的持存的印跡,僅僅是僵硬的形式。閱讀文本是結構消解之,實現為生生。然而消解并非還原,唯獨僵硬的抽象的物才可言其還原。”[4]
當小說文本被讀者不斷閱讀之后,作者創作這部作品時試圖表達的內心情感才能得到 “闡釋”。就我們的研究對象《荒誕歲月五題》來說,作者的創作對于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們來說是巨大的情感沖擊,尤其是和作者有著同樣的人生經歷和社會閱歷的人,作者采用如此近距離的描寫,將他們所經歷的一切都表現在小說文本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能夠理解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時代的人們所經歷的一切,對于他們的關注和描寫就是對于他們寄托著厚重的情感。
說完后,陳螢笑了,陳螢笑的時候口中露出兩排碎玉似的牙齒,兩只黑葡萄似的眼睛閃著深情的黑幽幽的光,真是太動人啦!后來交通車來了,我們一起上了車,在車上我們聊了一路。也就是從這天起,我開始了自己的初戀。
“紅蘋果”的最終結局是 “我”開始了自己的初戀,而 “我”的戀愛對象正是陳螢。對于生活在荒誕歲月的人們而言,人生的苦難和痛苦會以多元的形式降臨在自己身上,但同時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可以溝通的,他們都懷有對美好愛情的追求。小說中的 “我”以最為樸實、最為真摯的情感打動了陳螢,我們二人的愛情是在充斥著荒誕事件、迷失了評價標準的時代出現的。作者將這一切置放于前文復雜、扭曲的人性思考之下,實則是向讀者暗示了 “我”和陳螢的未來就是所有人的未來,荒誕的歲月終將要成為歷史,同時代的人們能夠在精神世界的溝通層面尋找到心靈的慰藉。
從總體上來說,小說《荒誕歲月五題》講述的五個故事之間并不存在邏輯意義層面和故事情節層面的連續性。在讀者閱讀之初,很容易讓人產生一頭霧水的感覺。但細細品味之后,我們就會意識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所有的荒誕歲月都會在人性最深處的愛情鼓勵之下得到釋放。對于人的肯定,對于人的尊重,將最終奠定我們的未來。
[1]錢谷融.“文學是人學”命題之反思[J].中國社會科學,2010(01).
[2][德]康德.判斷力批判[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171.
[3]丁守璞.人生與愛的多重變奏——論作家張承志的創作觀[J].民族文學研究,1987(05).
[4]謝遐齡.人之消解[J].上海社會科學學院學術季刊,1989(08).
張靜(1970— ),女,河北寧晉人,本科,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高級講師,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