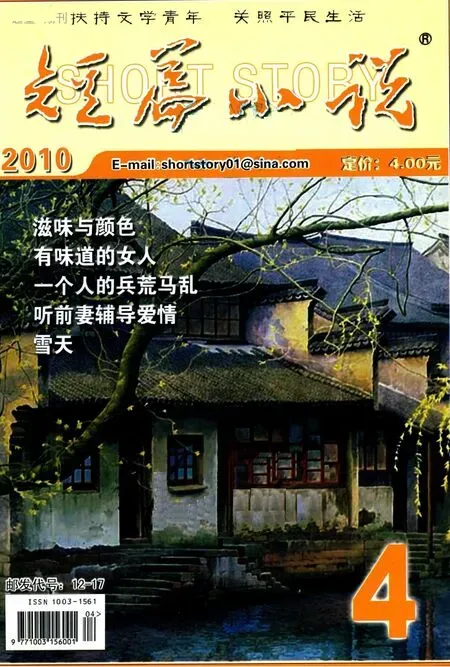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花四兩脫貧記》折射的官場文化
尹領巧
《花四兩脫貧記》折射的官場文化
尹領巧
王寶國創作的小說《花四兩脫貧記》是一篇質量上乘的現代官場小說,作者通過講述發生在花四兩身上的一件看似正常而瑣碎、實則蘊涵深刻社會問題的事件向讀者展現了中國當代社會官場生態的 “真實情況”。“由于傳統文化 ‘官本位’思想在中國當代依然產生著廣泛的影響,‘官場’這一領域便有相當大的言說空間,因而以官場為背景和表現對象的小說層出不窮。”[1]
一、諷刺現實的官場小說
在中國當代文壇中,劉震云創作的一系列以官場生態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小說堪稱中國現代官場小說的典范。中國作家熱衷于創作官場小說不僅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與廣大讀者的審美趣味有著直接的關聯。回首中國文學走過的道路,官場小說并非是在近現代才崛起的新興事物,而是很早就融入到中國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我們可以在早期的諷刺文學中找尋到相關的證據,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和《老殘游記》中可以了解到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官場生態的景象。這些小說從不同維度解析了中國官場的黑暗現實,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并非單一表現官員的可惡,還以大量的筆墨描寫了普通民眾糾結于反抗與妥協之間的現實選擇。誠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寫:“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篇,即千篇一律。”[2]
時代跨越了百年,中國人思維深處的 “官本位”思想并沒有隨著社會的歷史變遷而消亡,我們又一次在中國當代文學的作品中看到了反映官場生態的作品。小說《花四兩脫貧記》作為這一類型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整篇小說講述了貧困戶花四兩意外被選中作為扶貧對象的故事,當他成為交通局重點幫扶的對象之后,先后經歷了牛糞事件、沼氣池事件、新房事件、記者采訪事件和大棚事件,花四兩的心情也伴隨著降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不斷起起伏伏。花四兩所經歷的一切并不是針對他的實際情況量身打造的 “扶貧措施”,而是張局長和齊干事為了讓自己成為張副縣長和齊副局長的 “逢場作戲”。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這一點之后,花四兩依舊沉浸在各種事件帶給他的快樂和擔憂中,他沒有真正理解事情的本質,作者正是要借助花四兩的視角來展現人們對于現實社會中官場生態的理解。小說的作者沒有以直接的方式去描繪官場生活的真實面貌,這一點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他本人或許沒有能夠進入官場,對于真實的一切所憑借的僅僅是個人的幻想而已。
一直在大棚外等候的村長和齊干事問:行了?記者說,張局長幫扶誰不好,偏要幫扶這個花四兩。村長笑道,在古家莊除了花四兩,需要幫扶的人還真不多呢。記者說,修了路,就應該有個花四兩開著車在路上跑的鏡頭。這才顯得真實可信。村長擺擺手道,可別,那非要了狗日的命不可。他就會攆驢車,哪摸過方向盤。齊干事說,這事最好請示一下張局長。說完齊干事就開始打手機。聽了一會兒,齊干事畢恭畢敬地說,對,我們也是這樣考慮的,專題片一定要十全十美,反映幫扶工作的全貌。最后,齊干事說,請領導放心,我一定把這件事辦好。
上文是村長和齊干事之間的一段對話描寫,從中不難看出,所謂的幫扶只是走走樣子的官樣文章而已,其初衷并非是為了要改善某一個群眾的現實生活狀況。同時,齊干事在整件事情中的態度也十分值得讀者品味。他是整個事件的直接執行人,最終的功勞卻都是歸于張局長的身上。在他如此辛勤付出的背后,最真實的動機正是本篇小說的關鍵所在。作者不僅是在諷刺逢場作戲的扶貧行為,更是對類似于齊干事的鉆營者給予了辛辣的諷刺。
二、官場文化的社會解讀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自王蒙創作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之后就逐漸淡出,中國文學的官場文化氣息發生了變化。“隨著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的提出,真實反映生活尤其真實反映官場生活的文學創作開始繁榮起來……主要就是關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以單位為描寫場景的官場生態以及權力對普通老百姓刻骨銘心的影響。”[3]如果說作者筆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官場小說更多地涉及對于舊的計劃經濟模式下社會形態的批判,當時間的指針指向21世紀時,我們就會發現官場小說中開始出現新的表現對象。
總體而言,新時期的官場小說主要是以王躍文創作的《國畫》作為標志的。在這部小說問世之后,官場小說就被當代社會等同于揭秘現代官場的腐敗和多種不為人所知的政治斗爭。而當下的官場小說又可以被劃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宣揚主旋律的作品,如《至高利益》;另一種是反映官場陰暗面的作品,如《國畫》等。通過這些小說所描寫的情節以及出現在小說中形形色色的官員,讀者不難看出創作者更多地選擇了從社會角度去解讀中國現代社會的官場文化。我們必須承認,很多作品的確以多種形式展現了不為人所知的官場秘事,卻很少能夠看到有一部作品是從人性的角度去解剖官員的心靈世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官場小說作為當代中國社會的權力鏡像,是屬于政治意識形態的所謂宏大敘事,涵括了諸多復雜的話語系統,是個多重曖昧的話語場域,具有豐富的言說空間和特殊的研究價值。”[4]呈現在筆者面前的《花四兩脫貧記》在延續中國現代文學官場小說主要表現方式的同時,從被幫扶者花四兩的角度進行了適度的精神描寫,為我們解讀中國現代社會的官場文化創造了條件。
花四兩是以官場文化的對立面存在的,但他不是反抗官場的現實存在,而是生活在任何一個時代的社會底層的代表。在花四兩的身上,我們不僅可以找尋到人性深處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花四兩沒有希冀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去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是將改變自己命運的希望寄托在辛勤的付出上。他可以為了齊干事送給自己的一車牛糞而一夜不睡,他的盤算雖然帶有工于心計的痕跡,卻不失去樸實的精神本質。讀者在花四兩的內心深處看到的是他對于齊干事、張局長、記者、村長等人所采取的一切行為和措施的否定性理解,在他的眼中,只有在大棚中不斷地努力,才能真正造就屬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如果將花四兩的行為界定為踏實肯干,其對立面就是官場的形式主義;如果將花四兩所理解的生活界定為勤勞善良,其對立面就是官場的蠅營狗茍。
三、官場文化與官場小說的誕生
小說《花四兩脫貧記》中所描寫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中國現實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也有可能已經結束或正在上演,只要中國人思維觀念中 “官本位”的觀念沒有得到徹底地清掃,圍繞著仕途進退的官場文化就會持續不斷地發酵下去,并不斷為文學的發展提供新的素材。官場文化造就了官場小說的誕生和繁榮,使其具有文學層面和文化意義層面的雙重價值。當新的一篇關于“花四兩”的故事又被作者們整理、創作出來之后,我們就不能再用單純的諷刺社會現實對其進行界定和闡釋,而是需要從新的角度來加以認識,它儼然就是 “突出而重要的文學史現象和文化現象”[5]。
小說中有兩個情節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首先,張局長和齊干事來到村里開大會,這是展示二人對花四兩扶貧成果的大會,他們不僅取代花四兩成為整場大會的真正主角,更以電視宣傳片的形式為自己贏得了豐厚的政治資本。其次就是再一次來到村里的齊干事,他對待花四兩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村長對于發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切洞若觀火,因此他告誡花四兩:“領導不伸手,不要主動去握。”這正是對于官場文化的最佳詮釋。
那天晚上,花四兩是一個人在家睡的。花四兩一直睡到天光大亮,中間連夢也沒做過。這是這么多年來,他第一次睡得這么踏實。緊挨著他睡的是那個女人帶回的半大孩子。孩子把一條腿架在花四兩身上,那親熱勁兒,好像他們天生就是一家子。
花四兩終究無法憑借著張副縣長和齊副局長的幫扶擺脫貧困的現實境遇,但他在這一過程中所收獲的絕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更為直接的是他對于未來生活的肯定和樂觀態度。但當睡在領導給他蓋的新房子里時,他感受到的是家的溫暖。在這份溫暖的生活現實背后掩藏的卻是官場上的又一次交換,張局長和齊干事通過所謂的 “幫扶”為花四兩帶來了新的生活,讓這個村子成為一個盡人皆知的典范。
官場小說描述的是人性迷失了方向的精神世界,在這里無法找尋到精神的慰藉,也無法洞悉出現實社會的積極意義。在它的身上,“明顯地缺乏呼喚愛,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們在審視中國文學在當下的發展歷程時,卻不能忽略官場小說的存在意義。正是由于它為我們提供了從負面的角度審視社會、觀察官場的切入點,使得我們能夠以更加冷靜、客觀的態度去思考官場小說所折射的官場文化。官場文化的形成畢竟經歷了數千年的漫長發展,它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構成元素之一,單純地否定它的存在沒有任何意義。
官場小說為中國文學在當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它所延續的并非是晚清以來譴責小說的情感模式,而是針對當下社會的人性面進行重新思考、全面審視的理性產物。如何理解官場小說或許還需要讀者和創作者在人生的磨礪中不斷去探索,當社會不斷發展、法制不斷健全、人們的道德水平逐漸提升之后,“官本位”的文化傳統是否會有所改變都是未知的。
[1]趙井春.論劉震云官場小說的批判性[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13(02).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124.
[3]馬洪波.新時期“官場小說”論[D].齊齊哈爾:齊齊哈爾大學,2012.
[4]黃聲波.權利鏡像的拆解與迷局[J].中國文學研究,2007(02).
[5]劉復生.尷尬的文壇地位和曖昧的文學史段落——“主旋律”小說的文學處境及其現實命運[J].當代作家評論,2005(30).
尹領巧(1971— ),女,河北晉州人,本科,石家莊科技工程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