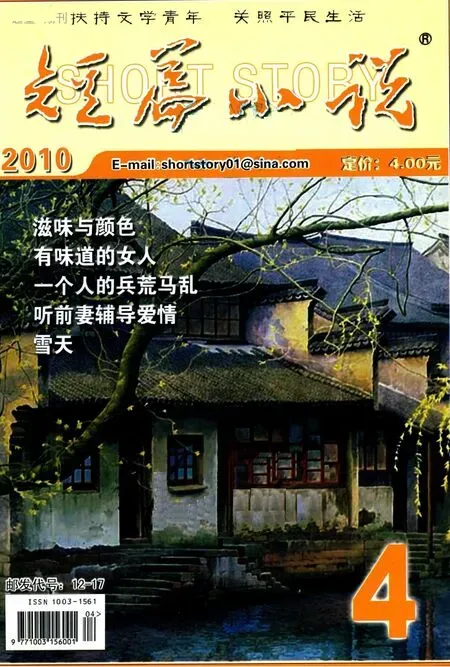從《不死的核桃樹》看現代田園小說的審美傳統
李春梅 任 娟
從《不死的核桃樹》看現代田園小說的審美傳統
李春梅 任 娟
一
小說作為一種獨特的審美意識形態,其曲折緊湊的故事情節以及變化多端的敘述語言總是能夠深入人心,打動人的心弦。雖然小說常常描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瑣碎,也常被作家用來暗喻或評判家國政治與民族歷史,但是對于優秀的小說來說,它絕不僅僅是單純地刻畫生活、指點歷史。優秀的小說家應該有很強的文字掌控力以及縝密的思維能力,因為想要完成一部優秀的小說,就必須具有凌駕于生活與歷史之上的眼光和老練嫻熟的表現手法。每個人對于生活的感悟程度都是有所不同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十分復雜而微妙多變的,人性當中的善與惡、美與丑體現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總是受到人性本能的控制,任何一對矛盾關系的演變都與人性本能的掙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說,作為一個優秀的作家,不僅要看透人性當中的善惡美丑,同時還能夠將這些特點借助文字的力量表達出來,發揚善與美,批判惡與丑。生活不是電影,生活不是小說,生活本身要比文字敘述、光影表現出來的情節復雜得多,場景也豐富得多,但是,作家卻可以利用藝術想象力,運用文字的神奇力量超越生活之上,為讀者展現藝術的魅力,這就是小說的獨特魅力所在。當然,作家在敘述的過程當中會遵循一定的生活邏輯和藝術規律,只要符合這些邏輯與規律,小說中出現的任何夸張成分與曲折情節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些偵探小說與傳奇小說中,經常出現緊湊曲折、夸張離奇的故事情節,這都是符合藝術規律的。
二
當代鄉土作家常常以自己的故鄉作為作品中最主要的表現對象,因為對故土的熟悉與熱愛,在相對廣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作家容易選擇和摘取最適合作品表現力的相關素材。鄉土作家一般都善于描寫農民的性格與命運,盧海娟就是其中之一,作家常常將農民的性格命運與民風民俗緊密地聯系起來,筆觸細膩而真實,充滿濃郁的鄉土田園氣息。盧海娟的小說緊緊圍繞著一個主題,那就是作家試圖通過自己的文字來反映鄉土中的各種風俗人情,表現日益荒涼的人心。通過作家的作品,我們似乎能夠發現一個被放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有人性中的真善美,也有陰暗無光被社會碾壓扭曲過的假惡丑,不管是哪一方面,讀者都能從中真切地感受到世間百態的眾生相。
《不死的核桃樹》作為盧海娟的一篇短篇小說,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濃郁的田園風格。小說刻畫出了老高太太這一具有些許傳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在刻畫人物的過程中,也描繪出了地方的風俗與人情。小說文字猶如一股淺淺的清泉,淡淡地流入情感的溪流中。雖然故事情節緊湊,扣人心弦,但作品文字簡約,并沒有顯得過于拖沓和冗長。文章用一種類似偵探小說具有懸疑性質的敘述筆調帶動讀者的情緒,因此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這樣的一種敘述方式就猶如一位耄耋的老人拉著幽咽的二胡在靜靜地獨奏,遠遠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引人入勝的鄉村水墨畫。
三
《不死的核桃樹》這種具有濃郁田園氣息的敘事方式采用的是當代新文學中鄉土小說的敘事方式,在新文學中,鄉土小說一直是范圍最龐大成就也最高的一種文學形式。在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中,鄉土小說起源早,線索發展最為清晰,結構也最為龐大,發展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作為一篇鄉土小說,《不死的核桃樹》不同于其他內容與形式的小說,現實主義的表現風格一直在小說中居于主導地位。這篇小說延續了寫實的風格,但是又不同于20世紀40年代以趙樹理為代表的鄉土小說,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反映農民面貌和農村風俗的作品在刻畫人物的過程中進行了現實主義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民智,推動了農村的發展,這些作品都具有深切的人性意識。
《不死的核桃樹》與傳統的鄉土文學相比較起來帶有一些浪漫主義的色彩,追溯起來,這種浪漫情懷也是有其歷史淵源與傳統繼承的。雖然理性色彩一直作為新文學敘事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但在鄉土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也有類似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的田園式抒情傳統。在眾多鄉土作家中,沈從文和廢名的作品就具有這樣細膩清淡、寧靜悠遠的風格,呈現出浪漫主義的意味。這種浪漫情懷在沈從文的作品中達到了極致,代表作品《邊城》就是典型作品之一,這樣的鄉土文學作品猶如一幅清新的山水畫,與我國古典山水田園詩如出一轍,雖然同為鄉土文學,但廢名、沈從文的作品卻與魯迅、趙樹理等作家作品的敘事風格特點具有很大的不同,在眾多鄉土文學作品中,廢名、沈從文的作品就有如居于文學大地一隅的小小烏托邦,人們常常把它放在理性的框架之內進行評判和解讀,這些作品基本屬于純粹的田園敘事。就像《不死的核桃樹》里描述的一樣,“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樣改變,小山村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守著祖訓,執迷,緩慢”。這樣一種淡遠的敘事猶如一首馬頭琴拉出的悠長的老歌,古樸、悠揚,散發著老酒一樣的陳年醇香。
從《不死的核桃樹》里,我們看到作者盧海娟敘事方式的獨特,她摒棄了傳統鄉土小說常用的敘事風格,而是改用了一種復調敘事的方式,這種敘事方式綜合了田園性敘事和反田園性敘事的方法,將這兩種不同的敘事類型進行綜合,從而表現出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體現出與以往鄉土小說完全不同的敘事類型。當然,《不死的核桃樹》這種復調敘事的方式在我國現代小說里并不是唯一的,它也有一定的發展軌跡和歷程。追溯這種復調敘事方式的源頭,我們可以從新文化運動時期 “五四”鄉土文學當中找到它的起源,在當時眾多的作品當中,魯迅的《故鄉》就屬于這種運用復調敘事的方式進行創作的作品,從魯迅開始,這種復調田園小說便一路發展下去,一直到抗戰之后,復調田園小說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高潮,這歸功于蕭紅和師陀等人,尤其是蕭紅的《呼蘭河傳》,以其獨特的語言張力與作品表現力將東北鄉土之間的世情風俗刻畫得入木三分,甚至讓讀者不寒而栗。從復調敘事的鄉土小說作品來看,它既具有魯迅、趙樹理等傳統意義上的鄉土小說的特點,同時也兼具了沈從文、廢名等田園式鄉土小說的韻味,在這種小說里,完全的寫實和完全的寫意已經沒有了具體鮮明的區分,它一方面與真正意義上的田園小說做著對抗,同時也與傳統意義的鄉土小說相互矛盾。因此,這種小說既不能成長為類似沈從文 “烏托邦”之類的城堡,同時也不能完全與傳統鄉土小說分庭抗禮。
從《不死的核桃樹》追溯復調敘事鄉土小說的自我內部結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復調鄉土小說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著的,因為田園與反田園這兩種敘事方式本身就存在著明顯的矛盾,雖然同為鄉土小說的范疇,但是這兩種不同的小說處于互相對立的地位,而對于現代文學來說,這兩種不同的鄉土文學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我國鄉土文學的敘事內容與表現方式,這是中西方文化不斷交流與碰撞的結果。從復調田園小說的藝術特征來看,正是這種看起來不清不楚、模模糊糊的敘事方式使得它呈現出與其他類型鄉土小說不一樣的魅力,正如《不死的核桃樹》所表現出的不同內容一樣,它有傳統意義鄉土小說的敘事,作者這樣描寫老高太太:“她可是村子里的活神仙,年齡最大不說,她還是村子里最有資格的薩滿,不過這是文明世界的叫法,村里人只知道老高太太是 ‘領仙的’,幾乎所有的村民都找她瞧過病擺過事,葉秀文也不例外。”這樣的描寫體現出濃厚的鄉土氣息,給作品籠罩了一種神秘的色彩。與此同時,作品還有田園小說所體現出的復雜情懷,在這篇小說里,作者在作品中所寄托的感情同樣也不是單一的,它既有愛,也有恨,充滿著無限地留戀,同時也夾雜著想要離去的苦痛,思念、眷戀、厭惡、嘲諷……正是這種愛恨交結在一起的復雜情感才使得復調田園小說的魅力大放光彩,這又與蕭紅的《呼蘭河傳》有了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仍有一片廣闊而遼遠的天地,作為中國新文學,鄉土小說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發展至今,仍具有十分頑強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途。從當下鄉土小說的發展來看,一大批鄉土文學作家活躍在當代文壇,我們應該特別珍惜這些鄉土文學作家。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不斷進步,城鎮化速度也越來越快,對于大部分讀者來說,鄉土文學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回憶或者認識農村面貌與風土人情的機會。對于鄉土文學作家而言,農村永遠是一種難以割舍的情結,這些作家通常都具有十分質樸的情懷和醇厚的品性,他們筆下的文字也都真實而生動,具有其他類型作家作品所不能比擬的感染力和表現力。鄉土情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鄉土文學作品發展至今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它之所以能夠具有持續性的美感,是因為鄉土文學作家個體生命所具有的頑強的生命力,正是由于這種對生命、對生活的感悟與感恩,才使得鄉土文學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1]高玉秋.傳統鄉村文化覺醒者的價值選擇——論20世紀初鄉土小說中知識者的“鄉村批判”[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
[2]戚鈞.反叛與眷戀─—論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文化意義[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03).
[3]滕小松.沈從文小說創作的文化心理[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1997(01).
[4]陳晉肅.二三十年代鄉土小說美學的文化苦旅[J].寧夏社會科學,1997(03).
[5]趙學勇.鄉土文學的走向與選擇[J].小說評論,2003(02).
李春梅(1964— ),女,陜西蒲城人,本科,陜西科技大學教授,從事高等教育管理與行政管理研究;任娟(1983— ),女,陜西咸陽人,碩士研究生,陜西科技大學講師,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