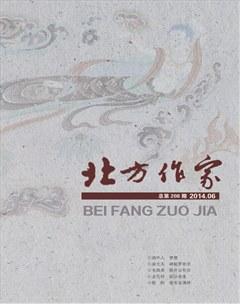老館子(外一篇)
“老館子”,本地一個飲食去處。單名字便是我極為喜歡的黑白片的意味,仿佛遠去的時光仍是心上晃動的影,現代奢靡生活里一部回放的黑白片。
其間的老飲食,不是過去的闊闊的牛大碗,一碗吃足飽。是小而精致的拇指食指錯開便可捉起的碗。待餐桌上交杯換盞洶洶攘攘的差不多了,人已有了疲憊之氣,方小家碧玉一般,一碗一碗次第上桌,一樣,另一樣,再一樣。
一樣,是面辣子。
面粉和辣椒面,二比一的比例,佐以花椒、鹽,用滾燙的大油潑澆,“呲”一聲,瞬息油滲入面和辣子和調味,即成。剛出籠的饅頭冒著熱氣,切片順順地碼在平盤里。吃時,只需舀幾勺面辣子抹夾在兩片饅頭之間,油滲入饅頭酥軟的空隙里,好像林間松針厚厚地鋪了一地。素樸的小麥的面粉,農家屋檐上染了秋色艷紅的辣椒面。大油,是豬油,豬身上的肥膘在大火上熬制成油。現在的人似乎不吃這種油了,過于肥膩,吃一口胃里暈暈的想吐。而曾經因為物質的匱乏,那樣的肥膩恰可以讓饑餓的胃部有一種短暫的富麗堂皇的滿足。
簡而又簡的原料及制作,入口卻是滲在舌尖流入身體的無限的暄軟和溫暖,好像秋日藍天下大片的明麗澄凈的葉的黃,好像民國時期大人小孩身上絆著腳后跟的綿綿的冬袍。因著豬油的肥膩,入口一剎是令人略略有些眩暈的,待完全入口細細地嚼起,便有一種入骨隨心的穩妥,仿佛懸著的心終于有了傍依,有了現世的安穩。
另一樣,是卜拉子。
方言總有些含糊不清的時候。本地發音是“bolazi”,我總以為應該叫“撥拉子”。因為它仍是以面粉和其他某種可食植物為基本的底料,期間有筷子亦或手撥拉的那樣動作。
一種叫艾蒿的野生植物,好像是最為久遠的做卜拉子的材料。春天的耕地,待微暖的風吹過,田地即浮起一層淺淺的綠,生煙一般。到了傍晚,小城的人去往散步,拿了塑料袋和小鏟子,地埂上細細地找艾蒿的新芽。艾蒿的新芽有一層絨絨的霧一樣的白,就像剛出生的小鴨身上毛絨絨地泛著光,很有一種欣喜。那絨絨的光,亦如春天漫漫的晨光,傍晚仍不散去。
散步回來,將艾蒿的嫩芽摘洗干凈,鋪在呆板上,略微地用刀切幾下,撒上面粉,撥拉幾下,到面粉濕濡在艾蒿芽并且薄薄地染一層干粉,方放入事先準備好的蒸鍋大火上蒸。大約一個小時之后出鍋,依然是燒好的油潑上去,灑一些花椒,用筷子或索性熱氣里跳著手撥拉幾下,均勻即成。
曾見過有人用五指撮起一小把卜拉子,捏一下,直接放入口中,好像有些蒙古糍粑的意思。我也嘗試過用手直接撮起來吃和用勺子舀起吃的不同,卻用了勺子總沾些冰涼的鐵腥氣,壞了它的本味。只有用手撮起一把,捏緊了放入口中,手碰著嘴唇,暖暖地,才是最本真的味道。味道并不見得要好于大魚大肉,然而,因著是春天的新芽,便有些晨光的清新,香味也格外地接近自然。
在北方,面始終是人們飲食的根,如同家鄉的老房子,離不開也舍不去。卜拉子,便是以面為宣紙的花鳥畫,潑墨可以是起初的艾蒿,也可以是后來人所發見的春天榆樹上新生的嫩榆錢兒、初散幽香的槐花、胡蘿卜、甜菜、香豆子,或者其他任意我所不知道的什么。其實,只要人的想象力足夠,怕任什么都可以作那畫間的絢爛花鳥吧。
后來知道,艾蒿除了食用,更是可以入藥,能理氣血、溫經脈、逐寒濕、止冷痛,為婦科要藥。另還有健胃、止瀉、降血壓等功效。我們的祖輩,天生的老中醫,無師自通,無醫自治,實在是智慧的很。
再一樣,是灰面。
戈壁灘上一種叫蓬柴的植物,風沙里長老了,長成了柴,割下來集到大坑里點燃,燒到蓬柴成灰成燼了,澆一些水,冷卻凝固成塊,便制成蓬灰。
灰面,便是蓬灰水和制而成。
農家人制作灰面,算作一個大的場面。大炕上,大的案板。蓬灰水和了大團面,最好要硬一些,由力氣大的男人雙手左右開弓,悠了身子案板上用力揉,不停揉,揉到面軟了,拉開來有了彈簧的筋道,方進入下一程序。不同于牛肉面的拉,灰面是捏出來的。面揉好后搟一下切成細長條。兩個孩子分站在炕邊上,擔起一根長搟面杖,一把長條面摞搟面杖上,由家里的主婦站在地上伸手攥面從上往下順著捏,捏到下方的面頭繞手上繼續攥捏,這樣反反復復直到想要的粗細,從搟面杖上取下來,一摞一摞放在案板上,等待入鍋。那個時候,火爐上的鍋熱氣騰騰,一家人炕上盤腿坐的,炕下忙碌的,小孩子繞著屋子鬧著玩,很是農家祥和的喜慶氣氛。待灰面入鍋煮熟,撈出,再涼開水激一下,放如碗中,清幽幽的一根一根散散的,燈光下滑溜溜地閃著亮。澆些醋盧子,拌一拌,撩起一筷頭,入口酸酸滑滑,沁人心脾,簡直那個“爽”!
其實,正宗的灰面城里人如今很少能吃到了。倘若日子久了,想吃爽溜溜的灰面,便給居住農村的那位老母親打電話過去。那老母親接到電話,喜滋滋地顛著身子早早就起身準備。又因為孩子們都在外上班,原本擔搟面杖和捏面三個人的活就只能靠老母親一個人完成。常常是那個老母親將搟面杖一頭頂在墻上,一頭抵在自己的肩窩處,細長條的面搭在搟面杖上,雙手就前從上往下捏。那一刻,屋子里極其安靜,陽光透過窗隙斜斜地照進老屋里,一道道彌漫著細細的塵……
“老館子”還有幾樣小碗盛著的飲食,記不確切了。然后,一樣一樣在客人們懶懶的神色里慢慢地上,頗有些饕餮盛宴后的夕陽晚歸遲。回頭看,似乎這些小吃并不見得有多特色,然而因其本身由這兒土生土長源發而來,雖有些形式上的刻板,卻多了延綿和恒久的意味,總會讓人想起從前,想起故鄉,想起曾經那些沒有紛擾的淡淡的日子,那一刻,心會突然變得柔軟,一種久違了的甜蜜和平靜,還有幸福的感覺。
以愛的名義
對于事件本身,我們往往更注重結果。譬如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出生以及由此帶給我們的驚喜、驕傲,仍是我們最終想要的結果。自然,母親在孕期會以她特有的方式感知他的真實存在,與他對話、相處,一起歷經。除外,不會有更多人去關注生命自孕育之初到脫離母親子宮這一過程究竟歷經了什么,那是身體內部我們無法看到的世界。
瑞典攝影師里納德.尼爾森以他的攝影作品為我們進行了解密。
他的第一張圖片是一對戀人的熱輻攝影。一對戀人,一男一女,他們牽著手。熱輻攝影呈現出的,是兩個以身體作為熱輻射源、被鏡頭感知并捕捉到的人的外部輪廓,它完全擯棄了物質意義上的任何裝飾和依附,比如衣物、設施、環境,只以黑色為背景,展現出兩個人最原始的身體輪廓。最原始的,創世紀上帝制造的亞當與夏娃,他們單純地沒有任何附加地相遇相伴;單純地,手牽著手。是的,這比什么都重要,對于生命的起源,它是最恰當不過的注釋,——他們牽著手,走在一起。
第二張圖片一個吻的熱輻攝影。我曾查找過熱輻攝影的相關資料,發現其表現的方式和結果竟完全取決于人體自身的溫度。也就是說,人體的溫度越高,聚集的熱輻射能量會越足,繼而經各類技術轉換到攝像機的影像的質感和色彩就會表現得越加厚重和濃烈。圖片中,依然是原始的輪廊及色彩的呈現。女的微微仰起臉,男的俯首迎合,他們柔軟的唇結合在一起。圖片凝固的一瞬間,兩人面部及頸部呈現出濃郁的紅色,火一般的釋放、燃燒、擴展。毋庸置疑,愛激發著人體的溫度逐漸升高,乃至噴涌。整個圖片亦是以黑色為背景,面部及頸部所呈現出的恣意的紅色,足以證明這對戀人,他們深愛著,并通過吻彼此全身心地傾注、給予、融合、滲透。他們以愛為圣潔而柔軟的表達,為一個生命的誕生奏響了華麗的樂章,深情,悠美,滲透靈魂。
接下來,精子的奔跑。圖片背景為藍色。無數白色的精子,游弋著黑色流線型的尾巴,爭先恐后向一個目標奔跑。藍色,男性的,冷靜、理智,海一般的寬廣和深情。精子們在奔跑,在競爭,以速度,以力量,以耐力,長長的尾巴跑成一條直線。它們竭盡全部的力量和激情,只為一個目標——找到生命的另一半,完成愛的儀式。雖然,它們中只能有一個、最有力量的那個,成為奔赴中的伊阿宋,獲取珍貴的金羊毛,得到想要的愛。但是,不管怎樣,奔跑吧,阿戈耳的英雄們,我們都是最有力量的,為了愛,為了相遇,我們毅然決然,我們義無反顧,哪怕最終一無所獲。
而卵子,亦在同一時刻準備一次相遇。橙色的、橢圓形的卵子——美麗的美狄亞——烘云托日一般,從白灰色的卵巢中排出,由絢麗的牡丹花一般的輸卵管傘引入,等待那個最強大的精子的到來。她的溫暖的略略透明的橙色,泛著喜悅和嬌羞的柔光,使得無論多么迫切的期待,都顯得那樣安詳和沉靜。等待,多么地令人幸福。默默地,等待一次相遇,相知,相愛。溫暖而寧靜的橙色啊,它在心底鋪了一層暖暖的絨,讓所有的愛與被愛沉浸在無盡的喜悅里,令人心弛神往。
“一個來自母親卵巢的卵子臥在一條輸卵管的粘膜皺褶內,在這條通往子宮的管道內,一個來自父親的精子將會使卵子受精,以創造一個新人類”,——多么詩意的表達。精子和卵子的相遇,就像孩子父母的相遇,是一次命定的、自此永恒的相遇。
接下來的圖片中,一個精子,就像不斷旋轉的鉆頭,在尾巴拍打的驅動下努力進入卵子。那是一個喜悅、幸福卻伴隨著痛的過程。是的,痛!相遇并相融,在它全部的過程中,除了喜悅、幸福,還要經歷一次激烈的痛。痛得撕心裂肺,天旋地轉。痛得無以逃循,惟愿消失。然而,只有經歷了痛,才可以擁有真正的愛。也只有痛,才可以讓愛更加完整。
終于,精子成功了!一張圖片里,一個最有力量的精子,它沖破了一切阻礙,進入卵子體內,獲得了最終的勝利。它驕傲地甚至連尾巴都丟棄在卵子殼外了。沒事的,丟便丟了,此刻的擁有比任何都重要。看,在卵子紅黃色的溫床上,藍色的精子將頭埋在一片溫潤里,那么安靜,那么幸福和滿足。親愛的,讓我就此停留吧,我不要太多,有這一次,足夠了。
精子與卵子結合了,生命有了它最初的物質原形一一受精卵。然后,受精卵到子宮,著床,開始發育。藍色大腦出現。咖啡豆一樣的心臟開始跳動。第四周,孕育中的胚胎,象一枚白玉蘭的花瓣,中間鼓起漸已長成的脊椎,泛著晶瑩的光澤。四十天時,胎盤和胚胎被流動著生命之血的臍帶連接在一起。紅色的生命之血,絲絲縷縷地將母親和胎兒緊緊連在一起……
在所有的藝術類別中,沒有比攝影更能客觀地表達事實,并直捷地穿透人的內心了。藝術家用他的攝影作品深情地講述著胎兒在母親子宮里一天天的變化,一天天地長大,并最終以完整的人的形式與母體作最后的告別。
由此,我們更加明白,生命不僅是單純意義上的一次物理合成,其間人類的情感、愛,已成為萌生并滋養整個生命最重要的陽光、雨露、土壤、養份,生命因此顯得莊嚴而令人敬畏。
田野間最早的長長的陰影
像人間的困境。
第一聲鳥鳴一點都不像陰影。
夏天的光非常年幼,而且完全無人監護。
沒人使它坐下來吃早餐。
它是第一個起來的,第一個出門的。
因為他已睜開眼睛,他必是光
而她,在他身邊睡眠,必定可見,
一小圈卷發環繞在她身旁。
他對她耳語:“醒醒!”
“醒醒!”他耳語。
(選自《哈斯詩集》“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
黃璨
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在《人民日報》、《文藝報》、《人民文學》(增刊)、《雨花》、《山東文學》、《飛天》、《西北軍事文學》、《甘肅文藝》、《作家導刊》、《朔風》、《甘肅日報》等報刊雜志發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