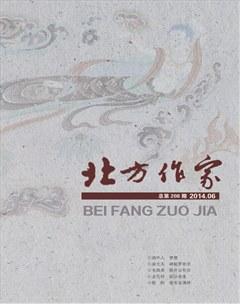夜光常滿杯
修柯
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走在什么地方,在或者不在。
當那么多人在忙著吹噓自己,尋找和制造“被吹噓”的條件時,他們一聲不出。
他們在忙什么?
靠想象修復過去
云里霧里的傳說
二零一二年夏天,酒泉電視臺制作的專題片《祁連夜光》播出。專題片中稱,酒泉制作夜光杯的歷史已有二千五百年。
由二零一二年上溯二五零零年,是東周。再向時間的上游探尋,我們看到了一個人的名字,他叫姬滿。周穆王姬滿。
在酒泉,對夜光杯有所注意的人都知道這個人。相傳,周穆王應西王母之邀,赴瑤池盛會,西王母送給周穆王一只精巧的玉質酒杯——“夜光常滿杯”。此杯“光明夜照,乃白玉之精,斯靈人之器”。
在酒泉,所有關于夜光杯的傳說,根源于此,更多的內容可靠性差,建議作為對歷史很不尊重的故事新編對待。
西王母是什么人?在《山海經》里這么描述她:在西海的南面,流沙之濱,赤水河之后,黑水河之前,有一座大山名叫昆侖丘。山上有個神,長得頭像人,身子像虎,皮毛上有花紋,尾巴上有許多白點。昆侖丘周圍,有個叫弱水的大淵環繞著,淵外有座炎火山,投上東西便同山一起燃燒起來。山上有個神人,她頭戴玉勝,一口虎牙,長一根豹尾,住在洞穴中,名叫西王母。這座山中世上萬物應有盡有。
酒泉文史工作者根據《竹書紀年》中“周穆王五十七年,西征于昆侖丘,見西王母”,和唐人《括地志》中昆侖丘在肅州東南八十里等記載,認定周穆王和西王母見面的地方就在酒泉,西王母所住的“石室玉堂”,正是酒泉城西南方向文殊山上的石窟。
但是,關于西王母人獸不分的相貌描述,和這些書里關于其他人、事、物顯然不合常理的記載,都讓人滿腹疑慮,始終不能堅信這一切都是確鑿的,都是無可置疑的。
應該是出于這樣的不自信,酒泉的老文化人們提起關于西王母和周穆王的這次會見,一般都在前面加上了兩個字:“相傳”。
真相可能是:在酒泉把玉石切一切
關于酒泉治玉,比較本分的說法是這樣的:
漢唐以來,因為運輸困難,酒泉開設了玉坊加工和田玉,不再以原石進貢,酒泉治玉業由此得到發展。
但是奇怪。在酒泉,我們很少見到傳世或出土的古代玉石雕件。即使在近年發掘的漢、唐、魏晉墓葬中,也幾乎沒有發現。秦國順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在酒泉老城區拆遷時收集到的玉珠和小的雕件,也都體量微小,不像是大規模高水平玉器加工應有的氣象。那些小雕件,更像是玉器加工中用邊角碎料完成的。而那些大塊玉料,經過了切削,被鉆取了棒料。那些選出的玉中精華,去了哪里?
宋應星《天工開物》里說道:新疆的玉料到達嘉峪關和甘州、肅州后,販玉的人再在這里采買,然后繼續向東送往燕京。玉工根據玉料的品質定價,而后才進入實際加工程序。
剖玉鉆棒,需要一種特殊的材料——解玉砂。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里說到:它山之石,可以為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可以為錯的“錯”——就是我們說的銼,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就是解玉砂。
酒泉解玉。清末、民國甚至酒泉夜光杯廠建廠初期,酒泉的玉工們還用到從更就近的地方找到的解玉砂——就在玉門市清泉鄉的灘上,被稱為金剛砂。它的成分是石榴石,當地稱為“石榴子石”。清泉金剛砂的硬度為摩氏七—八度,在使用人造金剛砂之前,一度是出口物資。直到一九七四至七九一五年,人造金剛砂普遍運用,清泉金剛砂才退出玉器加工材料行列。
運力所限,酒泉是入關第一站,可以就近取得解玉砂,中國販玉者“至此互市”……諸多條件決定了酒泉玉料初加工這個行業存在的必然。
一個地方工藝美術水平的高低是由它的經濟、文化水平決定的。必須承認,在這一方面,歷史上的酒泉一直沒有什么地位。
可能只能這么理解:總體上看,漢、唐、魏晉以至明清時期,酒泉,是和田之外絲綢之路上的另外一個玉料場。碩大笨重的玉料運到酒泉后,為了減輕負擔,降低運輸成本,商人們卸下部分玉料,就地進行粗加工,帶上切好的玉料,鉆好的玉棒,輕裝前進。而以高明的工藝美術水平為前提的玉器雕琢,不是酒泉玉石加工作坊的長項——歷史上不是,現在也不是。
歷史上的“牛市”或者“熊市”
我們能夠理清的酒泉玉石產業發生發展的脈絡,是一種粗線條的框架:
夏商時期,酒泉已經在加工制作玉器。同時,新疆的玉料或玉雕產品已經通過肅州運往中原地區。
春秋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形成,中原地區和西域的政治、經濟往來常態化,玉料的運輸路徑已經得到確定。
兩漢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達到全盛,敦煌、肅州成為東西往來的重要關口,軍事要沖,貿易重鎮。玉料的運輸和交易空前繁榮。同時,酒泉本地的玉料也已經開始開采利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肅州是國際大都會,“全國文化先進縣”。如果說肅州的玉文化、玉產業曾經有過發展的高峰,這個時候應該是其中之一。
唐宋時期,肅州是邊地,甚至長期不在中原政權掌控范圍內,尤其是宋代,河西地區長期在西夏治下,中原與西方的來往都是繞道而行,因為社會動蕩和戰爭,從和田到中原玉石運輸成本增加,可能促成了酒泉玉的開采。
元代江山一統,玉料的運輸已經不再關涉外貿出口等國際問題,中原對玉料的要求隨之提高,對代用品低看一眼,和田開始開發山料。這段時期,酒泉的玉料開發應該處于停滯狀態。
明代,西域各國商人把向朱家皇帝“進貢”當做一種生意做了很久。他們“進貢”給老朱家玉石、小金剛石、紺青及其他物品,朱家皇帝好面子,都給予豐厚回賜。到了嘉靖以后,實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限制“入貢”人數次數。人數多的商隊,必須留在甘州一年左右。這些商人留在甘州大做生意,肅州跟著一片繁榮。總體上說,這個時候,酒泉玉應該沒有什么地位,但是邊境地區在特定時期執行的對貿易行為的緊縮政策,仍然可能對酒泉的玉料開采提供了不止一次的“窗口期”。
清代,由于政府在和田大量采玉,肅州玉行做的最主要的事應該仍然不是玉器加工產業,而是玉料粗加工和貿易。
即使這樣,在酒泉治玉史上,雍乾時期仍然是酒泉玉雕產業最發達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所謂“酒泉夜光杯”仍然沒有創出名號,玉杯只是眾多玉產品中的一種。
清末至民國,酒泉玉雕產業式微,已經不再開采老山玉,只以河流玉維系簡單生產,產品花色也趨于單一。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因為玉門油礦的開發,酒泉夜光杯生產有過極短暫的興旺期。
一九四五年,酒泉有工商業同業公會二十八個,會員一千二百零八人,其中玉石業公會十七人。至一九四九年酒泉解放前夕,仍然維持玉器加工的作坊,只剩下三兩家而已。
一九四九年前后,酒泉玉雕產業已經約等于無,只有極少數作坊在生產玉杯。這個時期一直持續到了一九五六年。
從一九五六年到二零零一年,是酒泉夜光杯生產的全盛時期。
作坊里有師傅和石頭,沒有傳說
制作玉杯,玉料的利用率通常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因此夜光杯的產量很有限。
認為夜光杯珍貴,也還不單單是因為這個。
一九五八年,酒泉夜光杯廠成立,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雇人雇牦牛從祁連山里運輸玉料。在夜光杯廠當過廠長的巴天才說,最好的牦牛,一次馱料也不過六十公斤。為了降低運輸成本,夜光杯廠一度派人上山,直接在料場就地“拉棒棒”——鉆取棒狀玉料,只把“棒棒”運下山來。“在基地附近一個羊圈里搭上帳篷,排一排小伙子……”
事實上,就算是今天的酒泉,要從祁連山里運出玉料來,也得請牦牛進山。產玉的地方,還沒修出車走的路呢。
酒泉夜光杯廠的一間展室里,至今還擺著一架木制磨床,它過去的名字是“旋車”。磨床的動力來自人的雙腳。雙腳在磨床下像踏腳踏風琴的踏板那樣輸出動力,踏板帶動一根皮繩,皮繩帶動磨床臺面上的橫向傳動軸來回旋轉。傳動軸的一頭,帶著一塊圓形鐵片,需要切割的玉料湊近鐵片,加入用水調成糊狀的解玉砂糊后,玉石在鐵片帶動的解玉砂磋磨下,漸漸被劃斷。
《天工開物》里,有一幅“琢玉圖”。它的磨床的樣式,玉工的工作場景,和酒泉夜光杯廠老工人在那臺老式木磨床上的工作方法一般無二。
一九七八年,原酒泉縣工藝美術廠,即現在的酒泉夜光杯廠才使用了電動機械進行玉器加工。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腳踏手扯,兩人合作的方式解玉。
切割大塊玉料,是兩人鋸木式。一張木弓子,以鐵線為弦,兩人往來拉動。鐵線帶動解玉砂切割玉石。用這種方法切割的玉石,切面斷茬是直線。
切割小塊玉料用磨床,切面斷茬是弧線。
鉆取棒料,是用小手弓上的皮繩帶動一個鐵皮圓筒——空心管鉆,帶動解玉砂鉆取。
腳踏磨床隨著傳動軸帶動研磨工具的不同,執行或切、或鉆、或磨等不同工作。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們甚至還能看到一幅古代波斯工匠的解玉圖。不看工匠的相貌衣著等特征,只看他手中的工具,簡直感覺中外工匠們拜的是同一個老師傅。
天然金剛砂不能直接使用,要先破碎后分級。粒度大的,用來切割玉料,最細的用于上光磨砂。
如今我們看到的舊玉料,切口光滑平整,使人想起古代關于“昆吾割玉刀”和玉料在山中土里柔軟,被開采出來后見了日光和風就變得堅硬的傳說。
那其實都只是過去的玉工們一下一下耐心鋸割研磨的結果。
對玉料的加工,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所以在每一道工序上,都要給后面的工序留有余地,寧可加工不足,不能加工過度。稍一疏忽,一塊千辛萬苦采到運回剖好鉆出的玉料就會作廢。所以,夜光杯的制作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對玉料由粗到細加工的過程。
首先,把鉆好的棒料根據杯子的高度切段;用管鉆掏出杯膛;用扎杯切削出杯子的外形——其實也就是具體而微的一個解玉過程;接下來的沖杯、碾杯、拓杯、溜杯、拉幫,也就是把一塊粗具杯形的石頭逐漸碾磨成一只沒有棱角、內外平整、沒有磨痕、規格統一的杯子的過程。這幾個過程結束后,夜光杯的粗加工業就結束了。
接下來的工序,是拋光。先用最細的金剛砂粉進一步加工,提高杯子的平滑和光亮度,然后用金剛砂粉和漆片配制成拋光膠,用膠整體打磨。剩下的兩道工序是給玉杯加溫上蠟。上蠟之后,再用馬尾網——用馬尾巴毛編的絲網——把杯子上的浮蠟擦掉。
這個時候,一只玉杯的加工制作才告完成,全部工序原來是二十多道,后來增加到超過三十道。
這種工作方式,效率非常低下。用這樣的工具割玉琢玉,一名成熟工人一個月下來只能生產出五六只玉杯。而據金石玉器鑒定專家李彥君先生稱,這種工作方式早在商代已經開始運用。
時間和金剛砂最擅長的是“磨滅”
有關過去酒泉玉石加工的文字記載,十分稀少。可以搜集到的資料,大多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這一段時期,實際上是從一九五八年朱德到酒泉那一次視察開始。之前的記載,不僅零碎而且可靠性極低,基本依靠口耳相傳而不是依據第一手資料。
過去的玉器加工行業都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并沒有形成行業內部的緊密聯合,而政府也并沒有把這一行業當做值得引起注意的產業對待,所以關于這一行業的規模、產業點的分布、產業的實際生產狀況都沒有記載。這些文字資料的上限到達清晚期,即酒泉縣工藝美術廠第一批老手工藝人的父輩健在的時期。可以想象的是,正是這批老藝人根據他們的父輩的講述給我們留下了當時酒泉玉器作坊一鱗半爪、語焉不詳的模糊場景。
這樣的場景……
酒泉最重要的史志之一,《重修肅州新志》,成書于乾隆初年。清代的玉器制作工藝被認為是代表了中國古代玉器的最高成就。即使在這本書里,也僅在“物產”一節里簡單提到“玉石,一名噶巴石……俱可琢器。治之者取山丹回回砂磨之”。
從中可知,當時的酒泉玉,已經被作為一種物產對待。而且,這種物產被用以雕琢。
沈青崖在雍正十一年以西安糧監道管軍需庫務駐肅州,他于此間寫下的《噶巴石歌》,也證實了這一點。
他們的點滴記錄或者偶然留下來的感想,也給我們說明了另外一件事:在雍乾時期,酒泉治玉不是從山中采玉,而是單一地從紅水河里撈取。
明末清初被認為是酒泉歷史上玉料、玉器加工最興旺的時期之一。當時酒泉的玉器作坊三十多家,產品除了在本地銷售外,還運往國內其他地方,甚至被帶到國外。
在極少的,被輾轉轉抄了多次的資料里,寫到酒泉晚清民國時期夜光杯產業的狀況的文字,既沒有具體的時間,也沒有具體的人物字號,也沒有確切的人物姓名,更談不到明確的資料出處。
只能想象,隨著和田玉加工貿易的進行,酒泉的玉器加工業曾經有過一段鼎盛時期,玉料價格上漲,形成了專業的采玉隊伍。加工行業生意興隆技藝純熟,產品得到更多貿易伙伴的認可。
是不是可以這么想,酒泉老山玉的大量開采,必定發生在內地對玉石的需求旺盛、酒泉玉器加工業繁榮發展的時期,而不是發生在民生凋敝,民不聊生,商業活動不活躍,產品滯銷,價格低迷的時期。原因很簡單:進山開采老山玉的成本太高。沒有豐厚的回報,就沒有冒險的動力。
這種時期,最大的可能恰恰是在中原和西域交通堵塞,邊地局勢很不穩定的時期。這個時期,因為和田玉的輸入發生困難,對玉的需求導致玉價急劇上漲。作為玉料交易重鎮的肅州,當然會受到最強烈的價格波動的刺激。玉料加工作坊就此想起了采玉人。一支又一支馱著毛繩編織的口袋的牦牛隊星夜出發,尋找早年間封閉的洞口。和田玉價格高漲的時期,應該正是它很難弄到的時期。
梳理絲綢之路在古代各個時期的通暢狀態,應該可以找到和田玉價格漲落的時段。
當然,這些都是推想。關于古代夜光杯玉料開采運輸加工等諸多真實情形,現在已經成謎。歷史就是這么一種東西,它的殘缺處,很多時候只能靠想象和推理填平補齊,而不是像一塊石頭,你想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樣子,用一個空心管鉆就能達到目的,或者更直接一些,把它一劈為二。
“歷史”就是這些零碎
我們能看到的古代酒泉玉雕實物也幾乎沒有。或者說,在眾多的古代玉器遺存里,我們難以分辨出哪些是用的酒泉玉料。
這只有兩種可能:
一、酒泉玉雕本身制作不多。
二、酒泉玉雕作坊基本都是外向型企業,產品以外銷為主。
因為缺乏成品玉雕件,惟一發現的酒泉玉杯又是素面雕,杯型也傳統,甚至上至戰國,下至今天都有這種杯型,準確判斷酒泉玉雕的成熟發展期,成為一個難題。
這當然算不上什么。日子,糊里糊涂也是可以過的。
我們能獲得的確實的關于酒泉玉杯制作的資料,來自民國時期即從事玉杯制作的民間工匠之口。如今他們都已作古,想要找到他們問個一二三四,已經沒有可能,只能從和他們接觸過的人那里得到若干一鱗半爪的“二手貨”,湊不出完整的工藝制作、錢貨交換、商品流通等場景。
酒泉工藝美術廠的前身是酒泉夜光杯廠,酒泉夜光杯廠的前身是公私合營后成立的酒泉夜光杯玉器合作小組。
根據一九六五年即到酒泉工藝美術廠上班直至退休的老藝人馬全忠回憶,當時廠里的老藝人有五位,他們是王三忠、王三義、馮子福、王永和、于加輝。
這幾位老藝人在解放前即從事玉雕。因為民國時期百業凋敝,他們多已改行日久,而且年紀也大了,不再適合這種需要耗費大量體力,要求心手如一聚精會神的工作。根據巴天才的回憶,他們當時最小的五十五歲,最大的已經七十六七,還能工作的人只有三個:王三忠、馮子福、王永和。
巴天才說,根據王三忠介紹,清中期酒泉的玉器作坊甚至在加工玉翎管、扳指、旱煙嘴、紐扣。那時的玉器加工不僅產業興旺,而且產品價格也好,一個老山玉的翎管能換四斗小米,好的能換一頭騾子或一頭牛。到了清代后期,訂貨的人已經很少,民國時期就更沒有人訂貨了。
玉器加工生意好的時候,采玉業也被拉動。作坊出錢請人進山帶出石頭來,一塊好玉料可以換到十幾公斤甚至兩三斗小米。玉器加工銷路不行的時候,像民國后期,已經沒有多少人從事玉杯生產,只有極少數作坊在勉強維持。
家庭作坊式的玉杯生產在消亡之前的回光返照是玉門油田創建時期,因為外國和內地專家在玉門開發油田,在酒泉駐扎采購,酒泉玉杯作為一種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藝品,被帶走作為紀念。
一九三七年,參與玉門油礦開發的兩位美國地質專家韋勒和弗雷德·薩頓在肅州期間,玉門油礦的創建人之一孫健初告訴他們肅州的玉酒杯很有名,于是他們在肅州城南門附近一家商店的后院找到了一家小作坊,買了十件一套的兩套,每套六元。當他們了解到玉杯磨制不易以及破損率極高之后,稱每個酒杯他要賣十二美元,而在肅州每個才合十二美分。
當時這兩位美國地質專家住的是肅州城鼓樓東全城最好的一家旅店里一等一的房間,每天的房錢是四角八分。而一只玉杯的價格是六角。
我們應該感謝趙辛而先生提供的這些資料。有很多在這時看來 嗦無用的說道,在他日可能是彌足珍貴的回憶,只是當時還不知道。
“夜光杯”是你叫的?
有一件關于購買酒泉玉杯的文字,出自文化名人易君佐之手,是一首詩,《宿酒泉》:
酒泉一夕夢迢遙,白盡天山尚作宵。
逆旅孤燈收客遠,雄關名鎮認前朝。
詩人欲共黃沙卷,歸意飄從碧落遨。
買得夜光杯在手,時危何日醉葡萄。
易君佐解放前曾任和平日報社社長,著有《張治中將軍視察河西記》、《敦煌心影》等。
張治中視察河西是在一九四八年深秋。易君佐寫這首詩,是不是就在這個時候呢?同時,他是不是張治中將軍此次視察活動的隨行人員?
我們看到,在可以接觸到的資料里。酒泉玉杯第一次被稱為“夜光杯”。
二零一二年春,酒泉圖書館作了一次酒泉奇石、古玉展。展品多來自館長秦國順的私人收藏。在這些展品中,有一塊拳頭大小的綠色石頭,說明上寫著“夜明石”。秦國順說,這塊石頭出自酒泉市肅州區豐樂鄉涌泉壩所在的祁連山口,夜間可發出熒光。但是這塊石頭質地粗糙,類似砂巖,用來雕琢酒杯,無異于在麻袋片上繡花,應該難度極大。即使成功,產品也不能討人歡心。
夜光杯怎么個“夜光”法,是一個謎。
有一件廣為人知并廣為酒泉文史工作者和玉雕作坊、企業利用的詩篇,是唐代王翰的名作《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也并沒有說明用的是酒泉玉杯。
而且,日籍華裔作家陳舜臣認為,寫這首詩時,王翰應該正在河南或湖南。他的經歷里甚至沒有到達涼州的記錄。
我們不得不重新說一次,詩歌這種東西,正常情況下,里面的字句不宜當做鐵一樣的證據。“瑰麗神奇的夸張和想象”一向是詩人的長項,越是好詩人,越能夸張,越能想象。嚴重的時候,這種夸張和想象甚至不局限于詩歌創作,會波及他們對所見所聞的回憶和描述。
但是在酒泉出售的所有被稱為“夜光杯”的玉酒杯,都在拿這首詩做幌子。
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帶隊參加春季廣交會的酒泉工藝美術廠廠長巴天才在交易會上爭取到了一個展位。為了把夜光杯盡最大可能推出去,他想出了一個“買二送一”的辦法,讓廠里兼有會計、設計等職責,會刻字,寫字漂亮,出身于治玉世家的蔡生萬(約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寫了若干書法作品,作品內容就是王翰的《涼州詞》,誰買一對杯子,送一幅字。“日本人喜歡。三四天里拿去的四五百個杯子都賣了。又拿了些杯子,也都賣了。”
唐詩,對于日本人來說,似乎是一個巨大的魔咒,幾乎是無條件地喜歡。這一點,我們可以很簡單地從紫式部《源氏物語》里找到依據。紫式部出生于公元九七八年,相當于宋初。《源氏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地位,約相當于《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在這本書里,日本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在大量地背誦和學習唐詩。
文化程度不高的巴天才,誤打誤撞,憑借文化的力量,撓到了日本人的癢處,讓日本人歡喜贊嘆不已。
我們至今能找到的確切寫明是酒泉所出夜光杯的文字,只有易君佐的那首詩。
根據能夠搜集到的資料來看,酒泉玉杯生產的歷史,至晚應該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但是很長時間以來并不就稱為“夜光杯”。正式根據古籍和唐詩中的記述把酒泉玉杯稱為“夜光杯”,應該在晚清至民國這一段時間。
酒泉玉的發現和利用,酒泉“夜光杯”的興時一時,應了老話中的那一句:“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是在人見人愛的和田玉一度供應不上的時候,在“夜光常滿”的傳說難以印證的時候,酒泉的玉工們拿出來聊作安慰的替代品。
琢玉的舊年時光
琢玉的老漢“身體成了三角形”
在肅州區檔案館里,我們能見到的面向社會開放的檔案里,關于酒泉夜光杯廠最早的檔案,是一份一九六零年四月五日頒發的任命書,寫明任命陳掌林同志為酒泉夜光杯廠廠長。文書上蓋有代市長趙北克的一方簽名圖章,還有“酒泉市人民委員會”的大印。
一九七一年,酒泉縣工藝美術廠向上級打報告,稱按照天津外貿公司和省進出口公司對玉器產量及花色品種的要求,申請擴大廠房,解決車床、電動機,以利發展生產。
在車床、電動機運用于酒泉夜光杯制作之前,酒泉夜光杯的制作是全手工時代。
手拉腳踏的磨床生產效率極低,一個熟練工人一月生產五六只杯子而已,全靠手眼身心高度專注協調,避免稍不注意導致產品破損而前功盡棄。就是這樣,生產出來的杯子也還是難以避免大小不一厚薄不均等不如意處。巴天才至今收藏有一只手工制作的玉杯,壁厚達到三毫米,而且因為壁厚,導致通透感不足,材料發“實”,拋光也不足,發“悶”發“啞”。
因為機械簡陋,生產效率低,需要治玉工人長時間專注地盯緊玉料和磨床上的鋸、鉆、砣等工具,根據工作進程隨時調整手中玉料的方向位置,同時另一只手還要撮起經水調過的金剛砂漿,腳下還要一直踏動踏板,給磨床提供動力。
馬全忠說,工藝美術廠建廠之初的老藝人馮子福,因為長年拉砣,身子都成了三角形。一九四二年,工廠派人到天津特種工藝廠學習技藝,當時馮子福已經六十多歲,也去了。但是因為他是左利,天津的機器都是按右手工作設計,使用起來別扭不順。而且他年紀大了,學習效果差,視力也下降,精細加工部分看不清。六十多歲的老漢著了急,在天津哭。哭也沒有用,學習沒有結束,他就回來了。
將要在二零一四年退休的夜光杯廠老藝人魏建民,右手的幾個指頭因為長年撮取金剛砂和掌握工具,指甲變得厚而粗糙,密布裂口。雖然他現在已經很少再做加工,指頭上的職業傷害卻已經難以恢復。
“看瓜”的魏建民
因為看守照管瓜田的人往往是年紀較大的男子,在瓜田里又幾乎總是只有他一個人,所以,在酒泉,人們習慣于把不管做什么事負責最后留守的那個人比喻為“看瓜老漢”。
二零一二年,已經五十八歲的酒泉夜光杯廠老工人魏建民就是一位“看瓜”的人。這個時候,魏建明其實已經不從事實際生產。他主要的工作是在夜光杯傳統制作工藝演示中當“演員”。
在加工了四十年夜光杯后,魏建民對夜光杯雕工藝的傳承已經不再樂觀。四十年里,他先后帶過五十個左右的徒弟,這些徒弟現在都已經不從事這個行業——工資太低太低太低。
酒泉夜光杯廠工人的工資水平可以從魏建民本人的工資大概推想——他每月的工資“把該扣的扣掉拿七百六十元,退休后拿全能拿一千二百元”。二零零六年退休的馬全忠,退休時的工資是八佰元,到二零一二年漲到接近二千元。二零一二年,在酒泉的大小菜館酒店里,招個端盤子的小服務員,還是生手,管吃管住之外,也得開出至少一千二百元一月的工資,還不一定能招到人。
因為性格里的“不愛折騰”,趨向“安穩”,當年年富力強而且身懷絕技的魏建民曾經有三四次離開酒泉夜光杯廠“另謀高就”的機會,但是都沒有付諸行動。其中一次,對方甚至開出了給他一套樓房,每月工資幾千元的誘人條件。那是二十年前,當時一個事業單位職工的月工資不過二三百元而已。
“現在看來,當時走掉是對的。”魏建民說這話的時候,本來說話就平和的他音量又低了幾分。
在魏建民的敘述里,同樣音量降低的部分還有說到他目前從事的“表演”工作:“這也是在傳承文化。”
這樣,從個人收入角度看,夜光杯雕的傳統工藝傳承已經“不合算”。除非有人特別愛好這項工作,不計較經濟收入。
我們知道,這樣的人向來不多。
魏建民干脆認為“沒有”。
甚至就連夜光杯廠總經理蔡捷也說,如果不是為了把老祖宗留下的傳統工藝傳承下來,真想改行。
工藝的不復純粹,傳承無望,回報低微。魏建民留給人的印象是,他對他的工作從內心里充滿了矛盾。
他是一位手工藝人,而不是一位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的的廠長或商人,也不是一位只在酒泉短暫停留的游客。對于任何一個手工藝人來說,一件產品從自己的手中誕生,都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在其他任何一個每件產品都具有惟一性的行業里,也是一樣。
在酒泉夜光杯廠的展銷大廳里,魏建民能準確地從琳瑯滿目的玉雕里指出他的作品。那些作品,從一塊只有熟悉它們的人才能準確判斷它的品質的石頭,在魏建民的手里被磋磨成溫潤優雅的產品。在這個過程里,石頭和雕琢石頭的人之間,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傳的聯系。這種聯系不是單純直白的作者與作品的關系,更像是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同樣,對于這一項技藝的傳承,在魏建民看來,當然也應該和政府、董事長總經理、普通游客、一般市民的感受又有不同。
老藝人馬全忠家的一個柜子上,還陳列著當年他親手制作的一個岫玉雕件。巴天才家客廳里的一個玻璃架格上,擺著幾件夜光杯,其中一件他最為珍視的,是一只鵝黃的小酒杯,全手工時代的產品。高正剛的前妻張玉慧,是魏建民的師傅,已經去世。高正剛還珍藏著她親手制作的四只玉杯。
魏建民的家里呢?
每年夏天旅游旺季,都會有很多外國游客到廠里參觀,興奮地和魏建明合影。在他們眼里,身懷傳統技藝的魏建明是一道風景。
要繼續闊下去,還得再攢勁
“手溫”的失去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酒泉工藝美術廠生產的夜光杯品種并不多。
如前所述,一九七一年,工藝美術廠的產品價目表實際只開列了四種產品。一九七九年,工藝美術廠曾制定了一個簡單的質量標準。這個標準只有手刻油印的兩頁十六開紙,一頁上寫著四條質量標準,全文半頁,另一頁上,以圖示的方式開列了大小高杯、大小平杯的規格。直到一九八零年的一份文件里,才說到“全廠集中力量投入夜光杯及盅、盤、碗、盒等平素玉器的生產,調整技術力量,分為九個車間,專制七種規格的夜光杯” 。
排除了一段時間內市場因素的影響,我們看到工藝美術廠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新產品的主動研發投入的關注嚴重不足。大小高杯和大小平杯的生產,實際上在清末就是酒泉夜光杯生產的主流,直到今天,它們的形式也沒有什么變化,只是在工藝上有所進步而已。幾十上百年如一日地生產有限的幾種東西,初見夜光杯的人可能“眼前一亮”,卻不能做到以后一“亮”再“亮”。
直至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間,新開發的產品才算邁出了較大的一步,有十三項新產品被研發出來,如仿古型、龍鳳尊、啤酒杯,和其他非酒具產品相加,品種上了一百。
機械機具的改良提高了夜光杯的勞動生產率以后,產品的品質也較手工時代有了大的提高,但是手工的質感和它使人聯想到的淳樸風雅,以及對于流失的時間平心靜氣的撫觸也隨之失去了基礎。
花色品種的增加,并不是因為思考的深入,也不是因為對自己的挑戰獲得了成功。新的高度,一直沒有到達,或者正越來越遠。一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玉雕產品已經可以不帶任何手工的痕跡,平整的地張上密布均勻細密的直紋,圖案也死板僵硬。因為缺乏精神的投入,也沒有得到過帶有感情的抓握撫摸,它們不能讓人從內心里生出尊重和熱愛。
某種東西,被恭恭敬敬地供奉起來,寫入回憶錄,做成雕塑的時候,是不是說明,它已經死亡了?
機械化生產剛剛開始的時候,它帶給人們的震撼和欣喜的力量是巨大的。酒泉夜光杯廠沒有留下手工磨床、手拉弓鉆等工具。直到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才又投入資金仿制了兩套手工設備放在展室中,供游客參觀時做模擬表演。用這樣的設備,一個月才能生產出三四只玉杯,如今誰有這樣的耐心?
夜光杯廠成立之初進廠當學徒的工人,現在多已在安享晚年,他們會用這些設備。再過若干年,這些家什的用法也許也會成為古董本身。從游客饒有興趣地觀看玉杯加工表演的情形看,這應該不會是什么意外。
想象一下,如果某一天,酒泉的某條陋巷里出現了這么一間作坊:木門窗上油漆剝落,或者還有誰家小兒用粉筆開列的一道兩位數加法豎式。門內光線略嫌不足,一位老者正踩動踏板,磨輪一正一反刷刷地轉動,鼻架老花鏡的老者目光專注,隨著金剛砂漿的不斷添加,一只玉杯的形狀正在手中逐漸顯現。因為經年累月精細專注的手工勞動,他的面容安詳寧靜,言語也平和樸實,令人尊敬。中午,他端起老妻送來的飯盒,在陽光下打開,是一盒白米飯,米飯上是兩條蔥燒鯽魚,火候正好,顏色正好,味道也正好。
……
一九八五年,一位署名“木斧”的游客在夜光杯廠的留言簿上寫道,“杯中有詩”。
這么四個字,讓人久久無言。
“我們比先人聰明”是個幻象
酒泉手工治玉的第一聲嘆息應該始于一九七八年電動機的引入。
速度和效率永遠是手工藝行業的大敵,它的出現,類似于創世紀傳說中那條蛇的出現,它誘使亞當和夏娃吃下禁果,使亞當和夏娃產生了對自己赤裸身體的羞恥。而對于慢工細活的工匠來說,這種羞恥來自與機器相比手工制作的低效率、低收益。
夜光杯傳統制作工藝的失落和后繼乏人不是個別現象。
二零零七年,中國工藝美術協會發起了一次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工藝美術行業最大規模的普查,直接參加普查的隊伍達到一千三百人。這次調查結果表明,我國七百六十四個傳統工藝美術品種中,百分之五十二點四九的品種因后繼乏人等原因而陷入瀕危狀態,有的甚至已經停產。
有結論說,傳統工藝美術大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但因多為手工工藝、制作復雜而出現后繼乏人的問題。
是這樣的嗎?
工藝美術產品的“名貴”,更多地體現在產品本身的獨特或者說“惟一性”“稀缺性”上。然而 “這樣的東西,我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淺層自得也很讓人沉溺。
劉漢明拿出一把玉雕掛件說:“你挑一個。”
那些用各種雜玉雕制的小彌勒佛像,全都一模一樣,都是他所說的電腦雕刻產品。
收拾率頗高的中央電視臺“尋寶”欄目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專家們指出“寶貝”上現代機械加工的痕跡,說,這就是一件現代工藝品,擺一擺還是很好的。
傳統手工藝品制作年代里,技藝傳承的三種主要方式是有道理的。家族傳承,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保證了技藝本身應有的地位,也始終能保持消費愿望的積聚,不至于讓技藝和產品都成為“大路貨”。更進一步想,酒泉夜光杯在歷史上既沒有具體詳細的行業發展狀況記載,也沒有“秘術”“規程”或“夜光杯制作則例”等文字性的東西留下,理由可能也正在這里。
我們常常以為我們比祖先聰明,比他們懂的多。錯了。
手工藝、制作復雜,正是手工藝作品的生命所在。現在這些工藝之所以難以為繼,是因為它們失去了這些特征。它們現在由機器制作,會按按鈕的人即可從事生產——一塊石頭丟進機器,一會兒就刻好了。
而且,歷史上,每一種具有獨特魅力的手工藝產品加工行業,都不會出現大忽隆式的興旺景象,都只是由少數人在寂寞地傳承和制作,從而保持產品的市場地位。這些手工藝制作由作坊式而工業化之后的繁榮興旺,是殺雞取卵后關于“豐收”的短暫幻象。在很多中國民間傳說中,這種行為被認為是愚蠢的,不可持續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歷史上真正掌握手工藝制作的不傳之秘,能夠在作品中注入思想和愛,還有靈魂的人,本來也“就這么少”。而那些追隨經濟大潮的成功者隊伍,雖然壯大而繁榮,最終也只不過是漂在水面上的牛糞,不是沉在水底的金子。
歷史上已經失傳的技藝何止一種,真正熱愛這些技藝的人,會用生命讓它復原、再現。沒有記載,沒有師傅,都不是問題,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人傳承,也不是問題。只要有作品在。另一方面,一種技藝,一件作品,已經沒有人對它有興趣,失傳了又有什么可惜!
“高高在上”成為懷想
夜光杯的制作,需要二十八道甚至更多工序。在全手工時代,能順利通過選料鉆坯掏空拓展研磨燙蠟拋光諸程序而蝶變為夜光杯的石頭,不能算多。更何況加工制作一只杯子需要投入諸多人力和時間。所以,在全手工時代,夜光杯一直都是作為一種奢侈品存在的。
曾任肅州區文化館長的高正剛說:(夜光杯)其實沒有什么實用價值——拿什么不能喝酒?
除了巴天才聽到的老人們關于玉料、玉杯換糧食、牲畜的回憶,和記載中孫健初帶領美國專家買玉杯時提到的價格情況,我們還可以從檔案里找到關于夜光杯“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的消費價格紀錄。
酒泉縣工藝美術廠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形成的一份產品價目表上標明:高座大啤酒杯二十五元一個,平座大啤酒杯十元一個,高座小酒杯八元一個,平座小酒杯三元一個,蓋碗一套(三件)八十點八元。
而當時工藝美術廠的三名紡織二、五、六級工人工資分別為三十八點五元、六十五點四元、七十點九元。作為廠干部的巴天才,直到一九七六年月工資也才只不過五十五點九六元,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夠買一套玉蓋碗的——現在有這樣的廠長嗎?
一九八零年代,一位在酒泉工藝美術廠參觀購物的香港游客——我們眼里的“有錢人”——在留言中抱怨:夜光杯好,價格昂貴。
高正剛回憶,建廠初期,在夜光杯廠從事過設計雕刻的蔡生萬還曾設計研發鑲金鑲銀的玉杯。這應該屬于酒泉夜光杯中的高端產品。但是很快被人批為有悖傳統,不倫不類,并沒有形成實際生產。這段時間,普通的夜光杯已經不是一般人家能夠消費得起的高檔工藝品,鑲嵌貴金屬后,它的消費人群當然會進一步縮小,不能投入實際生產是必然的。
如果蔡生萬的設計開發是在二零一二年,情況可能會大大不同。
如果今天的游客能穿越時光,看到手工碾制夜光杯的場景,他們絕不會為一只造型別致優雅的竹節杯和賣主討價還價。耗費了那么多精神心血的一只杯子還賣不到五十元人民幣,而在酒泉,二零一二年吃一碗牛肉面也要五元,這不是大家最愛占的便宜是什么?
永遠有先知先覺的人,他們在吃第一只肉雞腿的時候,就已經發現它雖然肉多,但不如土雞腿滋味醇厚。
最甜蜜的那一段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是能引起酒泉工藝美術廠工人甜蜜回憶的十年。那是酒泉夜光杯生產和銷售的黃金時代。酒泉旅游業開始起步,慕名到敦煌參觀的港澳及外籍游客路過酒泉。當時的酒泉夜光杯廠有各種加工設備八十多臺,職工最多的時候達到一百八十多人,年加工銷售各種夜光杯三萬多只。酒泉夜光杯供不應求,在更多人眼里,夜光杯真正成為酒泉的標志。
一九八七年,中國工藝品進出口總公司下發文件,指名要求酒泉夜光杯廠選派一人參加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三月十七日由日本高島屋株式會社舉辦的第七次“大中國展”,進行“夜光杯古式成形表演”。這份文件上要求派人參展的公司(廠)全國只有五家。時任酒泉夜光杯廠廠長的武夫參加了這次展會。武夫一九六五年參加工作,一直從事玉器制作、設計等工作,文件上稱他“技藝嫻熟,業務精通”。
現在想想,在我們大力追求“經濟效益”的時候,日本人關心喜歡的居然是“夜光杯古式成形”而不是我們熱火朝天地進行半機械化生產的場景,令人羨慕嫉妒恨。
二零零五年,一支由日本人組成的采訪隊伍經過酒泉,他們找到馬全忠做了短暫的采訪。后來,他們給馬全忠寄來了一期周刊。在那本記錄絲路風物的周刊上,他們對馬全忠的職業也表現出了特別的關注。
一九八八年四月,武夫還代表酒泉夜光杯廠參加了第三屆全國工藝美術藝人、專業技術人員代表大會,受到了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一九九一年,武夫被甘肅省輕紡工業廳授予“甘肅省工藝美術大師”榮譽稱號。同一份文件上,被授予這一稱號的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的雕塑家、“黃河母親”的作者何鄂。
在生產量大幅提高的同時,夜光杯的花色品種也快速增加。為了滿足低端市場的需求,也為了最大限度地把來之不易的原材料“吃光榨盡”,充分利用,夜光杯廠甚至開發出了用下腳料制作的微型夜光杯。這種小杯設計新穎,小巧玲瓏,年產量達到三千只,創產值貳點七萬元——一只小杯的終端價格只有九元。這個項目獲得了酒泉市二輕工業局一九九一年的技術革新獎,獎金是一百元,在當時大約相當于一個普通公務員月工資的三分之一。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六年間,酒泉夜光杯廠被國家旅游局、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號”“全國旅游商品研評會金獎”等諸多榮譽和獎項。
這一時期,到酒泉夜光杯廠參觀訪問的除了普通游客,還有眾多“重量級”的人物:彭德懷夫人浦安修,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國務院原副總理陳慕華,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總參謀長伍修權,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泰國公主瑪哈扎里克·詩琳通,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馬萬祺……
酒泉夜光杯廠的展室里,至今懸掛著他們來參觀時的題字和照片。
在一九八三年之前,朱德、葉劍英、黃鎮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曾對夜光杯雕予以關注。
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做了一些采訪。和那些與夜光杯有關的人談話,看他們手里的照片和夜光杯,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們好像沒有一個考慮過要保守這個工藝本身的秘密。所以,前后算起來有半年,我都在利用休息時間尋找他們,雖然正在談話的時候也許會接到電話,要求我立刻去聽一個什么會,也仍然覺得這樣的采訪有巨大的吸引力。
有一些東西,不問,可能就永遠湮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