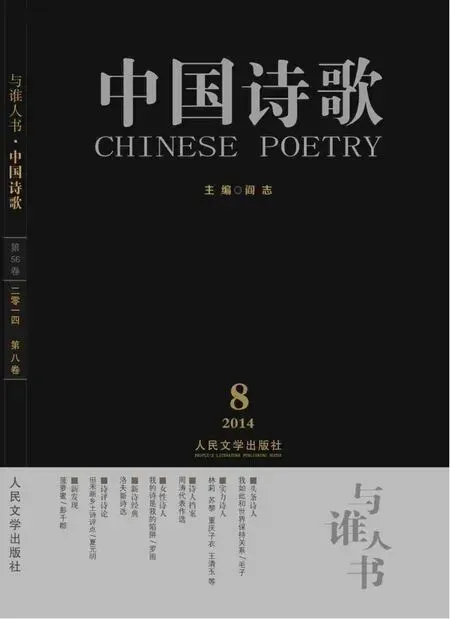羅鹿鳴的詩
羅鹿鳴的詩
LUO LU MING
牌樓,高處一朵石蓮
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
宏大,壯闊,肅穆而莊嚴
我呢,只是宮殿前貌似孤獨的
一座堅定不移的石牌樓
在游客最先看過之后
便被亦步亦趨的腳蹬在外面
不,我還不是那繁華落盡的牌樓
失意在黃昏的霧霾
我只是牌樓上一朵開放的石蓮
如過江之鯽的幢幢身影
有誰會駐足瞬間
人們只一味地向前,向前
對高處的事物
不是吝于仰望,就是視而不見
蓮的清芳飄散在四野之間
亭閣懷春
鉆過木柵欄的
返老還童的濕風
在園子里放浪形骸
捏紅了三月的山茶花
慫恿不諳世事的蜂
撞得亭閣的窗欞憐香惜玉
撩撥得那只花貓
翻墻,恐怖地嚎春
風卻潛入閣內
對閣頂的藻井放肆偷窺
覬覦已久的月亮
黑著臉,弓著背
在寶頂之上
溜之大吉
華表,謗木的轉世
剛直的木頭,飛翔兩臂
形似桔槔的謗木,開始了
蜚短流長,波譎云詭的
朝堂之外,民聲民意
借此翻越高墻,躡手躡腳
直達圣君龍顏
歲月的消磨使它孑然一身
還有皇權的風蝕水毀
謗木腐朽之后,一個制度
倒塌出電閃雷鳴
用上好的石料替換謗木
于是,華表隆重而莊嚴地誕生
形在,而神卻相差十萬八千里
恰如貍貓換太子
換來的只是一具石質的空皮囊
承露盤曬干了最后
一滴長生不老的甘露
那只叫做的神獸,從此
充耳不聞民間疾苦之聲
只徒具,有時望君出
有時盼君歸的
形式主義
八角形的龍柱出沒于云紋
日月板上的圓太陽和長月亮
也在云朵里潛身而行
渾身是膽的須彌座緊貼大地
撐起的不是藍天,而是
沉重的文化底蘊
石柱頭、石柱身、石基礎
三位一體的是巍巍乾坤
須彌座,誕生與變形
佛,坐在圣山之上
撥動念珠如一顆地球
善惡拿捏其間,蓮花朵朵
朵朵蓮花開處
法號長鳴,法幢飛揚
這座有著迷你名字的
須彌山不高,其實只比人心
高出那么一截
那里長森林,也長花草
九色鹿在陽光下奔跑
佛在放牧一群似是而非的羊
人呢,則長成了菩提樹
佛呢,其實是人類的一只頭羊
當須彌山藝化為須彌座
它便收斂自身
婀娜的束腰,上下仰伏著
清凈無染的蓮瓣
那是輾轉生生,造化
不息的象征
須彌座上的蓮花
與鹿與鶴這類穿越時空的
靈獸為伍,面向天空
打開自己的胸懷
為一切向上的事物
提供無限向上的想象
屋舍、牌坊、華表、影壁、獅子
香爐、日晷、旗桿、花盆
都可以在胸膛之上任意地生長
讓它物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讓云紋,欲停還飛
而自己,就如那伏蓮
低得只有體己的大地相連
香爐,青煙香灰的居所
用三條鐵腿抓緊大地
爐足上的金猊,在過慣
吞云吐霧的生活之后
又矢志不渝以煙熏火燎為生
鼎立在中軸線上,作一個挺拔的
不滿足于當一座供人
觀賞的殿前擺設
而樂意,讓燒香敬佛的人
將一顆心煨得熱乎乎的
滾燙燙的,讓香火的舌頭
添著面冷心熱的鐵帽
任各種祈愿不斷地向上飛揚
在寶頂之上,青煙朵朵
芬芳中,有誰聽到
香灰崩塌的梵歌
你是否是聽香的那一個
安居在深凹底座的
白燼香灰,是否還在揣摩
大殿里,那尊笑面佛
是皮笑肉不笑,還是
皮笑,肉也笑
日晷的訴說
有誰還記得日晷的影子
太陽的尾巴曳過大地時的樣子
光的羽毛投影在圓盤之上
長長短短的晷度里
響起歲月走來走去的聲音
仿佛沒完沒了的
恩怨是非
時光留給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多
有的人卻在時光里永生
有的人,連一聲咳嗽
都沒有留下
歷史深處的回音
變成了鐘表,嘀嘀
嗒嗒的雷鳴
碑碣,發現與永恒
如果歲月是一座碑
有沒有剝落的時刻,甚至
有沒有倒塌的事情發生
因為時光飄忽不定,也
太不可靠,為了留住
匆匆而行的分分秒秒
于是,人們想起了碑
從此,擔起刻文記事的責任
也落下了樹碑立傳的心病
一些人,任由毀譽一生
也舍不得從碑刻里跳下來
如花落紅塵
流芳千古的終得流芳
遺臭萬年的豈是浪得惡名
逃避歷史審判的伎倆
如何逃出人心,看
碑碣,勇敢地舉證
石幢的祈愿
在佛寺大殿之前傲然站立
如傘,飾以絲綢寶珠
的經幢,或者挺拔在佛寺的
殿堂中央,隱忍著自己的
頭顱,讓經文與佛像
或垂或飛,幢影映及人身
甚至幢上的灰塵
都能避除人的罪垢
經幢搖身變成石幢
是不是一個華麗的轉身
是不是一步之遙的距離
或許,只是一個念想的發生
本是八角形的腰桿
卻因修福業,行善事
頂天立地一偉丈夫
凝固的瓔珞硬化的垂帶
風撼不動雨蝕不滅
消災祈福,解冤除罪
恰如永不發聲
永不消失的
逝水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