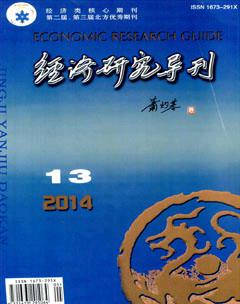重慶市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陳海燕 陳佳陽
摘 要:運用泰爾指數和基尼系數從不同收入層次、不同收入來源兩方面分析重慶市農民不同收入層次的內部差距,并建立線性或非線性回歸模型研究影響因素的作用軌跡。研究發現,重慶市農民不同收入層次的內部差距穩中有升,主要歸因于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的擴大。經濟增長總量和農村固定投資額度將有助于縮小農民內部收入差距,但是現行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工業化的加速將擴大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進而持續擴大農民內部收入差距。
關鍵詞:農村居民收入;內部差距;倒U型關系;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3-0222-05
引言
直轄十七年來,重慶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逐年遞增,由1997年的1 692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7 383元,特別是“十一五”期間重慶市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大大提升,從2006年的2 873元增長到2010年的5 276元。在2002—2011年間區縣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為14.6%,渝東北翼地區和渝東南翼地區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5.1%、15%。農民收入的提升,不僅直接加速農民生活的改善和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更正向地影響著地區經濟結構的調整乃至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且農民增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總體購買力和市場的總規模。但是,當人們關注重慶市農民人均純收入上升的同時,其內部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內部收入差距是擴大還是縮小更值得引起重視。
農村居民群體的收入平等問題直接關系著地區經濟的和諧發展和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許多學者運用泰爾指數、基尼系數等刻畫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比如對全國農村居民收入來源不平等(唐平(2006)、葉彩霞等(2010)等)[1~2]、城鄉收入不平等(王少平和歐陽志剛(2007)等)[3]、行業收入不平等(李娜等(2013)等)[4]、省市間收入不平等(萬廣華(1998)、孫慧鈞(2007)等)[5~6]等問題進行研究。當把某地區或某省市農民收入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差距研究時,采用的農村居民收入數據為全部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這將不能反映出不同農民收入層次的內部差距。
關于農民不同收入層次差距的研究文獻,主要有分析不同收入層次農民的消費模式,比如盧方元和魯敏(2009)選取五個不同收入組作為橫截面,建立了九個消費模型分析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7],馬薇和楊超(2002)中分析了城鎮居民收入層次與消費彈性的關系等。而對于農民不同收入層次差距度量的研究并不多,李政(2004)給出了定性的分析,但未進行內部收入差距度量[8];黃祖輝等(2005)通過微觀調研,對村莊內部和村際收入差距進行了分析[9]。
對于大城市與大農村結合體的重慶市,農村地域廣闊、基礎薄弱、人口眾多,有100多萬貧困人口集中在三峽庫區、大巴山區和武陵山區,還有40余萬人在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深山陡坡峽谷地帶。在重慶市38個區縣中有19個區縣處于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其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等受到生態環境制約,約束了部分農民收入增收途徑。處于一小時經濟圈范圍內的農民收入明顯高于兩翼地區,而受主體功能區劃、土地流轉、城鎮化、工業化等政策的影響,圈內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也明顯快于兩翼地區。這表明在重慶市農民平均收入提高的同時,部分農民收入被平均化。針對重慶市農村居民收入情況,黃應繪(2007)將重慶市分為三大經濟區,利用泰爾指數從區內、區間對農民收入差距進行了測度[10]。那么,目前重慶市農民收入內部差距是怎樣的,其收入來源的差距如何,對收入內部差距起主要作用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已有研究成果寥寥。本文將從不同收入層次和不同收入來源兩方面去探究重慶市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并分析其主要的影響因素。
一、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測算
1.數據說明與描述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2005—2013)》,考慮到每年物價水平變動幅度不一致,采用1997年為基期(1997=100)消除物價因素影響的農民人均收入。根據所有調查戶依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隊,按五分位數20%、20%、20%、20%、20%的比例依次分成:低收入組、中低收入組、中等收入組、中高收入組和高收入組等五組。由于重慶市不同收入組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數據統計是從2004年開始的,所以本文研究時間范圍為2004—2012年。收入來源分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等四組。①
鑒于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占比達到86%以上,表1給出2004—2012年這兩部分收入的原始數據。
圖1給出了重慶市農村居民家庭總體收入來源趨勢。可以看出,工資性收入與家庭經營性純收入在農村家庭中占比最大,且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占比最低。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之前都是工資性收入低于家庭經營性收入,2010年開始前者高于后者,說明受城鎮化、工業化影響,農民進城務工的收入開始漸漸大于家庭經營性純收入。但是從圖2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民群體看,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收入群體從2008年開始,其工資性收入大于家庭經營性收入,而高收入群體的工資性收入在樣本期內一直低于家庭經營性收入,這說明真正能提高農民收入的來源是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純收入。
2.收入差距測算
目前度量收入差距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采用絕對指標,比如收入的標準差、極值等具有量綱的指標;二是采用滿足匿名性、齊次性、總體獨立性、轉移性原則、一致性的相對指標,比如沒有量綱的基尼系數、廣義熵指數等。在研究重慶市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時,本文將從收入層次差距和收入來源差距進行測算。收入層次差距采取泰爾指數進行刻畫,收入來源差距則采用基尼系數進行刻畫。
泰爾指數(Theil index)是Theil (1967)利用信息理論中的熵概念提出的衡量個人或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指標。廣義熵指數定義為:
其中,n表示總的個體個數,yi表示第i個個體的收入,y表示平均收入。參數α表示對收入差距的厭惡程度。α取值越小,厭惡程度越高;反之,厭惡程度越低。當α=0時,為泰爾第二指數,也稱為泰爾L指數;當α=1時,為泰爾第一指數,也稱為泰爾T指數。
泰爾T指數的取值范圍為0~1,當收入絕對平等時泰爾指數值為0,泰爾指數值越接近于1,說明收入差距越大。
基尼系數采用矩陣的方式進行計算[11],公式如下:
GN=PQI (3)
其中,P為行向量,研究不同收入來源的收入差別,將每種收入來源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算出來,按照人均收入由小到大排列得P矩陣。I為列向量,獲得步驟與P相同,唯一的差別在于包含的是收入比例。Q是一個方陣,上三角元素是1,下三角元素是-1,對角元素為0。
采用公式(2)和(3)計算重慶市農民收入差距的結果(見圖3),泰爾指數反映的是重慶市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反映的是重慶市不同收入來源的農民總收入差距,兩種差距折線變化趨勢總體一致,都呈現出在波動中整體逐步上升的趨勢。
從圖3中看出工資性收入差距在波動中具有明顯的縮小、放緩趨勢,這得益于“十一五”期間重慶市大力推進城鎮化、工業化政策,為農民外出務工獲得工資性收入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呈現出“先減后增”的周期循環趨勢,尤其在2008年收入差距突然加劇,波動幅度加大。值得注意的是,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引起的不平等在2008年發生了異常變化。在2008年由于60%(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和中收入戶共占比為60%)的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增長率下降,而工資性收入提高,導致此年的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基尼系數偏高,同時工資性收入的基尼系數下降。
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差距都呈現出平穩的波浪式變化,收入差距并不明顯。因為直到2010年,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才達到2%左右,其收入渠道有限、收入金額很小,而轉移性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在10%左右,所以這兩項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明顯。
因此可以說,正是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大幅變動引起了重慶市農民收入內部差距的變化。
二、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分析
結合上面的結果分析影響因素對重慶市農民收入總差距、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和工資性收入差距的影響力。已有文獻中鮮有對不同層次和不同收入來源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研究可參考,文獻徐增海(2011)[12],高連水(2011)[13]和潘文軒(2010)[14]中主要選取了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城鎮化、政府對基建和教育投資、人口負擔率、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當地農民整體收入也會提高,但是由于經濟發展紅利分配不均也可能導致農民收入內部差距擴大;工業化發展通過增加就業機會,將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還將導致對農產品的需求,帶動農民經營收入的增長;城鎮化通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能增加人均耕地面積,提高農業邊際生產率和農業經營收入;農村固定投資的增加,無疑將改善農村生產經營和投資環境,有助于農民收入的增加;家庭經營性收入與農產品價格指數有關,過于低廉的農產品價格不僅降低農民收入,而且會傷害他們的經營積極性。又由于重慶市不同收入層次農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數據無法獲取,且沒有按照縣域地區進行劃分,也無法獲取不同收入層次的人口負擔率。所以選取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農村工業化水平、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農產品價格指數為主要影響因素。
經濟增長水平用實際GDP衡量,單位萬億元;城鎮化水平用城鎮常住人口占常住總人口比重表示,記為UR;農村工業化水平用鄉鎮企業勞動力占農村總勞動力之比表示,記為GYH;農產品價格指數記為API;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記為RFA。泰爾指數計算的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民收入差距記為GE,基尼系數計算的不同收入來源的農民收入差距記為GN,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和工資性收入差距分別記為JGN和GGN。數據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由于影響因素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且為了說明每種因素對收入差距的獨立影響,故針對每一種因素建立線性或非線性回歸模型。下面所列模型均為多種擬合模型中的最優形式,選擇標準為滿足模型整體顯著和參數顯著,且AIC值最小。考慮到2008年家庭經營性收入的突變,設定D1為0~1取值的工具變量。
1.經濟增長水平的影響
進行多次擬合后受經濟增長水平影響的最優模型(見表1)。
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經濟增長水平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都是顯著的。泰爾指數和總收入的基尼系數與GDP之間是非線性的倒”U”型二次曲線關系,其對稱軸分別為0.75和0.738,重慶市2010年的GDP為0.79萬億元,即在對稱軸的右邊,這說明隨著經濟增長水平的持續提升,重慶市農民收入內部差距將縮小。工資性收入差距與GDP之間是斜率為負的線性關系,隨著GDP的增加,工資性收入差距將逐步縮小。而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與GDP之間為非線性的不對稱”W”型關系,GDP的影響效應不明確。
2.城鎮化水平的影響
進行多次擬合后受城鎮化水平影響的最優模型(見表2)。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城鎮化水平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都是顯著的。城鎮化水平對農民收入內部差距的作用都是正向的,意味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將擴大農民收入層次之間的不平等和農民不同收入來源之間的不平等。城鎮化的提升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進城務工機會,將促進農民工資性收入大幅提升,縮小中低收入者與中高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但是,城鎮化對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負向的,城鎮化水平越高,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越大。對進城務工以獲取工資性收入的農民群體,其家庭經營性收入必然下降,相對以家庭經營性收入為主的高收入群體,進城務工機會成本較大,即其工資性收入增長幅度遠遠不如家庭經營性收入。所以,城鎮化是把雙刃劍,吸引的是家庭經營性收入偏低的農戶進城務工,雖然提高了工資性收入,但是卻擴大了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
3.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
進行多次擬合后受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影響的最優模型(見表3)。
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都是顯著的。泰爾指數和總收入的基尼系數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之間是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其對稱軸分別為0.96和0.92,2010年農村固定投資為0.94百億元,2011年為1.06百億元,說明在2011年之前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額度越大,反而會擴大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但是當投資規模達到一定額度以后,將逐步縮小農民收入的內部差距。工資性收入差距、家庭經營性收入與農村固定投資之間都是負相關關系,隨著農村固定投資額度的增大,工資性收入差距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將縮小,且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縮小的幅度大于工資性收入差距,這說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增加固定資產的建設將有利于縮小農民的收入差距。
4.其他因素的影響
進行多次擬合后的最優模型為:
JGN=1.48-1.48D1-3.22GYH+4.5GYH*D1,R2=0.941,
PF-statisitic=0.01
(0.01) (0.03) (0.02)
重慶農村工業化水平GYH對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顯著的,對其他收入差距的線性或二項式非線性關系均不顯著。在2008年之后,工業化水平對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正向的,即隨著農村工業化水平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越大。這里的農村工業化水平選取的是鄉鎮企業勞動力占農村總勞動力的比例,被鄉鎮企業吸收的農村勞動力的家庭經營性收入是減少的,但是鄉鎮企業吸收勞動力的增加并不會擴大其他收入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重慶農產品價格指數API對所有農民收入差距的線性或二項式非線性關系影響均不顯著,在研究時期內農產品價格指數的波動呈現”W”型,與收入差距之間的統計關系不明顯。這也說明現行統計數據中的農產品價格指數并不能完全反映農民的主要收入變化。
結論
本文對重慶市農民收入內部差距進行了研究,不同收入層次和不同收入來源的內部差距是穩中有升,在工資性收入差距逐年縮小、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差距變動幅度小且趨勢不明的情況下,其主要因素是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擴大。盡管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差距不大,但是其收入絕對數也很小,引導并支持農民增加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將有利于農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總量和農村固定投資額度的提升,將有助于縮小農民內部收入差距,但是現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和農村工業化將擴大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進而導致農民內部差距的擴大。所以,在推進城鎮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應當加強醫療、教育、就業等公共服務,妥善安置失去或減少了家庭經營性收入來源的農民群體;通過技術引進、政策鼓勵等措施引導農民開展多樣化家庭經營,縮小家庭經營性收入;通過發展第三產業、保障農民工工資等方面促使農民工資性收入差距的縮小。結合村外保障安置和村內鼓勵引導等措施以縮小農民內部收入差距,保障農民的可持續收入,實現城鎮化工業化的科學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唐平.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及影響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6,(5):69-75.
[2] 葉彩霞,施國慶,陳紹軍.地區差異對農民收入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2010,(10):103-107.
[3] 王少平,歐陽志剛.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對經濟增長的效應[J].經濟研究,2007,(10):44-55.
[4] 李娜,李利,郭艷平.中國行業工資差距:基于泰爾指數的分解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3,(7):93-96.
[5] 萬廣華.中國農村區域間居民收入差異及其變化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1998,(5):36-49.
[6] 孫慧鈞.中國農村區域間收入差距構成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07,(11):42-47.
[7] 盧方元,魯敏.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J].數理統計與管理,2009,(1):122-129.
[8] 李政.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民收入層次差距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4,(2):19-20.
[9] 黃祖輝,王敏,宋瑜.農民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研究—基于村莊微觀角度的一個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05,(3):75-87.
[10] 黃應繪.重慶農民收入差距的分析[J].經濟問題,2007,(1):85-86.
[11] 萬廣華.不平等的度量與分解[J].經濟學(季刊),2008,(1):347-368.
[12] 徐增海.中國農民工資收入波動及其環境因素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6):186-192.
[13] 高連水.什么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地區收入差距水平?[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1):130-139.
[14] 潘文軒.城市化與工業化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12):20-29.
[責任編輯 王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