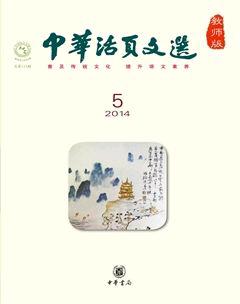借助意象解讀,探秘心中之景
方妤
我國傳統的散文學者認為,“散文結構應講究起、承、轉、合,應有一種嚴謹的結構美”,講究“在有限中求無限,在統一中求變化,在人工中求自然”的江南園林式的注重外在謀篇布局的散文結構。這種傳統的散文結構使散文寫作陷入了程式化和單一化的境地,往往是開頭一段景,中間一件(或幾件)事,接著以事喻人,最后抒情,升華哲理。出人意料的是,作為中國現代作家的錢鐘書,卻摒棄了固有的散文創作模式,他的散文結構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結構的謀篇布局。他試圖把散文從老套子中解放出來,甚至借鑒了小說創作中的一些表現手法,運用想象、象征、聯想等手段,憑借敏銳的藝術感覺,營建了散文新結構,創造著散文的表現形式。《窗》就是這樣的一篇文章,在錢老筆下顯得開闊、隨意、自由、流動,又不乏意義的象征。
這種意義的象征在《窗》里是通過意象的表達來完成的。意象作為情感抒發的一種重要手段和載體,并不僅局限于詩歌。以表情感懷為主的散文同樣可以擁有意象技巧,用以加強文體的抒情色彩,表達某種言外之意,并構成推動散文意蘊的深層動力。在《窗》中主要有“門”和“窗”兩個意象,通過對這兩個帶有象征性的意象的解讀,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作者在選擇自然意象構筑心中之景,表達了內心想法與現實場景的對立之感。
首先,我們來看“門”。錢老在文中寫道:“門是造了讓人出進的”,但“門的開關是由不得你了”。這是否可以看成是門的虛設和與己無關呢?因為“屋子本是人造了為躲避自然的脅害”,而“門”正好是可以借以阻擋外界所有的誘惑與災難的,可現在的門居然成了擺設,因為門外的不可預知,決定了門的空洞與無奈,也決定了人的焦慮與荒誕。
加繆曾詳細地闡釋過焦慮的發生,他說海德格爾冷靜地觀察了人類命運并宣告這種存在是卑微低下的,而唯一的實在就是在生物進化系統中的“煩”;對于被拋到世界上的人以及他的歡樂來說,這“煩”是一種短暫而難以捉摸的畏懼,但當這種畏懼覺悟到自身時,它就變為焦慮。也就是說,門相對于作者來說,是一種有形的焦慮的存在。因為“門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主的”,“有人敲門,你總得去開”,無論是愿意的還是不愿意的。這就滋生了人們對于門的存在的一種焦慮,甚至害怕,正如文中所說的,“你愈不知道,怕去開,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開”,甚至“使你起了帶疑懼的希冀”。
這里,我們發現了錢老筆下的“門”其實是帶有兩重性的。一方面,門是隔絕污濁的,可以拒絕所有的不祥;但另一方面,門卻是無力的,它無法預測門外的世界,也阻擋不了門外的世界,當有人敲門時,人們無法知道門外世界的真相,只有開門迎接,增加必要或不必要的焦慮。美國的存在主義者保羅·約納內斯·蒂利希認為,人的基本生存狀態是“焦慮”:對命運和死的焦慮,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對罪惡和譴責的焦慮……沒有人能逃脫這種焦慮,正如文中所指出的,“門許我們追求,表示欲望”。欲望的無限導致了焦慮的產生,焦慮的產生又和門息息相關。這也正如錢老對人性的認識,人們可以有欲望,但欲望的無法遏制,就如同門外的無法預知。
其次是窗。如果把門看成是通向不可預知的外面世界,那么窗似乎就是可以把握的內心世界。如果門是有形存在的人性焦慮的根源,那么窗似乎就是反抗這種焦慮的最好承載形式。
王光東認為:“人類在其生存的歷史過程中,要經受三種苦難的困擾,這就是人與自身的沖突、人與自然的沖突及人與現實的沖突所形成的無法逃脫的生存環境的折磨。當然,在這三種矛盾沖突中人類也總是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消解這種沖突的劇烈程度,通過種種方式來尋求和諧,達到情感與理性、生存與死亡、自我與現實的平衡和完滿。”而錢老就是用了“窗”的方式去尋求和諧,達到完滿。
他首先就給予了“窗”充分的肯定:“窗比門代表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段。”接著他舉例說明其中的理由,“窗子可以收入光明和空氣,使我們白天不必到戶外去,關了門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義”;“門的開關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來,只要把窗幕拉過一邊,就知道窗外有什么東西在招呼著你……窗子算得奢侈品”;“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許里面的人看出去,同時也許外面的人看進來”。所以最后錢老給了窗一個高度的總結:“假使窗外的人聲物態太嘈雜了,關了窗好讓靈魂自由地去探勝。”
對于錢老的世界來說,他的內心具有一種絕對的豐盈和充實,一種難以表達的優雅和從容,但這些東西總是被一個現實的世界無情地騷擾,他不得不進入一個“他者”的世界而面臨巨大的困擾。于是,他一方面極力避免敞開,以一種逃避的姿態——“門”的形式,將自己關在狹小的空間范圍內;另一方面卻企望逃離那狹小的空間,享受陽光的明媚,春天的動人,于是“黑夜給了他一扇不由人做主的門,他卻用窗來尋找光明”。這或許也就是錢老營造的兩個意象所傳達的心中隱秘吧。
參考資料:
1.曹國瑞《情有所鐘──散文奧秘的探尋》,光明日報出版社。
2.佘樹森《散文創作藝術》,北京大學出版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