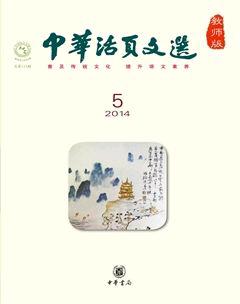聶紺弩五章
劉再復
初祭聶紺弩
聶老安詳地吃完最后一顆橘子,過了兩個小時,就靜靜地長眠了。沒有一點聲響,沒有一句遺言,沒有一點死的征兆,就這樣,他和我們永別了。
這位人生像一篇屈原《橘頌》的高潔詩人,正直秉性不可轉移的戰士,我心靈的導師,逝世之后,給我留下永遠的感傷。但是,看到他這樣靜悄悄、沒有痛苦地遠走,在悲哀中又感到欣慰。他實在太累了,一生除了革命、打仗、辦報、坐牢、勞動改造之外,還寫了二十七本文學集子。近幾年來,已經精疲力竭,但還在思索,還在掙扎,還在咀嚼自己的心。他已經消瘦到沒有一點肌肉,腿和胳膊幾乎一樣細,犯了哮喘病甚至連氣也抽不出,只有揪心的干咳嗽。不能翻身,一翻身就會感到刺骨的疼痛。可是他偏不屈服,咳嗽時還是顫巍巍地讀著,想著,有時還拿起筆寫幾個字,筆拿不住,最后,連那么輕的一支香煙也拿不住了。我知道他的心事是怎樣廣闊浩茫,心靈深處是怎樣活潑、豐富、奇特,但是看到他拿著顫抖的紙筆,只覺得他在服著精神的苦役,實在受不了。每每看到他這個樣子,就想起他懷念邵荃麟的詩句:“君身瘦骨奇嶙峋,支撐天地顫巍巍。”我知道科學世界和藝術世界正是像他這樣一些不幸又不屈的人所支撐的,然而,我實在受不了他那種拿著筆的“顫巍巍”的樣子。他的生命已被吸干了,數十年中被征途與牢房吸盡了大部分,近十年來又被詩歌與文章全吸干了。他該休息一下了,不應當再繼續飲啜人生的苦汁了。此時,我提起筆,一串眼淚灑落在紙上,我竟分不清這眼淚是苦味還是比苦味還要苦的生命意味。
真不愿意多想他的過去,脆弱的心靈很難承受他的太沉重的人生。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后,他被判入另冊。一九五八年初,他被劃為“右派”,送往北大荒勞改;“文革”中他因不滿林彪、江青而以“現行反革命”之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被宣判無罪。他是個不幸者,但又是一個征服不幸的剛強者。任何艱難的命運都無法把他擊倒,他也從來沒有因命運的兇險而放棄真理。在鐵窗下,他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繼續學習與思索,把《資本論》細細地讀了四遍,并在書頁上貼了幾千張寫著要點和心得的小字條,此書現在就在我的手里。他告訴我,他讀懂一句,就在底下畫一道紅杠杠,最后,他把全書都畫滿了紅杠杠。今天,再看看這書,只覺得這些紅杠杠里注滿了他的血痕與傷痕,也注滿他博大的思想與心靈。撫摸這血痕與思想,真像觸到一團團火。這位《資本論》的偉大讀者,正是在煉獄的火焰中戰勝了魔鬼和死神的威脅,使自己不屈的靈魂獲得了空前的升華。
晚年他發表的古典小說研究論文和《散宜生詩》,固然可看到他的眼淚,但也可聽到一種帶著樂天氣息的笑聲,我想,這正是他經受了苦難之后,進而穿越了苦難感悟到人生真理的一種愉快,也正是他洞察了社會人生真相之后反而自由地駕馭人生的一種自豪感。晚年,他正是用這種心境從事寫作,寫出一篇篇令人驚嘆的、具有真情真性真品格真境界的文章。
他用錚錚硬骨支撐著艱辛的歲月和超越了自身的痛苦,卻無法超越另一種痛苦,這就是他人的痛苦。他在自己受到折磨的時候,卻總是想著別人。去年十一月,他病得很重,提起筆就顫抖,但還是寫了一篇懷念馮雪峰的詩,其中有“識知這個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這是他的絕筆。這絕筆正透露出他的心靈與人間的憂愁如何相通。他晚年對我們祖國的改革表現出一種感人肺腑的關切,他深深感到此時中華民族所選擇的歷史方向是對的。對于聶老重重的心事,我曾有不少感悟,待以后情緒平靜下來,再慢慢體味和細說。此時我陷入送別這位太陽般的長者與親者的悲傷里,只愿他辛苦一生的靈魂,能在地母懷中得到安息。
寫于一九八六年三月
最后一縷絲
聶紺弩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去世。他生前以深摯的愛和深邃的思想,在我身上注入了他的一部分靈魂。每次想到他的名字,我就在心中增添一些潔凈的陽光和抹掉一些無價值的陰影。
聶老作為一個杰出的左翼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還經歷了那么沉重的痛苦和艱險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他有奇才,但才能既是他的成功之源,也是他的痛苦之源。他既不懂得掩蓋才能的鋒芒,也不懂得掩蓋良知的鋒芒。每次政治運動,他都要說真話,真話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它是通往真理的起點。愛講真話,這就決定他要吃虧,反“胡風”時,他當了“胡風分子”;反“右派”時,他當了“右派分子”;反“走資派”時,他又因為說了輕蔑江青的話而當了“現行反革命分子”,最后這一次非同小可,被判了無期徒刑,送進監獄。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釋放回北京。
我和聶老真是有緣。他出獄后不久,我們便成了近鄰,同住在北京市的勁松區。十年之間,我們成了忘年之交。我數不清到過他家多少回,不過,每一次見到的幾乎都是同一種情景:他靠在小床背上,手里拿著夾紙板和筆,想著寫著。我一到那里,就悄悄地坐在他的小床對面的另一張小床上,呆呆地看著他想著寫著,等著他放下筆轉過頭來和我說話。聽他說話的時刻,是我最快樂的時刻。
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都是如此。只是慢慢覺得他的露出被單的雙腳愈來愈細,最后細得和他的手臂一樣,只剩下皮和骨,絕對沒有肉。
屋里是絕對的安靜,他的心跳也是絕對的平靜。人世間的一切苦楚都品嘗過了,和死神也打了幾回交道,此時,死神對他已無可奈何,他對死神也滿不在乎了,至于別的:貧窮、榮譽、名號、財富、反自由化,那就更不在乎了。然而,他還在乎一點,就是寫作。天天寫,絕不浪費一分一秒幸存的生命。他的身體已被摧殘得沒有多少氣力了,但他還是用殘存的氣力去提起那一支圓珠筆。他贈給我的詩說:“彩云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堅。”他相信一切都會消失,唯有藝術是永存的。對于被迫害,對于坐牢,他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失去了許多時間,少寫了很多文字。我相信,只要有紙和筆,他坐一輩子牢也會滿不在乎的。
他的雙腳不能動了,自然到不了圖書館,因此,也只能利用家里有限的藏書,把精力放在古代幾部長篇小說的研究上。他自嘲說:“自笑余生吃遺產,聊齋水滸又紅樓。,他沒想到自己在七十三四歲之后,還有“吃遺產”的幸運,他真是傾心、迷醉于“遺產”。從最痛苦的地獄黑暗中走出來,能贏得一個機會,靠在小床上,欣賞自己心愛的藝術,感悟祖先的智慧與天才,這不正是天堂嗎?昨天夢中的天堂不就是眼下這張小床和這些文字嗎?
一九八五年夏天,他處于病危之中,發燒,昏迷,發脾氣,我一見到這情景就非常著急: “為什么還不送醫院?”他的夫人周穎老太太說:“他就是不肯走,早晨好幾位朋友要他上擔架,他卻用手死死地抓住小床,就是不肯走。他就是這么犟。”我們只好干著急,不知道怎么辦。他的夫人和朋友都走出屋了,我還站著呆看著。突然,他張開眼睛對我說:“只要讓我把《賈寶玉論》這篇文章寫出來,你們要把我送到哪里都可以,怎么處置都行,送到閻王殿也可以。”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我知道這是他最后的牽掛,至死都放不下的牽掛就是賈寶玉。
他的最后的生命脈搏全被《紅樓夢》抓住。他的紅樓思考疑聚著他對宇宙人生和文學藝術的全部見解。這是他最后最真實的心愿。就像一只蠶,他必須吐出最后的也是最美麗的一縷絲,才心甘情愿死去。只要最后一縷絲能吐出來,他就可以死而瞑目,這個九死一生的詩人,其人生的最后希望已變得非常具體,具體到吐出一條可以稱為“賈寶玉論”的絲。
聶老去世之后,我常常想起他最后的心愿和最后的遺憾,想到他抓住床架不肯離開這個世界僅僅為了吐出最后一縷絲,真有無限的感觸。這是他對我最后的教導,最后的呼喚。想到這里,我就更懂得珍惜,懂得該珍惜那些最該珍惜的東西。同時,我也不能不感慨,人與人的差別實在太大了,那么多人最后眷戀的,是金錢、地位或者一頂桂冠。他們也像聶老抓住床沿一樣緊緊地抓住自己的桂冠,然而,這是多么不同的眷戀呵。
聶老臨終前,留給我許多非常寶貴的東西,包括他在監牢里讀過的《資本論》和書中的數千張小批條,還有九箱的線裝書。但是,朋友們不一定知道,他還留給我這一價值無量的最后的一縷絲。
(選自《漂流手記》)
思想錐心坦白難
在聶紺弩生前,我請他為我書寫兩句詩以作為人生座右銘,他想了想,便鋪開紙張,提起毛筆,寫下“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因為從心里敬愛他,所以我真的一直把它作為座右銘。漂流海外后,時刻把它帶在身邊。現在又把它掛在書房的墻壁上,像一盞燈火,時時在我身邊發著光明。
聶老臨終前不久把他的一小本詩稿手跡和兩本已出版的詩集送給我。因為常常翻閱,才發現這兩句詩早已在他心中釀成,然后再移植于完整的詩中,也因此,這一對聯竟兩次在詩中出現,這是聶詩中所沒有過的,一次是在《三草》 (香港野草出版社)的《歸途二首》中,全詩為:“雪擁云封山海關,宵來夜去不教看。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一夕樽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爛柯山。偶拋詩句凌風舞,夜半車窗旅夢寒。”這首詩是放在《北大荒》輯的最末,應是作于一九六六年,但聶老的好友高旅先生在為《三草》所作的“小序”中說: “或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系六六年劫后被囚時作。非。一九六二年曾讀之,列一組雜詩中。”可見,這兩句詩在寫《歸途二首》之前就出現過。然而,有意思的是聶老在八十年代又把這兩句詩放入給馮雪峰的挽詩中。詩日:“狂熱浩歌中中寒,復于天上見深淵。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一夕樽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爛柯山。從今不買筒筒菜,免憶朝歌老比干。”此詩收入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散宜生詩》。大約聶老覺得馮雪峰才配得到這一對聯,所以便在他逝世時七為挽聯為他送行。這又可見聶老真把這兩句詩視為生命的晶體,只能獻給純正的靈魂。
查了聶老的詩稿手跡,又發現他給馮雪峰的這首挽歌最后兩句原是“孟嘗門有三千客,長鋏懸空孰再彈”,發表時改成另一樣,大約是覺得把馮雪峰比作養士三千的孟嘗君,還不如比作剖心自白的比干。這一比喻和“文章錐心坦白難”一句相連,寓意更深。這些苦心琢磨,可以看出聶老也把這兩句詩視為自己的座右銘。而這座右銘也只有經受許多苦難之后才能產生,它屬于生命深層脈管里流出來的血。
深深了解文章坦白之難有如比干剖心,可能只有中國作家。聶紺弩自己因為襟懷坦白而被拋入牢獄,而他的朋友胡風的上書,其實也只是坦白直言,然而,他的報償是“三十萬言三十年”,坦白地道出自己對文學藝術的看法,結果是坐牢三十年。一個人要承受三十年的地獄生活是不容易的,特別是要承受入獄的理由僅僅是“坦白直言”更不容易。而著名的“三家村”冤案,其實也只是在雜文中坦白地說了一些真話。鄧拓身為《人民日報》總編輯、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坦白地批評一下“偉大的空話”,就遭到滅頂之災,更何況別人。我有次談起鄧拓時,一位朋友說:鄧拓算什么,彭德懷是戰功赫赫的大元帥,三軍總司令,他在上書中坦白地說點真話都不行,還容得了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說話嗎?在千百萬人餓死溝壑時一個開國元勛都難以直言,那么,真實地描述社會人生的文章該從何做起呢?縱有天才又有何用呢?文章原來難的不是文采,不是技巧,不是知識的萬花筒,而是直面慘淡的人生與淋漓的鮮血,是像錐子錐著自己的心靈然后坦白地面對人間的強權與黑暗喊出真實的聲音,這聲音,不是肉聲,而是心聲;不是詞章包裹著的唇齒,而是負載著人間苦痛的坦蕩胸懷。這一點,西方的評論家很難了解,他們永遠不能理解中國作家踩著鐵蒺藜前行時的心情,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為什么總是要在自己的肩上挑起被純文學作家所瞧不起的道義重擔。
(選自《西尋故鄉》)
聶紺弩山脈
因為聶紺弩這一名字已成為我靈魂的一部分,所以我常常想起他。說人死丁之后可以永遠活在人心中,過去以為是愿望,今天才知道這是現實。聶紺弩的名字,絕對活在我的心里,活得很具體,具體得像一盞燈光,一顆寶石,一朵雪蓮,一座大地上的山峰,伸手就可觸摸得到。對于這座山,近看厚重,遠看也厚重。
在精神山脈的登臨中,我常想到許多峰巒的名字,例如荷馬峰、但丁峰、莎士比亞峰。這些名字是人類共同的。而聶紺弩山脈,則屬于我,當然也屬于愛他的中國讀者與朋友。那些常常凝望聶紺弩山脈的旅行者,一定是我的兄弟。
我見過許多年邁的作家和學者,看過他們或站立著,或踉蹌蹣跚地走著,唯有聶紺弩,我只看見他平實地坐著,總是靠在床頭坐著,坐在那里,手中拿著筆。時間停滯,空間濃縮為筆下的夾紙板。大約有七八年,我沒有看到他走動過。聶紺弩山脈永遠是坐落著的,和大自然的山脈一樣。
每次見到他坐著寫作的時候,我就感到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很大,它迫使我也坐下來,老老實實地讀、寫、思考,不敢亂走亂動,不敢丟失任何一個早晨與黃昏。因為聶紺弩,我才悟到:坐著就是力量。
經歷二三十年的精神摧殘和監獄生活之后,聶紺弩本來應當好好休息以享受人生最后的時節,至少可以躺著看看閑書,不必再那么勞累了。然而,他偏選擇了勞累,確確實實的勞累,別人坐著不算什么,而他坐著卻不容易。他的體力在監獄里幾乎耗盡了,現在支撐他坐著的是完全沒有彈性的骨架,是沒有被剝奪掉的生命最深層的意志。意志的力量真是驚人。看不見的很抽象的意志,真可以變成一種非常具體的挺立的大山。聶紺弩就是這種山峰。他憑著不死的意志,就整天在那床頭坐著不動,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十年歲月,就在那個角落里,就在那個空間濃縮的紙板上,寫出了上百萬字精彩的詩歌、散文、回憶錄和論文,像巖隙里的泉水奔涌,像山谷里的鮮花盛開。在他那個座位的墻外,數不清的讀者為他的才能而感動而嘆息而坐立不安,但他一概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在乎。贊揚與詛咒對他都無所謂,他只是坐著,只是寫著,除了面對自己的良心之外,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與朋友談論起聶老面壁十年的寫作故事時,大家總是驚嘆。但我總是不滿意朋友們的解釋,他們說,聶老是受壓迫之后的奮發,是為了爭一口氣。我感受不到聶紺駑在爭氣,只感到他的心氣格外平和從容,沒有憤怒,沒有浮躁,只有山脈似的靜穆。天崩地裂過了,留下的是永恒的太始之初。一切都重新凝聚于筆尖,凝聚于他的開山之斧。他知道,情緒是沒有價值的,重要的是把以生命的痛苦代價換來的體驗一筆一筆寫下來。對聶紺弩我作出不同于朋友的“唯心論”解釋:他的生命就是特殊,當人們在嚴酷環境中生命秩序發生混亂的時候,他并不混亂;當人們把自己的靈魂切成碎片爭先奉獻而贏得茍活的時候,他偏偏為了保持靈魂的完整而讓肉體受盡摧殘。他坐著的力量首先不是表現在小床上,而是在監獄的鐵窗下。在死亡的角落里,他始終直面死神坐著,也像山峰,巍巍直沖天穹。十幾年中從未有過哀叫、求饒和哭泣。伴著鐵一樣冰冷的四壁和若有若無的明天,他終于把牢底坐穿,終于戰勝命運最嚴峻的打擊,重新贏得寫作的權利。當他贏得這一權利之后,就比誰都更懂得珍惜,也比誰都知道坐下來把握這一權利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在他的晚年,表現出比“把牢底坐穿”更大的力量,坐到肌肉全部消失,坐到心血全被吸干了,坐到從骨髓里吐出最后一個字。
當我遠離故土,也遠離聶老生前那座樓房的時候,我總是想起他的小屋和小屋里的那張小木床,他的那二塊夾紙板和那一支圓珠筆,還有那座思想者山脈。一想起它,就聽到它的召喚:坐下來,坐下來就是力量。當我身心俱倦的時候,一聽到這種召喚,就會回到書桌前,拿起筆。在人們競相沉淪的歲月里,我所以還一篇一篇地寫著,其實與這遠山的呼喚有關。
我的遠山,我常常登臨的聶紺弩山脈,你將永遠坐落在中國的大地和我心中的大地。
(選自《西尋故鄉》)
背著曹雪芹與聶紺弩浪跡天涯
三四年來浪跡四方,在東西大陸里來回往返,逼迫我必須輕裝前行,把喜愛的書籍留在原處。書籍實在太重,一部《史記》就比一件大皮襖還重。可是,此次我要去的地方是瑞典,名副其實的雪國,書固然重要,皮襖也很重要。
誰陪我去浪跡天涯呢?從孔夫子到王國維,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從屈原到馬奎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撿起,和妻子、女兒爭奪幾個箱子的地盤。妻子重視的是形而下,民以食為天,以穿為地,書本再重要,也得先求生存。而我崇尚形而上,以文字為天為地,于是,總是爭吵,朱熹、尼采就被她從皮箱里驅逐過好幾回。沒有爭論的只有那些我愛女兒也愛的詩集,屈原、李白、李煜、蘇東坡等,在皮箱里,總有他們的位置。
明知前去的學校圖書館很容易找到,但還是一定要他們陪我漂泊的古人是司馬遷和曹雪芹。《紅樓夢》中的那一群天真而干凈的少男少女是我朝夕相處的朋友,生活在社會的爛泥中是需要一群干凈的朋友的。大觀園里的少男少女,無論是林黛玉、薛寶釵,還是賈寶玉,我都喜歡。我真恨那些把他們劃分為不同階級的紅學家,厭惡他們給這些充滿天真天籟的人類花朵戴上骯臟的政治帽子,這比“佛頭點糞”還讓我難受。不會戴帽子的俞平伯先生還挨了他們一陣亂棍。可是,這些棍子們很快就會化為塵芥,而我喜歡的詩意生命,卻在世界八方的精神土地里笑著、鬧著、相思著。
除了《紅樓夢》,還愿意背著《史記》。當朋友把《史記》從大陸寄到芝加哥時,我高興了好久。我真喜歡這部又是歷史又是文學的奇書,而且喜歡司馬遷的精神,在嚴酷的命運面前絕不屈服的精神。一部龐大而殘暴的政治機器,只能閹割肉體,卻無法閹割掉人的精神與天才。
現代作家中我所敬愛的聶紺弩,也是一個司馬遷似的任何力量都無法閹割其精神的人。無論是惡鬼似的罪名,還是山岳一樣沉重的監獄,都不能壓彎他那一支正直的筆桿。比罪名和監獄更沉重的打擊,是他唯一的女兒在難以忍受的牽連中自殺了。他的夫人周穎老太太告訴我,他出獄后唯一的心思就是想見女兒,怎么向他交代呢?然而,最后還是告訴了他。這一致命的消息本來足以使他喪失理智,可是,他卻支撐住命運最殘酷的打擊,把本該滴落的眼淚吞咽下去,注入筆桿,繼續寫作。他知道,唯有吐出積壓了幾十年的正直之聲,才能告慰一切自己的所愛和一切受難的靈魂。我不管走到哪一個天涯海角,都背著他的書和他的一些珍貴的手跡。這些書與手跡,支撐著我的脊梁,幫助我度過艱難與心事浩茫的歲月。四年過去了,我沒有一天忘記他的名字。因為他的名字,我一天也不敢偷懶,更不敢說一句背叛人類良知的話。
自然,我還得背其他書,俄羅斯的《卡拉瑪佐夫兄弟》,美利堅的《熊》與《白鯨》,故國的龔自珍、嚴復、梁啟超、魯迅等思想者,雖沉重,但已背著他們跨越多次的天空與海洋了。還有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等,也和我一起辛苦輾轉了好幾片蒼茫的大地。但是妻子從來不驅逐他們,皮箱里總有他們的地盤。這回遠行,我把故國的這些學者的書和康德、福柯們的書放在一起,奔赴地球北角的雪原,結果行李超了重,被罰了一百多美元。
一被罰,就想到被罰的日子何時終了,真想有一天能結束漂泊生活,可以面對四壁的藏書,在一張平靜的書桌前和古人今人從容對話,既領悟人類的卓越,也領悟說不盡的大荒謬。
(選自《遠游歲月》)
(選自《師友紀事》,有刪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