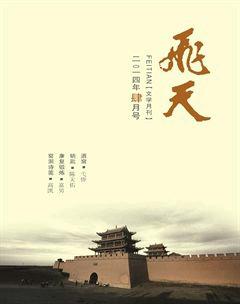輪回的“生死場”
左晨帆
魯迅在為蕭紅的《生死場》作的序中,稱它是“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jiān)強(qiáng),對于死的掙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而馬步升在為趙旭峰的小說《龍羊婚》(甘肅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所作的序言中,稱將其“展現(xiàn)了叢林法則下的人性法則。”無論是戰(zhàn)火連月的哈爾濱近郊的偏僻村莊還是西北邊陲與世隔絕的雙龍溝蛤蟆鎮(zhèn);無論是解放戰(zhàn)爭中對抗外敵入侵和地主壓迫還是解放后對抗貧窮和饑餓;無論是以女性的掙扎作為敘事中心還是用男性的抗?fàn)幦ゴ蚱苽鹘y(tǒng),一個(gè)多世紀(jì)以來的中國鄉(xiāng)村,無不在往復(fù)輪回著“生死場”。蕭紅在《生死場》中這樣寫道:“在鄉(xiāng)村,人和動(dòng)物一樣,忙著生,忙著死。”這種表面上充實(shí)的“忙碌”,被鄉(xiāng)俗禮儀死死地固定了下來,也將一代代的莊稼漢和他們的妻兒拴在了那充斥著塵土腥膻的鄉(xiāng)村中。
作為甘肅天梯山石窟管理員的趙旭峰,迥異于一般身處鬧市的作者,也正是因?yàn)榄h(huán)境的單純,培養(yǎng)出了他小說、詩歌、書法等多方面的愛好;可僅把這些論為愛好又有些不當(dāng),趙旭峰做一事愛一事,更是做得有鼻子有眼。《龍羊婚》蘊(yùn)蓄著作者對文學(xué)和人生的執(zhí)著和熱愛。
一、行走在“生死場”中的那些人
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可以說是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女性敘事的巔峰之作。在眾多的女性角色中,《呼蘭河傳》中的小團(tuán)圓媳婦和《生死場》中的月英雖然并不是貫穿始末的焦點(diǎn)人物,但也許是眾多讀者掩卷沉思后最為憐惜的兩個(gè)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