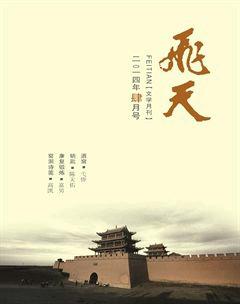外婆的家(外一題)
2014-05-06 20:54:10王世江
飛天
2014年4期
王世江
十月一,送寒衣。轉眼間,已是外婆去世百天的日子。裊裊的紙錢的味道,把我的思念帶到了故鄉。
外婆家和我家隔一條小河。小時候,外婆疼的并不是我。也許在媽媽的姊妹們中間,媽媽也不是外婆喜歡的類型。外婆不追星,外婆是一位純樸的母親,誰是弱者外婆就喜歡誰。我小時候喜歡吃蔥(呵,到現在這毛病也改不了)。每當我牽著耕牛犁地的時候,只要外婆能看得見,外婆準能包著一頭巾的小蔥,顫顫微微的立在我的耕牛前面,示意我——是該緩干糧的時候了。當時的我,能把外婆一頭巾的小蔥吃得干干凈凈,直吃得我嘴里木木的,好幾天償不到漿水的酸味。
本來外婆跟小舅住在一起,這也是我們農村老家的“國際慣例”,也是外婆疼弱者的具體表現。再者說了,外婆自從嫁到這里來,就一直生活在這個院子里。前幾年,小舅領著一家人進城打工去了。這就有了問題了,外婆沒家了。不過,外婆還有個大兒子——就是我的大舅。外婆搬家了,搬到了我大舅家。我想著也一樣,都是兒子嘛,在哪兒還不就是吃個飯睡個覺。
熟料,外婆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真可謂時時處處在想著我小舅家的事。可惜的是,外婆的所想所盼,我小舅可能全然不知,也許還有點煩。有一年,外婆八十幾壽辰(我也記不清了),外婆領著我媽媽姊妹們到了我小舅家——其實是我外婆心中的家。媽媽姊妹們驚奇地發現,小舅家的莊院里多了一大堆柴禾。外婆說,那是她每天在路上撿的廢枝枯條,想著小舅回家時,有了生火做飯和喝茶的基本燃料。……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