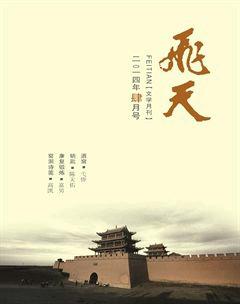窯洞詩箋
2014-05-06 20:48:55高凱
飛天
2014年4期
高凱
一
我出生于窯洞。
我的詩歌也發掘于窯洞。
雖早已不在窯洞里居住,但靈魂里我始終是一個窯洞的兒子。
窯洞的背影已經模糊。在大多數人還住在窯洞的時候,在我的故鄉隴東,每每走近一個黃土塬,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那一孔孔勾人魂魄的黑窯洞。我的長詩《舅舅家的路》,寫千辛萬苦去舅舅的家,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最后才看見“坡底兩孔坐北朝南黑眼窩般的窯洞/就是舅舅的家”。舅舅的家其實就是母親的娘家,是我生命的遠方,那幾孔黑眼窩般的窯洞,曾讓我不止一次長久駐足凝視。而近處見到的窯洞,則如我的《鄰家》一詩中寫的這樣親和:“和神仙作伴/都沒有和人作伴/心里踏實//土窯洞 一個個/肩挨著肩/一年到頭/都取著暖暖/做飯的煙走上天去/也能擰成一股”。這哪里是在寫窯洞呀,我是在寫窯洞里的人!
窯洞就像故土的肚臍眼兒,而鄉情就像剪不斷的臍帶。命苦的母親早已去世,但她一直活在我的詩歌里。窯洞是母親生兒育女的窩兒,但也是母親生命的墳墓。在《屋里人》中我這樣寫母親這樣的女人:“女人呵 亮閃閃的一盞燈/白天和夜晚/都掌在深深的黑窯里/一個低低的門檻/遮暗了女人的一生”。在《出生地》一詩中我又這樣寫母親:“像一盞燈 照亮閆家洼村的一孔窯洞/于1963年農歷二月二的后半夜/將我從她苦難的身體里放生”。窯洞見證生活的艱辛,詩歌述說人生的苦難。這首詩里的“放生”一詞,十分凝重,得來猶如神示,從我的心里蹦出來后,連我自己也吃了一驚!……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