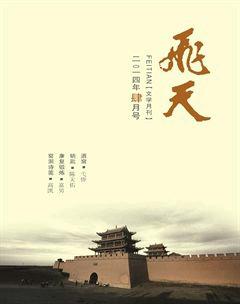酒窩
2014-05-06 20:30:13弋鏵
飛天
2014年4期
弋鏵,女,現居深圳市,深圳作協會員。2004年開始發表小說,已發表作品八十多萬字,獲首屆魯彥周文學獎、首屆廣東省小說獎、第七屆深圳青年文學獎、首屆全國青年產業工人文學大獎、第三屆原創網絡文學拉力賽獎等。作品散見于《當代》《花城》《天涯》《上海文學》《飛天》《世界日報》等報刊,部分作品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小說精選》《短篇小說選刊》《作家天地》等雜志選載。
1
父親的墳用土慢慢地封了。幾個幫忙的人用鐵鏟狠狠地夯實了松軟的土塊,使得新墳隆成了一丘尖尖實實的土包。一個年紀略輕一點的后生還用鏟尖慢慢削平了突出來的一點黃色的泥土,很細致地打圍了一圈。然后大家就都接了萬根水遞過去的煙,吸起來。把對襟的褂子打開,里面的汗,嘀里噠啦地沿著黝黑或赭黃的肌膚、順著根根數得出來的肋骨,已經像小溪一樣地流淌著了。
巧云拔幾棵新草,小心地點綴在新起的墳包上。然后曲了膝,跪在地上,朝著父親的地方,連磕了九個頭。
不是特別悲傷。自打母親早早地死后,父親對她就沒慈眉善目過,后來又娶了劉寡婦。后來的日子,人家都知道巧云是怎么活下來的了。可是,人老沒土的時候,還是得巧云給他披麻戴孝,還是得埋在巧云的娘旁。劉寡婦拖帶來的三個孩子,只遠遠地在屋外草棚里住著,連靈都不能守的。劉寡婦也哭了幾場,但是,生的時候能相守十幾年,死的時候,卻也只能各和各的那位頭親埋一處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