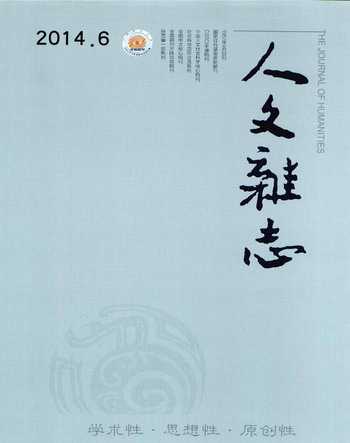晚明高僧《四書》詮釋文獻考察
樊沁永
內容提要晚明儒佛會通是中華文化整合的又一次高峰,而在這個宏大的文化思潮中,高僧群體解釋儒家典籍《四書》文本尤為引人注目。《四書》經由朱熹章句集注之后,升格為儒家新興經典,通過精英講學、科舉選拔、民間教學等方式普及甚廣。但由于朱熹嚴格批判佛老的思想,也使得佛教遭遇了理論上的挑戰。時至晚明,學風敗壞,儒佛兩家均受到重大影響。佛教在重建良好宗風的過程中也主動融攝儒家思想,在《四書》文本上有多樣化的詮解,為傳統儒家四書學打開了一個新的面向,體現了佛解《四書》的共同特點。本文對晚明佛教解釋《四書》的文獻進行全面考察,通過詮釋體例分類及宗趣分析,初步介紹這一學界尚未全面且充分關注的領域。
關鍵詞晚明佛教《四書》儒佛會通
〔中圖分類號〕B24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6-0013-07
晚明高僧詮釋儒家《四書》典籍有著豐富的內容和角度,但是歷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較大的晚明四大高僧的相關著作,且主要以文本的哲學研究來檢視儒佛會通的效果,對于晚明其他龍象的《四書》詮解文獻研究相對較少。本文以文化史為視角,盡可能搜集所有的晚明高僧《四書》詮解文本,注重從中華文化整體的角度補充敘述明清文化儒佛之間融匯的復雜面貌,增補長期以來為學界所忽視的以文本詮釋為中心的歷史事件。本文認為,詮釋文本的先在文獻結構對理解詮釋文本具有重要的先在意義,特別是在文化史的研究中,必須通過梳理文獻的不同結構背景,才能清楚地把握詮釋文本的文化史意涵,這有別于哲學和哲學史的義理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任務和基本方法。本文對晚明高僧《四書》詮釋的文獻考察即是基于這一方法的努力和嘗試,通過這一獨特群體對于儒家文獻的詮釋的考察,以期為明清文化史、儒學四書學的研究拓展視野。
一、 晚明高僧《四書》詮釋的文獻背景
晚明一般指萬歷中期至清初,明代遺老在清初的活動在文化上具有延續性,因此一般文化史的研究將之也歸為晚明,而不是以政權更迭為劃分標準,這與一般的歷史研究略有區別。因此,現存佛教文獻很多署名清代高僧的部分按照本題的研究也應當歸為晚明。以此為標準,則晚明上下限的僧人又具有兩個不同的時代特點。萬歷時期的僧人以四大高僧為代表,對于時代學風與宗風衰頹的格局有所傷痛,立志振興佛教,展開了豐富的文化活動和興教運動。明末僧人除了延續四大師的傳統之外,亦有很多儒門中人迫于改朝換代的壓力逃禪歸佛,他們在終極旨趣上有著復雜的面貌,不可統括。對于《四書》,以儒闡儒、以佛闡儒的情況兼而有之。因此,并不能籠統地概括僧人作為佛教徒詮釋《四書》的特點。如果我們將其詮釋《四書》的文獻作為經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置于四書學文獻之中考察,則會發現一個較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對于了解晚明文化史、佛教史均有重要的意義。
《四書》作為一個完整的文本系統始于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此后的四書學無論是在朱熹的系統之下,還是作為心學詮解的面貌,都脫離不了朱熹的文本結構奠定的學術格局。朱熹的四書學具有對儒學文獻的宏觀安排,因此,其四書學的意義不局限于《四書》本身。
朱熹認為,“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朱杰人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450頁。朱熹所謂的階梯關系主要是想強調讀書人切己的感受建立的文本與生活的關聯,比較而言,《近思錄》所記載的宋代大儒更容易以人格氣象感染熏陶,使儒生獲得切身的感知和感動。同樣,他認為以四子為階梯,才能夠更加真切地懂得經的道理。粗略來看,朱熹在處理六經、四子書以及宋儒理學之書的關系上,強調了依順宋代之優秀者進入對四子的理解,進而通過四子深入對六經的理解,這樣得到的才是儒家意義上的對經的正解。可見朱熹在儒學文獻上具有嚴格的文本導向,以儒家經學作為其《四書》詮解的重要方向,雖然《四書》修身立本是基礎,但是最終的六經(實為五經)才是終極目標。
在朱熹完成《四書章句集注》以后,四書學的發展出現了重要分化:一方面,儒學學統內部的程朱派和陸王派對四子書有不同的解讀和修養方法,在道統觀念上也對《四書》有輕重不同的認知;另一方面,明代統治者承接元代,將《四書章句集注》作為程序功令,在政統上強化了程朱派的地位。此外,明成祖命胡廣等人編撰《四書大全》,頒刻四海,程朱派四書類文獻成為讀書人求取功名的敲門磚,這種由明朝統治者推動的學術風氣造成了惡劣的結果,不少讀書人對朱熹初衷及思想產生了背離和誤解。而具有儒學道統擔當的讀書人則更多的開始親近和認同陸王之學。政統與學統交織的格局使得道統的延續不再穩定,在程朱陸王紛爭的背后,精英儒學開始出現新的危機。
2014年第6期
晚明高僧《四書》詮釋文獻考察
作為過渡階段的元代四書學之概況,周春健博士《元代四書學研究》詳見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究》,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2005年。論述了元代四書學在民間和官學之間的沉浮,注重科考對學術研究的影響,介紹了宗朱、異朱、會通朱陸等不同派別在四書學上的具體差別,對此本文不再贅述。但明代編著的《四書大全》則顯然具有很強烈的宗朱色彩,并且吸收和總結了部分元代的成果,成為了實際上影響明代四書學的核心文獻。如果區分朱熹的四書學和明代朱子四書學的差別,可以通過文獻構成分析來體現。
首先,從《四書大全》所宗者而言,本當以朱熹晚年定本為是,然實際情況卻是對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定本的選擇沒有精善的處理。中華書局1983年新編諸子集成本《四書章句集注》點校說明指出,“明初官修的《四書大全》,全錄朱熹的注,為此后坊間各本所宗依,其實并非善本。”這一問題直到清嘉慶間吳英、吳志忠父子于1811年刊出校訂版本方得以改善,第3頁。其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了《四書大全》文獻結構上的兩個問題。其一,《四書大全》編撰有泛濫之病,后雖有元代倪士毅增刪,但終究其裁度受到程序影響,胡廣等人編撰的《四書大全》延續了泛濫的毛病。這一點從四書學文獻內部來看,不合乎上文分析的朱子四書文獻內部結構,缺失了朱熹四書文本詮釋體系的方向性和完整性,并且在理解上因為增入了多家的注釋,相對陸子學而言,支離的特點更加明顯。其二,《四書大全》的頒布雖然同時有《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在文獻結構上類似于朱熹“五經——四子——近思錄”的文獻架構,但是,因為科考明確的功利性,《五經大全》不能與《四書大全》形成完善的外部文獻系統,《四書大全》的孤立也必然使得時代學風空疏無歸。關于性理的討論則會合心學派別越走越遠,也漸漸脫離了四書文本的約束。參見永瑢、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經部三十六,四書類二,第200頁。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基如果真的如同《提要》所說,全部落在《四書大全》,則學術風尚的改變必然會激蕩出新思潮。
明代興起的心學,從士人以及民間讀書人閱讀的書籍來看,《四書大全》的影響和刺激不能忽視。如果將陽明學置于陸王一脈,則其心學先賢陸九淵同樣認同四書,但是卻否認朱熹以理學架構的四書學,他強調讀書要讀古注,注重經學,反對過分的闡發詮釋四子書,特別不同意對四子書中的概念做理學的詮釋,而是直接在身上踐履,直呈本心。陽明則從批評朱子《大學章句》出發,建立了古本的系統。通讀陽明遺作,他沒有在文獻上安排四書的結構,更多的是通過討論理學問題,特別是依托《大學》文本討論心性之學,這一點有別于陸九淵。從文獻學的角度看,似乎王陽明對四書的認同要低于陸九淵,但是同樣對朱子的四書學的詮釋有重要的沖擊。而這一切參照朱熹龐大的文獻架構,似乎只是對應了四書和理學的部分,并且沒有通過理學理解《四書》進而回歸經學,反而是借《四書》討論理學問題,理學反而越來越成為關注的核心。
晚明高僧詮解儒家《四書》大體上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儒學道統與政統、學統與道統交織的紛繁復雜的局面,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普通民眾對經典的學習和解讀成為一個普遍性的需求之時,儒佛兩家如何隨順時代發展詮解《四書》正是晚明高僧詮解《四書》的大背景。
二、晚明高僧《四書》詮釋文獻介紹
現存可見的晚明高僧詮釋《四書》的文獻主要分布在佛教經藏禪師語錄,此外,亦有不少散見大型叢書和地方叢刊,有待進一步的搜集整理。但是不同于儒家注釋《四書》文獻,高僧詮釋《四書》很多并不是以《四書》或者《四書》內部篇目為名,現將已搜集整理的主要晚明高僧四書詮釋文獻列表如下:
序號晚明高僧四書詮釋文獻經藏出處詮釋類別1云棲祩宏
(1535-1615)《阿彌陀經疏抄事義》
《阿彌陀經疏鈔問辯》卍新纂續藏經第22冊No.0425《阿彌陀經疏抄事義》典故類編2憨山德清
(1546-1623)《大學綱目決疑》
《中庸直指》卍新纂續藏經第73冊No.1456《憨山老人夢游集》單篇講解3顓愚觀衡
(1578-1645)《中庸說白》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28冊No.B219《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單篇講解4吹萬廣真
(1582-1639)《一貫別傳》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40冊No.B480《一貫別傳》章節選論5覺浪道盛
(1592-1659)《學庸宗旨》
《杖門隨集?天界紀聞》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34冊No. B311《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單篇講解;章節選講6蕅益智旭
(1599-1655)《四書蕅益解》
(《孟子擇乳》亡佚)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36冊No.B348《靈峰蕅益大師宗論》通篇講解7方以智
(1611-1671)《一貫問答》手抄本,安徽博物館儒釋道三家雜論8金堡澹歸
(1614-1680)《書義》《徧行堂集》,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章節選論
晚明時期,三教融合是一個重要的時代特點,高僧一般對于老莊亦有深入的理解,因此,在很多作品中大多參雜三家思想,以上文本亦有不少是雜取三家言論之作。結合體例從內容上略作區分,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筆亂謇唷8美嘀饕指上表所列祩宏《阿彌陀經疏抄事義》,其主要目的是輔助僧眾文化基礎知識的學習,幫助僧眾進一步準確了解佛經思想。我們可以通過清代通理禪師的“事義”體論著的序言略觀一二。
余曰:欲辨正訛之義,還須講論之功。爰茲披文過講,日事窮研,間有字句舛差處,不無點竄。但疏中引古事跡,及諸典語,多有疑兕。未見的據者,以故徧討群籍,潛詢博達,不期年而匯集成本,用佐經疏流通。目曰《首楞嚴經指掌疏事義》,斯乃借古人有據之事跡,眾典可法之詞句,以證今疏樹立之義,則疏可發明,而經無疑滯矣。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者,聊為一助云爾。《卍新纂續藏經》第16冊,No.0309《楞嚴經指掌疏事義》,第347頁。
從通理禪師的序言可以看出,佛經注疏的講解需要借助事義類的著作來講解古人事跡詞句,這本身也是儒佛會通的歷史積淀,是明清文化發展的基礎條件。這一體例從經藏目錄來看,始于云棲祩宏。我們也可以大體上做出推測,祩宏講解凈土宗經典《阿彌陀經》,信眾開始從精英普及到民間,而這個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對很多文人士大夫耳熟能詳的典故進行補充講解,否則難以為普通民眾了解,這一類作品的出現,正是出于這樣的民間需要。其中儒家典故的條目涉及到了四書五經的各個部分。梳理其引用文字我們也可以進一步了解祩宏對儒家文獻的了解和取舍。
2苯簿類。該類文獻包括上表所列《大學綱目決疑》《中庸直指》《中庸說白》《學庸宗旨》《四書蕅益解》等。嚴格來講,該類文獻并不是嚴格的注疏體例,但大體上受到文本約束較多,以討論四書文本具體章節為核心,至少按照思想或者經文行文來講論。該體例的著作客觀來講,也受到時代講會風氣的影響,所以其思想淵源對于儒學程朱陸王的取舍也有豐富的展現。需要指出的是,《中庸說白》在思想內容上完全沒有涉及到佛教思想,這在佛教高僧詮解儒典上是有非常特殊意義的,因為顓愚所處年代較早,并非晚明逃禪僧,而史傳碑銘中對顓愚的記載也沒有相關的論述,對《中庸說白》的深入研究可以豐富我們對僧人以儒解儒旨趣的了解。總的來看,講經類著作在安民化俗、知識傳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于士大夫以及一般文人學習儒學和佛學產生了重要影響,該類作品中的《四書蕅益解》至今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對于民間善化的作用非常顯著。
3庇锫祭唷3了以上相對較為規范的講經類作品外,佛教語錄整理一般將禪師的儒家言論作為雜著單獨整理,如內容較少則歸類收入語錄,即在形式上更加自由,除了對話性質之外,還有一些就儒家思想發出的議論。以上所列《一貫別傳》《杖門隨集?天界紀聞》《一貫問答》《書義》等大多如此。而該類作品在內容上不完全是對儒家《四書》的詮釋,同時雜有對佛老的論述。如果以《四書》文本為中心考察,則可以豐富我們對佛教高僧詮釋儒典的認識。該類作品的作者也不乏如方以智這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從經學角度考察其作品,是長期以來我們研究較少的角度。而對于金堡澹歸這樣在歷史評價上存有氣節爭議的僧人,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其儒典詮釋的研究了解其心志,有助于我們對其作出客觀的評價。
三、晚明高僧詮釋《四書》文獻分析
如果兼顧高僧除《四書》之外的儒家文獻的部分,我們可以發現,德清和智旭儒典詮釋著作還有:憨山德清的《春秋左氏心法》、藕益智旭的《周易禪解》。此外,永覺元賢《囈言》討論理學與佛學問題也有很多集中在四書相關核心概念上,林我禪師勸孝和勉學也以儒典為焦點。也就是說,從文獻角度看,高僧詮釋儒典不只局限于《四書》,其對《春秋》、《易》、《禮》等都有論述,并且對兩宋理學的諸多問題,比如心性、理氣、無極、太極等也多有涉及。本文接下來以表中所列文獻為例,分析其文獻詮釋的理解背景的差異所決定的理解的差異。
晚明早期的僧人詮釋《四書》首先是因為《四書》的影響是其不能不顧及的,無論是高僧自身從學的經歷,還是要誘導儒生學佛,基本上都是從《四書》入手。晚明早期高僧詮釋《四書》基本思路是將四書學作為儒學的部分,作為世間法置于佛學思想的架構。因此,對于佛教而言,宣講解釋儒家學說是其佛學思想契機契理的方便法門和下手處。對此,佛教高僧也從不諱言,智旭講:“儒也、玄也、禪也、律也、教也,無非楊葉與空拳也,隨嬰兒所欲而誘之。”《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36冊No.B348《靈峰蕅益大師宗論》,第354頁。不但儒家的書如此,即使佛教的經書也同樣如此。以此對照朱熹四書學外在文獻結構,首先出現了文獻結構上的重建。這種結構性的重建影響深遠,特別是在儒家內部,陽明學派討論心性問題大體上就是會通佛老在《四書》和理學上討論,從時代的閱讀經驗而言,高僧對《四書》的詮釋應該是找到了明代讀書人的根基,就此而言,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四書大全》的評價是一致的。
本文接下來對上表所列具有代表性的文獻做基本分析。以憨山德清為例,德清并沒有嚴格按照朱子四書學的脈絡對《四書》做出詮釋,而是以自己的知識結構選擇性地解釋了部分文獻,并且這種解釋在文本上結合了老子思想、佛教思想,如其《中庸直指》,明顯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來解釋。德清對于《大學》的解釋則認同了朱熹經傳的區分,但是他只是對《大學》經的部分有所解釋,對于《四書》中的《論語》和《孟子》則沒有專門的解釋,可見,德清并沒有明確而精細的處理朱熹關于文獻結構提出的問題。換句話說,在朱熹的參照下,佛家的解釋是否具有真正的融合力,在四書學的角度而言,是存疑的。至少,這種儒佛會通的思想詮釋如果沒有接受文獻結構約束的情況下,思想的真正融匯并沒有實際發生過,深層次的交流也無可能,只是借助語言用法之間的共通性構建了一個交流的平臺。
又如《中庸說白》,顓愚和尚的《中庸說白》由三個部分構成,開篇是朱熹引用程子對《中庸》的論述,這與《中庸章句》相同,下文則去除了朱熹的注解,直接在章節原文下依照《中庸》經傳的順序論述要點。由此可見,在文本上使用的是朱熹的底本,但是在道理的理解上并不完全認同朱熹的思想。對于章節理解有不同意見也直接調整,不做過多說明和論證。這一文獻非常獨特之處在于,幾乎在所有的佛教高僧以及逃禪僧都會依托《中庸》文本強調三教融合的心法,但是此篇對《中庸》原文的解釋嚴守了儒家自身的理解,對于《中庸》作這樣的詮解在于他理解的儒家之道與佛教的關系不需要在具體的思想上再作融匯,儒家《中庸》之道可以與“平常心是道”的趙州思想直接等同。他在《中庸說白序》中講:
是書乃孔氏心法。此心也先天地而無始,后天地而無終,若斯豈有古今隆替哉?其隆替之端在乎人耳。羲皇之上無有文字,雖不見授受之跡,而心傳密會,信必有之。自堯舜乃有典型,其傳受之語明著其中,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傳至周孔,其道大行。然道與世事有盛必衰,孔孟而后其道幾喪,秦漢以降六藝并行,人莫識其本末。于中雖代有其人,不免為余氣所雜,僅微微一絲潛注而未絕,似乎亡矣。至于大宋程朱諸夫子正脈復起,程朱之起者乃因佛法之勝,激勵其心也。程朱排佛,可是知佛恩乎?有僧問趙州:“云何是道州云‘平常心是道?”似合此書之旨。且何處是平常心?即夫婦之心平常心也,兄弟之心平常心也,父子之心平常心也,朋友之心平常心也,君臣之心平常心也。至于天覆地載,暑往寒來,皆平常心也。雖然如是,要在即今夫婦君臣間指點出平常心來,又卻難矣。欲知平常心,到不如黧駑白牯卻有些子。如此說話,但識趙州字,未知趙州義。欲得趙州義,自知不止欠三十年飯未吃在,是謂說白。《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28冊No.B219《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第697頁。
顓愚對于儒家道統的判定和認識與程朱理學類似,特別是他同意尊奉程朱為正統。稍有不同意見之處在于他認為程朱應該感激佛恩的激勵使得儒家得以中興。他引用趙州語錄“平常心是道”以對應《中庸》宗旨。他將儒家天地人倫之道盡歸為平常心,這樣的思想架構使得他并沒有在文獻內部再做文字思想上的整合。但是,此書之作并非就是《中庸》或者趙州所修證到的理解。故稱尚需三十年的修行努力,此非為謙辭,實則強調了對道理的理解終究只是虛知,需要落實到實處。“說白”之義正是強調的該論只是說,而不是行。充分體現了顓愚解釋經典文本強調工夫論的方面。
再如,智旭四書學著作主要為《四書蕅益解》,從表面上看,他認同了四書學的基本體系,但是對于《四書》的理解也沒有完全等同朱熹在文獻順序上的安排。或者說,智旭站在儒家心學一脈的視角,順理成章地對朱熹的《四書》學進行了消解,這個消解的第一步就是擺脫《四書》強化了的結構。他解釋:
首《論語》,次《中庸》,次《大學》,后《孟子》。《論語》為孔氏書,故居首。《中庸》《大學》皆子思所作故居次。子思先作《中庸》,《戴禮》列為第三十一。后作《大學》,《戴禮》列為第四十二。所以章首“在明明德”承前章末“子懷明德”而言,本非一經十傳,舊本亦無錯簡。王陽明居士已辨之矣。孟子學于子思,故居后,解《論語》者曰點睛,開出世光明也。解《庸》《學》者曰直指,談不二心源也。解《孟子》者曰擇乳,飲其醇而存其水也。佛祖圣賢,皆無實法系綴人,但為人解粘去縛,今亦不過用楔出楔,助發圣賢心印而已。若夫趨時制藝,本非予所敢知,不妨各從所好。蕅益智旭:《靈峰宗論》,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685頁。
首先,智旭認為學庸皆為子思所作,但沒有過多地解釋文獻考證上的理由,如此則四書文本是三子的傳承系列,這無疑是一種自然的時間順序。去除了朱熹先用《大學》三綱八目奠定一個人的規模,再通過《論語》、《孟子》涵養操存圣賢氣象等來修養,最后體貼《中庸》心法的精心安排。其次,從《大學》文本內部來看,智旭不認為舊本有誤,否定了朱熹增加的《補格物致知傳》,不同意經傳的劃分,并直接引王陽明觀點為證。再次,智旭對于《中庸》《大學》的看法比較重要的一個銜接工作是,針對他自己提出的四書讀書順序,他給出了文本證據,強調《中庸》在《大學》之前,即指出了《中庸》最后一段引用詩經的文字“予懷明德”,他認為這個“明德”正是銜接《大學》“明明德”的,而這個問題從文獻學的意義上看,主要是開始在四書內部提出與朱熹不一樣的讀書順序,并給出一定的理由。最后,他明確提出不是為了程式功令,只是幫助印心,此心從儒學來看,即陸九淵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心,但更為重要的是,智旭將此落實到佛學所說的本來清凈心,將儒學講的心看成是性。如果拋開身份,從儒學看智旭的解釋,他也已經重新整合了文本,沒有了朱熹一再強調的《太極圖說》潛在預設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的結構,對于儒家德目的理解更加注重以佛教來統攝。同時,智旭添加了儒學的其他文本作為參照,如《周易》、《詩經》、《孔子家語》以及陽明的解讀和李卓吾的解釋。這部分較為特殊的是,智旭對《四書》的詮解從引用率看,比較偏重陽明和李贄,從明儒傳承看,李贄思想雖然和陽明思想有親緣關系,但是,直接抽出李贄和陽明,拼貼出來的儒家言論并不符合嚴謹的學派特征。從智旭對《周易》等儒家五經文本的解讀來看,他在詮釋《四書》的時候,也沒有正面回應朱熹為何強調《四書》的讀書順序,對于五經以及四書五經關系的論述更沒有提及。
而覺浪道盛似對程朱理學并不認可,他在《書義全提序》中提到:
孔子時集大成,則中和位育,無所統紀矣。孔子后有顏曾思孟,相繼申明孔子為天地人物之師宗以,故后之千圣百王皆得取法。此慎獨至誠為教養之道,不致流為無忌憚者率禽獸而荒之。誰之力歟?宋儒多墨守其法,不知變通,不免又流為執計穿鑿矣。至姚江良知之學一出,大掃支離。惜未有幾人能述此教養時中之道。精至慎獨,神于至誠,原于天命,為天地人物之宗旨,以定平此世界也。所賴有《大易》《五經》《四書》之微言尚可尋繹,故予自知有此道無時不全,提此教養宗旨,以統會三教九流百工人物歸于慎獨至誠,以克此精一中和勤儉簡易為目標,使天下古今曉然,不敢大過不及,為無忌憚,以亂千圣之心法。《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第34冊No.B311《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第721頁。
他認為儒家至陽明學派興起,才對教養之道有所復歸,而可惜風尚影響不大, 所以他認為,必須依靠儒家經典來闡發這個大道,使得世間三教九流皆能受到教養。這個論述中有兩個重要的部分,一個是強調了儒典對于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還有一個就是他強調的儒學不再是精英之學,對于三教九流百工皆要教化,從受教者的普世性上看,要更加寬泛。所以,其《學庸宗旨》的部分基本上與儒家心學一脈是契合的,其論述除去其佛教徒的身份實則與儒家相差無幾。《天界紀聞》大體上也是以《論語》的內容進行講論,思想主旨與上述差別不大。
此外,廣真的《一貫別傳》共五卷,儒家一卷,老莊一卷,佛家三卷,儒家部分也涵括較廣,除總論儒宗之外,有《周易》、《四書》相關章節的討論。廣真認為儒釋道三家是“一鼎三足”的關系,他認為儒釋道還可以用一乳多名來理解,強調三者之實具有共同的特點。其詮解儒典多以老莊佛經典故等詮釋。
青原愚者方以智的《一貫問答》內容不是很多,共計只有一萬多字,但是討論儒家《四書》部分,涉及到的其他典籍則包括了《周易》《華嚴經》《莊子》《陰符經》《維摩詰經》《楞嚴經》等等,還涉及邵雍、唯識學等相關內容。在思想主旨上已經開始偏離了《四書》文獻的注疏式理解。在這個方向上有不同發明的還有金堡澹歸。
金堡澹歸的《書義》應該說是晚明《四書》詮釋的又一個獨特范例,其書論述四書標列《四書》相關主題,斷以己見。如其詮釋《大學》“知止而后”節曰:
今夫萬境俱來,一我應之而具足,此非有而我也。萬境俱變,而我未嘗遷,萬變俱往,而我未嘗去,此非我只所止哉?然而世之人有止而不知,求知而愈不止,何也?……故止者,示有定名,而未始有定位也。不知止者,不知無定之自定,而求定于定,則往往求定于靜,此倒見也。夫定者,定亦定,不定亦定。故有定者靜亦定,動亦定,定而后能靜,靜亦靜,動亦靜。……澹歸:《徧行堂集?卷十八》第2冊,廣東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1頁。
對于《大學》原書的詮解旨趣,他并沒有過多的關注,而是借助《大學》文本抒發自己對于“知止而后有定”的理解,在文獻上脫離了《大學》的限制,而將對“止”和“定”的理解放到其自己的知識背景之下。從上述引文我們可以發現,《物不遷論》以及《莊子》,乃至程子的《答橫渠先生定性書》皆是其思想的主要來源。由此可見,金堡澹歸的《四書》詮解與前面的僧人詮解儒典沒有延續關系。
綜上所述,即使同是佛教徒,對于儒典詮釋在文獻學的角度也能看出類似儒家程朱陸王的差別,但是總的來看,因為文本的語境和關聯發生了改變,無論注家是否刻意,都一定會產生新的理解和融合,從邏輯上講,應該有一個文獻語境先在的決定性。而這種文獻語境的先在性又與佛教高僧自身的學養和讀書因緣有關,并沒有一個學理上的必然性。
結論
通過以上的文獻基本介紹和分析,我們可以總結高僧詮釋《四書》在文獻上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是高僧詮解《四書》的背景是儒釋道三教文獻結構的重整,不局限于某一家某一派;二是高僧詮解《四書》對儒家詮釋傳統并不全部回應或詮釋,因為他們沒有爭奪學統、道統解釋權以影響政統的期望,但是三教整合的詮釋旨趣塑造著一個以民間為基礎的文化道統;三是高僧詮解《四書》對儒家詮釋傳統的選擇性拼接,按照佛學立場截取所需;四是因為缺乏內在學理上的規范,因此高僧詮釋《四書》的文化功用主要在于激發民間傳統、化民安俗。總的來說,高僧詮釋《四書》的多樣性為儒典以學理形態深入民間生活各方各面提供了文化滋養,也是儒家典籍與生活融貫的重要方式,不可忽視。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