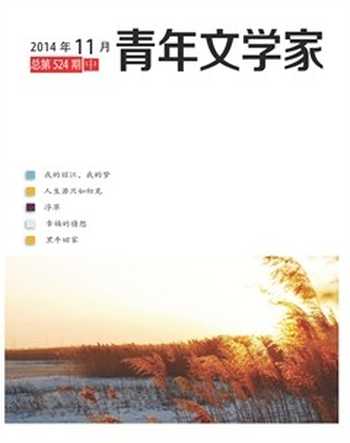試論北魏造像碑的漢代淵源
張優群
摘 ?要:北魏時期,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下,我國佛教造像大肆興起。這種佛教造像藝術是外來佛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北魏時期的造像碑既受了外來文化藝術的熏染,也有著對漢代藝術樣式的傳承。本文擬從形制、圖像、結構和構圖以及藝術手法等方面分析北魏造像碑造型的漢代淵源。
關鍵詞:造像碑;造型
[中圖分類號]:J3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32--02
一、引言
早在造像碑興起之前的遠古時代,中國人就有用樹石來表達對土地神崇拜的習俗。現今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玉璋、玉圭 ,證實了先民對“美石”的偏好。據文獻記載,商周時期人們就已經模仿玉圭發明了石碑,用于重大的禮儀活動。《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載了秦始皇泰山刻石的情況,可惜原碑已殘,僅存十字,無法考證原石的形制。但這些都是石碑的原型。到了漢代后期,用銘文記述建碑原由、出資者姓名的功德碑,祭天、祭孔的石碑,以及用于喪葬目的石碑廣泛流行。這些碑大部分建于公元一世紀至公元二世紀。到了北魏時期,由于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我國佛教造像之風大肆興起。這種外來藝術一開始就和我本土文化交相融合,進而產生了一種具有諸多文化因素的中國特有的藝術樣式:造像碑。
造像碑按所屬宗教性質可分為佛教造像碑和道教造像碑,還有一種佛道混合形造像碑。北魏造像碑在形制、圖像、結構和藝術手法等方面承襲了漢代造型藝術樣式,既吸收了外來文化藝術特征,也是漢代藝術樣式的傳承。
二、北魏造像碑基本形制的漢代淵源
漢代早期石碑通常高一至三米,最初多為圭形和簡易方形,但很快又出現了以螭裝飾的弧形碑首。這些石碑大部分產生于公元一至二世紀,基本上由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組成。碑身的正面謂“陽”,刻碑名;反面謂“陰”,刻題文;左右兩面謂“側”,亦用以刻題名。碑首內通常有用于題刻“標題”的篆首,碑陽刻造碑緣由,碑陰刻出資者姓名。漢代保存下來的這類石碑多為喪葬碑,其次為功德碑。這種構造的石碑在后世廣為延用。
北魏造像碑在最初建造時并沒有被稱之為“造像碑”,而是被稱為“石像”、“四面好銘”等。據羅宏才先生在《中國佛道造像碑研究—以關中地區為考察中心》一書中對“扁體碑形造像碑各時期稱謂示例統計”一表中顯示,遲至北周保定三年(公563元),造像碑發愿文中始見“碑”的稱謂。筆者按羅先生的統計將發愿文中的稱謂進行分類,有如下幾種:1.以其形體指稱,如“四面好銘”“四面真容”;2.模糊稱其為“像”、 “石像”;3.以主龕造像尊號指稱,如“阿彌陀佛”、“彌勒”,4.稱“碑”者;5.其他。這些稱謂交錯繁復,通過分類,筆者認為冠以“四面”指出其形體的,應該和石窟造像中“中心柱式”石碑有著某種關聯。而以主尊尊號指稱應該是強調具體的信仰。泛指為像者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應該是在強調其“圖像”的視覺性。這些構想缺乏依據,還有待進一步考證。而稱謂“碑”者,我們通過分析現藏臨潼博物館的北魏正光年間(公元523年)的師錄生造像碑,了解到其在建造之初就和碑的視覺特征及其紀念功能相關聯,使之具有碑的特征。這是一尊佛道混合造像碑,高215cm,寬77cm,厚27cm。碑陰碑陽在視覺形式上和漢代石碑相似,同時也具有漢代石碑所具有的螭形碑首、篆額、碑身銘文等基本要素。這些要素佛教造像碑也有采用,如甘肅省博物館藏北周保定三年(公元563年)權道奴造像碑,碑高82cm,寬33cm,螭首,長方形碑額,內有“伏福寺”三字,碑陽有發愿文和供養人提名,這些符合我們今天碑的定義的視覺特征和基本構造。又如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的北周呂建從造像碑,碑高111厘米,寬50厘米,螭首圓頂,篆首內刻“建崇寺”三字,碑陽有長篇發愿銘文。
受佛教造像藝術影響,雖有圖畫因素融入了傳統石碑,但北魏造像碑還是保留了漢代碑的一般形制,并沿襲了漢代以來石碑的紀念功能。
三、北魏造像碑一般圖像的漢代淵源
北魏造像碑的基本圖像有龍紋,廡殿式龕楣和博山爐,這些圖像和它象征在漢代已經形成。
龕楣交龍紋圖樣是造像碑常見的樣式之一。中國已知最早的龍的形象是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村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碧玉龍,是不同圖騰崇拜的部落融合的產物。進而發展成商周時期刻在青銅器上的夔龍紋。秦漢之際這種龍紋成為皇權的象征及民間祥瑞動物,并使用在碑上。其漢代墓室的壁畫和畫像石中也多有表現。漢代人相信靈魂不死,龍引領是靈魂升仙的交通工具。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銘旌里,墓主人的靈魂正是乘著雙龍飛升天國的。北朝造像碑沿襲了漢代信仰及以龍為裝飾的圓形碑首的樣式。
龕楣廡殿式圖樣是佛教造像和道教造像主要區分的標志之一,顯示了道教造像一開始力圖區別于佛教造像的花瓣形的背光造型。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樣式來源于墓室建筑闕。闕在漢代標志著天宮的入口,是靈魂升仙的場所,和北魏造像碑就有相同的“升仙”功能。漢代人們認為靈魂不死,在另一個世界應該享有更好的物資條件,因此漢代畫像石經常刻有這一建筑形象—“天宮”。
漢代博山爐昌裝飾在主龕造像的下方,兩側常有“邑師”、“邑正”和“道士”等神職人員,作禮儀狀。早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就有燃香的習俗。博山爐在漢代是非常流行的樣式,主要源于漢代對于神仙居住之所-仙山非常向往。博山爐爐體峰巒疊嶂,中空用于燃香,有孔與外相通,燃香時煙霧從孔洞中冒出,頓時群山間煙霧繚繞,有如神仙仙境,因此而得名。這種博山爐在漢墓中多有出土,其中最為精美者有現藏陜西省歷史博物館的漢代無名墓出土的鎏金銀銅竹節熏爐和河北滿城劉勝墓出土的錯金銀博山爐。北魏期道教造像碑所刻博山爐與漢代博山爐形式相仿或直接挪用了漢代博山爐的樣式,這些樣式在一些佛教造像碑也有采用,并成為禮佛的象征。
這些在漢代就形成的具有特定象征的圖像,在北魏道教造像碑上大量出現,同時也被佛教造像碑所采用,顯現出造像碑對漢代藝術的繼承。
四、北魏造像碑畫面的結構和構圖的漢代淵源
北魏造像碑碑身從一面造像到四面造像的多種樣式,各個面在構圖上自成整體,尤以碑陽和碑陰最為精美。造像碑多為“天”、“連接天人的中間結構”和“人”三段式結構,采用不留空白的“滿畫幅式”構圖。上部碑額通常用龍紋、雙鳳鳥、屋頂、日月紋來裝飾,竭力營造一個奇異的天上空間。中間間以“道士”、“邑師”、“邑正”等神職人員來溝通天和人,碑身下部為供養人、出行圖等,表現出人間生活。各部分雖屬不同空間,但并不以界格將其完全分開,而是各不凡間相互穿插交織,空白處飾以瑞獸、植物等紋樣,這樣在構圖上主龕造像突出,形式飽滿,渾然天成。如耀縣博物館藏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魏文朗造像碑,這是一尊佛道混合式造像碑,高131cm,寬60-72cm,厚29-31cm。該碑碑陽主龕刻雙尊坐像,一佛一道。上部龕楣刻雙交龍紋,雙龍身和龍舌分碑交繞在碑身中線上,左右各飾一飛天羽人,雙龍尾各由左右兩側垂至龕楣中部,上卷的尾部巧妙的圍合了上部空間,而使像龕下部成開放狀態。主尊造像坐在胡床上,兩側床腿稍下延,右側外部刻一道女,左側刻一漢式建筑。胡床下方兩床腿中央刻一博山爐,博山爐上部與胡床底部相接,兩側各刻一人作跪拜狀。博山爐下方刻一行車馬出行圖,兩側都到碑的邊沿。其中以女子持傘,傘頂部升至博山爐底座左側跪拜狀人居于下方。碑的底部刻一排供養人,成平列式展開。該碑碑陰和碑陽相仿,局部內容稍有不同。兩碑側稍簡。北朝年間道教造像碑多采用這種結構方式和構圖。如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北魏延昌元年(公元512年)朱奇兄弟造像碑。其中有些碑由于下方所刻供養人過多而影響視覺,但就其結構而言并未改變。
這些造像碑的結構和構圖樣式我們在漢代帛畫,畫像石,畫像磚里能找到其原型。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銘旌最為典型。一號墓銘旌也分“天”、“中間結構”和“人”。上段天宮中央畫有一人首蛇身女媧,兩角分別飾象征日月的金烏和蟾蜍,女媧和日月圖形間以仙鶴填補。天宮下部畫兩條蜿蜒飛舞的巨龍,兩龍頭上仰至女媧交繞的蛇身兩側。天宮下部雙龍中央有天闕,兩司閽守門。上方兩只瑞鳥相對而立,下飾一蝙蝠的菱形紋樣鑲入天闕之中,兩條飛龍載著墓主人從兩側飛向天闕。下段錯綜交繞的兩龍尾中畫一廳堂,廳堂內設案列鼎,有人跪坐向死者致祭。這樣的原型還有馬王堆三號墓銘旌和山東臨沂金雀山九號墓銘旌。
通過分析比較北魏造像碑和漢代帛畫的結構與構圖,我們發現其有很大的相似性。
五、北魏造像碑藝術手法的漢代淵源
北魏造像碑除基本形制、圖像、結構和構圖等方面沿襲了漢代藝術之外,還在藝術手法方面承襲漢代畫像石陰線刻、平面減地輔以刻線和淺浮雕等造型方式。陰線刻是不直接拉開物體到底層次,僅通過向下刻出深深的線條來區分物體和背景以及物象的各個部件,結構類似于白描的一種方式。平面減地輔以刻線的造型手法是在平整的石塊上將主體物象以外的背景薄薄的減去一層,以區分物象和背景,但各物象間和物象各部分并不以高低層次表現物體的空間,而是通過邊緣輪廓線和機構線表現物象形體和空間的一種藝術造型手法。漢代畫像石淺浮雕手法和平面減地手法類似,通常也薄薄地減去一層背景,但物象各部分的空間層次通過減低交界處在后面的部分來實現,而物像高點部位處在同一平面。這兩種手法具有很強的平面繪畫性。這類畫像石在陜北,蘇北和山東與四川等地都有出土,北魏造像碑藝術繼承了這一手法,顯現出與外來佛教石窟造像所用的圓雕或高浮雕的明顯差異。
北魏造像碑通常在主尊造像處先造出一個弧形的深坑,主尊造像采用高浮雕手法表現主尊造像的形體,而龕楣裝飾圖樣和供養人采用畫像石平面減地或淺浮雕手法,既保證了碑體的整體性,同時主龕造像突出,光影下也顯得異常神圣。如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田良寬造像碑。該碑除采用高浮雕形式刻出主尊造像形體,并刻曹衣出水般密集的線條表現外,龕楣、飛天 、供養人等采用刻線的手法。又如邑子六十人造像碑,除主龕造像外,龕楣交龍紋、道士、邑師等神職人員與各供養人均采用平面減地輔以刻線的手法,這和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藝術手法一致。兩者均采用平面減地的藝術手法,刻去圖像以外的背景,使之與圖像相比低一個層次,圖像整體在一個平面上,圖像結構和裝飾均采用刻線。由此可見北魏造像碑在藝術手法上對漢代畫像石造型手法的借用。
六、結論
漢代民間流行 “升仙”信仰,事死如事生,盛行厚葬。為實現“升仙”的愿望,在地下建造起富麗堂皇的墓室壁畫、畫像石、畫像磚,在地上樹立了高聳的石碑、石闕,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漢代喪葬藝術樣式。這些藝術樣式后世不斷沿用和發展。北魏造像碑在形制上基本承襲了漢代石碑石闕的基本樣式和構件,圖像沿襲了漢代帛畫和畫像石的圖樣及象征,結構和構圖樣采用了漢代帛畫、墓室壁畫和畫像石、畫像磚的結構和構圖,藝術手法方面直接承襲了漢代畫像石平面減地輔以刻線的藝術手法,是外來佛教藝術的外衣影響下的中國特色的藝術樣式,對后期佛教造像中國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羅宏才.中國佛道造像碑研究—以關中地區為考察中心[M]. 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
[2]王靜芬.中國石碑一種象征形式在佛教傳入之前或之后的運用[M].商務印書館,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