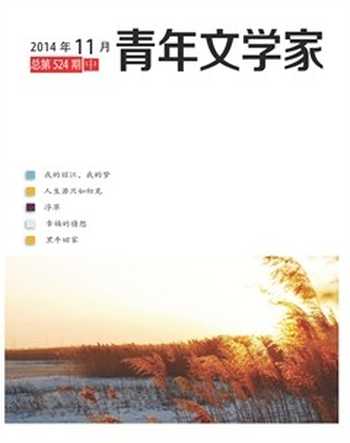“索非索,欲索何索”
摘 ?要:虹影的《阿難》以一種不可靠敘述,兼用各種流派的各種手法,把一個神秘人物的神秘事件敘述的撲朔迷離。在具有強烈可讀性的同時,深入地探討了當代人的靈魂世界,體現一種無根的漂泊無助感和無法取得救贖的深深悲涼。
關鍵詞:精神與肉體;靈魂與欲望;孤獨;不可靠敘述;各種表現手法
作者簡介:張磊,女,1984年出生,河南信陽人,畢業于河南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方向,碩士學位,現就職于河南大學民生學院。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32-0-01
佛教基于它“解救眾生于苦難之中”的信條給蕓蕓眾生以心靈的洗滌與解脫。對于普遍沒有信仰的中國人來說,這樣一種精神慰籍的圣道確實給過無望的眾生以靈魂的超脫和救贖。<<阿難>>中,虹影向我們傳統的認知方式提出詰問,并以一種探尋的筆觸向我們揭開了人在完成自我救贖時的艱難與漫長,以及這種救贖實際上最終無法實現的人生悲劇。 “小說抓住了存在的一種可能(人與他的世界的可能),并因此讓我們看見了我們是什么,我們能夠干什么”。[1](p42)
虹影曾說:“苦難與我是‘帶發修行”[2]。其實,所謂的苦難,也就是精神與肉體之間的博弈,是靈魂與欲望無法達到統一時的“心的苦難”。即:“精神的工作是解放人,讓人超脫;肉體的工作則是設陷阱,搞欺騙,讓人陷在欲望的深淵里。只有這兩方面的互動才夠成追求。”[3]。米蘭·昆德拉說:“我們被外界所決定,被一些誰也無法逃避的境況所決定,這些境況使我們和其他人日益相象”[1](p24)。阿難最終沒有抵制住外界的誘惑,沒有抗拒住肉體欲望的侵蝕,沒有逃避掉商品大潮中對金錢的無境角逐,他終于放棄了自己精神的純粹, 變成了黃亞連——一個在商品經濟社會角逐中俗不可耐的投機商人和經濟罪犯。“人要作為有理性的動物來釋放欲望,就逃不脫變形的命運”[3],虹影從側面抨擊了幾乎畸形的時代精神,以及這種精神給每一個個體生命造成的強烈的沖擊。然而,淪為罪犯的黃亞連終于感受到了肉體的強烈禁錮,也感到了世俗欲望的毫無意義,他開始試圖尋找自己以往的精神家園。在異國印度舉辦個人演唱會就表明了他對現實錢欲的放棄以及向藝術靠近的努力。而這一過程的艱難使他明白,墮落的肉體與純粹的精神彼岸有著怎樣的溝壑,他們之間的矛盾在現實面前又是怎樣的難以調和。虹影在這一過程中傾注了大量的筆墨與感情,向我們傳遞了她對現實、人性的復雜的深層思考。
然而,虹影的思索并沒有停止。她之所以讓她的所有人物集聚印度,并且在“大壺節”這一特殊節日中來審視這種精神救贖,正是為了探索宗教之于人靈魂的作用。黃亞連為了完成自我救贖,遠赴印度`,企圖能夠在圣城,在萬人滌罪的昆巴美拉節洗滌自己的罪惡,可他并不知道,“精神若要穿越肉體的原始森林,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同死亡晤面之外沒有第二條路”[3]。他終于看到了宗教對于自身靈魂的無力救贖,他所有回歸的努力,他努力過程中的巨大痛苦,佛手遠不能超度。虹影在這里傳達了另一種終極認識:人類的精神矛盾和困境沒有終點,欲望之水永遠高于理性的堤壩,這才是精神困境永無出頭之日的最大原因。
如果說《阿難》這部小說是一部純粹的后現代小說是不夠準確的。盡管作品中體現了后現代小說的“通俗化”傾向,即情節離奇、曲折、可讀性強,并且運用拼接的手法把各種毫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但純粹的后現代小說無法從中釋讀出作者的創作意圖和某種特定的意義,而從虹影的敘述中我們很明顯就可以知道她的創作意圖以及作品的意義,即在時代大背景與歷史的契合之中彰顯人性的復雜和對自身命運無法把握的困惑。在《阿難》這部小說中雜糅了各種流派的各種手法來為她所要表達的主題服務。作者運用現實主義作為她敘述的大框架,即“我”出發去印度尋找阿難到“我”從印度回國的整個過程,無疑是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來敘述的。
著名文學評論家樂黛云給予《阿難》這部小說很高的評價:“這部小說不管是在形勢和內容的結合上,在哲學和宗教的結合上,在藝術和人生構思上都很突出,它探索人的靈魂和歸宿,又很高的品位。”[4]虹影這位“脂粉陣里英雄”,這位敘述狂歡者,以她獨特的敘述筆法和深邃的洞察力向我們揭示著對終極人生問題的拷問,引導現實中的人們對自身命運、靈魂的關照和思索。愿作精神的朝圣者,“恒河金黃的細沙,一如既往地順著河水流淌”。虹影在作品自序中這樣說。她對存在可能的探索沒有停止,相信也不會停止。
參考文獻:
[1]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M].文化生活譯叢.1992年6月第1版
[2]張潔.成長如影如虹.人民論壇[J].2003年第8期
[3]殘雪.精神與肉體.讀書[J].2002年第8期
[4]樂黛云.中國式的后現代小說.涪陵師范學院學報[J].2007年1月第2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