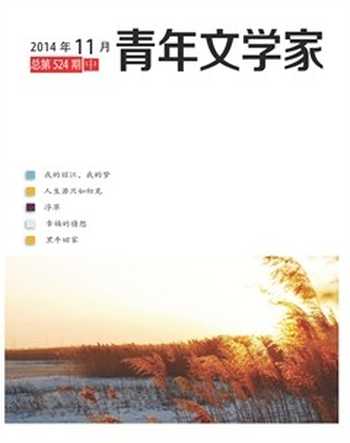近代小說“新聞化”的內在動因
摘 ?要:關于近代小說“新聞化”現象的研究,已有不少學人做出貢獻,而近代小說“新聞化”的成因分析也多有建樹,但多側重在時代風潮、技術革命等方面。本文將從中國傳統小說自身的特質,來探討近代小說“新聞化”的內在動因。小說從古代社會發展至近代,具有“新聞化”特征的“實錄”與“教化功用”,并不是僅僅來源于近代社會風云突變的各個方面的影響,而是傳統小說中早已孕育著的因素。
關鍵詞:近代小說;新聞化;內在動因
作者簡介:龍橋波,1987年生,女,漢族,籍貫:成都,畢業于四川大學,就職于四川師范大學成都學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32-0-02
1992年出版的《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一書中,作者袁進指出近代“新小說”作品有“文章化”和“新聞化”的傾向。“新聞化”是近代小說不同于中國古代傳統小說,也區別于現代小說的一種特點,此前已有不少學人對這一特殊文學現象進行了研究,關于近代小說“新聞化”的成因分析也多有建樹,但多側重在時代風潮、技術革命等方面。本文將從中國傳統小說自身的特質,來探討近代小說“新聞化”的內在動因。小說從古代社會發展至近代,具有“新聞化”特征的“實錄”與“教化功用”,并不是僅僅來源于近代社會風云突變的各個方面的影響,而是傳統小說中早已孕育著的因素。
一、基于事實的創作,古已有之
《世說新語》中記載: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于此,《語林》遂廢。”
南朝梁劉孝標注這段故事,引《續晉陽秋》云:“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自是眾咸鄙其事矣”。
東晉裴啟的《語林》,是一部品評當時知名人物語錄的書,由于《語林》的標新立異,為時人追捧,甚至形成風靡一時的“裴氏學”。但這部書卻因為所記的謝太傅謝安的語錄,遭到謝安本人的否認,被認為“太傅事不實”,而“眾咸鄙其事”,可見當時對小說 “實錄” 的追求。
無論作品是否全為事實,小說家至少都會強調自己的作品有根有據。東晉干寶撰《搜神記》,本多記民間神話傳說中的鬼神之事,但作者卻在序言中說:“雖考先志于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茍有虛錯,愿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可見,干寶是以史學家“實證”的態度,將“鬼神之事”作為真實來記述的。
小說發展至唐代,始開白話小說先河,而以搜奇記逸聞名的唐傳奇,也有實錄之作。如唐傳奇代表作品《李娃傳》,文末作者白行簡就道出了自己做這個故事的淵源:“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群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附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引文中所說的“生”即是《李娃傳》中的男主人公,“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群其事”,可知小說故事來源于發生在作者身邊的真實故事,基本為事實。
明代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的序言中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為奇,而不知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其為譎詭幻怪,非可以常理測者固多也。”作者抨擊時人多愛鬼怪小說,認為小說應把注意力放到日常生活中來,刻畫普通瑣碎的真實生活,也大有可為。
“睡鄉居士”為又一擬話本短篇小說集《二刻拍案驚奇》作序說:“今之小說之行世者,無慮百種。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為奇,而不知無奇之所以為奇。舍目前可紀之事,而馳騖于不論不議之鄉,如畫家之不圖犬馬而圖鬼魅者,曰:‘吾以駭聽而止耳。……即如《西游》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
這一段話,認為小說“失真”是“病”,而大贊《西游記》的“幻中有真”。接著,“睡鄉居士”還指出,凌蒙初的《二刻拍案驚奇》“其所捃摭,大多真切可據”,強調、宣揚作品中的“實錄”成分。
《中國古典小說理論史》一書提及:“中國古代小說早期創作十分注重語出有憑、事出有據。小說家一般不敢憑自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虛構結撰作品,而更多是借前朝或前輩的事件創作,于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可見,“實錄”在傳統小說的創作觀念中早就存在,近代小說求實求真,反映當時當世的社會現實,也不過是繼承了這種傳統觀念。
二、輿論教化的功用,古已有之
文學發展至明清,傳統的文學主流——詩文——走向衰落,小說作品開始大量產生,并在民間以傳閱、傳抄或演繹、說唱的形式,得到大眾的青睞。《金瓶梅》、《紅樓夢》等作品的誕生,更在宣誓著小說更多的可能性,定位著小說全新的高度。而近代小說則在這樣一種基礎上,由“大眾之愛”,走上了“精英之旗”的發展道路,不少仁人志士、學者文人開始關注小說、肯定小說,并致力于小說創作,甚至創辦專刊小說的雜志。自然而然地,小說的地位被抬升至了空前的高度,走出“小道”的低等定位,開始繼承傳統詩文“經世致用”的嚴肅使命。
而事實上,小說這種針砭時弊、引導風氣的功用,古已有之,歷代批評家都在強調小說的“功能性”:
對于“稗官”,顏師古引如淳之話,注為“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者,使稱說之。”可見,最初搜集這種街談巷語的目的,亦是為君王知曉民情來服務的,相當于君王治理國家的資料依據及輿論參考。雖然班固引述孔子的話,認為小說是“小道”,“芻蕘狂夫之議”,甚至還將其放在低于其他九家的地位:“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小說家的存在,是帶有功利目的性的,是為政治服務的。雖然《漢書·藝文志》的“小說”概念與后世小說大有不同,然而這種強調政治輿論功能的思維方式,影響深遠,也是孕育出白話小說的文化土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十分明確,自己是為“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迎合“春秋之義”,才創作這篇小說的。強調的是小說的輿論教化功能。
再如白行簡《李娃傳》開篇便說:“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
近代小說發端之前,明清小說已然蔚為大觀,佳作頻出。而這個時期的小說,仍然沒有擺脫《漢書·藝文志》中的思維方式,還是力圖在尋求小說的功用。
與金圣嘆認為《水滸傳》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的娛樂之作的看法不同,明代李贄撰評點《水滸傳》的《讀<忠義水滸全傳>序》,指出“《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將《水滸傳》的創作動機,與古代先賢韓非子進行類比,還進一步指出讀《水滸傳》的政治社會功用:“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日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日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君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茍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為發憤矣。”
終上所述,這種自小說發端就已根植的特征,已經漸漸深植于小說之中,成為中國小說倡導的特質。而中國小說這樣一種特質,剛好迎合了時代需要,也與新聞的特征不謀而合,于是小說在近代一變,更全面、更典型、更深刻地呈現出了成熟的“新聞化”特征。這是近代小說會發生“新聞化”的內在性的、根本性的淵源及動力。沒有中國小說自身的特質,就沒有近代小說“新聞化”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袁進《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6月版;
[2]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3]干寶《搜神記》,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9月版;
[4]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第十第四百八十四》,中華書局,1961年9月新1版;
[5]凌濛初編著《初刻拍案驚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6]凌濛初編著《二刻拍案驚奇》,陳邇東、郭雋杰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