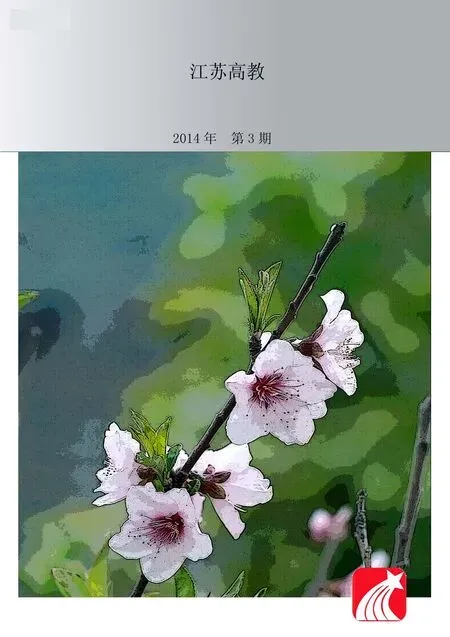人類學(xué)“田野工作”范式對(du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啟示
喬凱
(蚌埠醫(yī)學(xué)院藥學(xué)系,安徽蚌埠233030)
人類學(xué)正進(jìn)入到世界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術(shù)陣地的前沿,國(guó)內(nèi)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qū)W者借鑒人類學(xué)的成果日漸增加。但迄今為止,人類學(xué)并未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學(xué)科研究者的足夠注意——人們進(jìn)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時(shí)會(huì)借鑒諸多學(xué)科的理論與方法,但多不見人類學(xué)的蹤影。這是否意味著人類學(xué)與思想政治教育學(xué)科沒有交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人類學(xué)尤其是其獨(dú)到的“田野工作”研究范式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學(xué)科建設(shè)提供諸多啟示。
一、“田野工作”范式的意義理解與研究立場(chǎng)
1.“田野工作”范式的意義理解。當(dāng)談?wù)撈鹑祟悓W(xué)“田野工作”范式,首先想到的這是一種資料收集方法,指研究者深入到實(shí)地,通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居住體驗(yàn)等方式獲取第一手資料的過程。事實(shí)上,“田野工作”對(duì)于人類學(xué)的意義,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資料收集層面,而成為研究者學(xué)科認(rèn)同的重要標(biāo)志。我們可以從“田野工作”范式在不同學(xué)科視野中的地位進(jìn)行理解:“田野工作”范式在其他學(xué)科里只是研究的第一步,為后續(xù)研究做準(zhǔn)備;而在人類學(xué)里則得到完全不同意義上的發(fā)展——到實(shí)地去感受“正在發(fā)生”的事件的客觀環(huán)境與具體過程,理解當(dāng)事人的思想和行為,收集各種形式的資料,構(gòu)成整個(gè)研究的主體甚至全部[1]。如果從研究過程的角度來說,人類學(xué)的三個(gè)階段與“田野工作”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具體而言:首先是進(jìn)入“田野”地點(diǎn),獲取大量原始資料;接著是退回書齋,對(duì)“田野”資料進(jìn)行整理,撰寫民族志作品;最后,以“田野”經(jīng)驗(yàn)和文本寫作為基礎(chǔ),進(jìn)行文化理論的建構(gòu)與完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