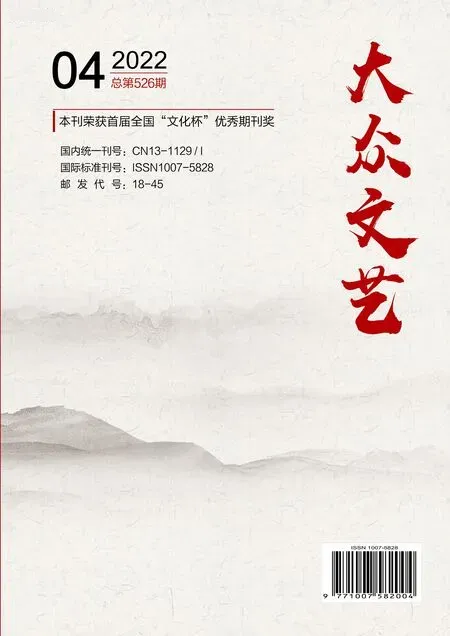海南黎族織繡中人物造型觀念探析
劉建峰 (四川美術學院 重慶 404100)
早在20世紀20年代,當代人類學家克魯伯在《人類學》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人類學的時代”的命題,到如今作為研究人的科學,已越來越成為顯學,出現了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以及史前學、民族學等分支學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視野對人類自身進行全面的研究。在這一學科大趨勢下,從人類的視覺造型藝術中來透視其歷史、文化、心理等諸多內容的新興領域——視覺人類學,也開始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新的方法和路向。
從嚴格的學科意義上來說,視覺人類學隸屬于文化人類學,但又有所區別。視覺人類學主要是從人類藝術活動中的視覺造型手段入手,通過其造物的形制、色彩、線條、空間、表現等,來關注作為社會存在的人,研究人的物態化、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習俗方面的文化內涵。狹義的視覺人類學,則指繪畫和工藝美術這類視覺藝術為研究對象,來探尋其中人類活動所隱含的文化意義。這里所研究的黎族人物裝飾紋樣,即屬于狹義的視覺人類學的范疇。
海南黎族是一個只有語音沒有文字的民族。因此,視覺圖形成為信息與情感傳遞的主要手段。在現存的織繡工藝中,源自生活、源自自然的獨特造型,為我們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實物資料。心靈手巧的黎族婦女借助傳統的手工技藝,織繡出濃麗燦爛的視覺圖形,它不僅融入了黎族古老的文化傳統和心理積淀,而且織繡出的幾何符號記錄了黎族社會的歷史變遷和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圖形除了具有圖畫的記事功能之外,還體現出黎族婦女的審美意識和豐富的想象力,自然成為黎族對社會生活本身的一種關照形式。其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含義主要表現為人們在社會生產活動中那種集體性的意愿和內心情感需要,而這些社會生活的背后卻深深隱藏著與這種集體性愿望和內心需要相聯系的原始信仰觀念。樸素的視覺圖形反映了由物質世界向精神世界過渡和轉化的這一過程,它開始表明人類物質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的意義,這也是黎族織繡圖案的社會價值所在。
黎族分哈、杞、潤、臺、美孚五大方言,各方言區由于生活習慣、文化經濟、生產環境等因素的不同,織繡圖案也有所差異。但在黎族各方言支系的織繡圖案中,包括一些年老婦女的文身圖案里,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舞蹈的人形紋樣作為藝術表現的主要題材。人形紋主要有反映狩獵、婚嫁和祭祀的內容,以及男女手持火把、載歌載舞、歡慶豐收的情景,寄寓了黎族對生育繁衍、人丁興旺、子孫滿堂的生命意識,其中蘊蓄著人類無窮的生命力,而這種生命力恰與原始的舞蹈中所表現的動作性融為一體,生育繁殖的生理本能或隱喻或直白的表現在狂放的舞蹈動作中。舞蹈是人類最早的藝術形式之一。幾乎在人類誕生之初的各種形式的生產活動中,就已孕育了原始舞蹈的雛形和萌芽。從現今我們所掌握的考古材料來看,1973年出土于青海孫家寨馬家窯類型墓葬的彩陶盆上繪有以“人”為表現主體的舞蹈造型,反映了我國西部原始先民生活中巫與舞的演變,特別是他們將巫術禮儀活動與描繪記事符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在長期的文化承傳過程中形成了從寫實到抽象的一個完整的文化藝術序列。在信仰萬物有靈的的原始初民那里,舞蹈無時無刻不與宗教活動有關,無論是節日慶典、人生禮儀、還是祭神祈福、驅邪逐疫、宗教樂舞都以古樸多姿、內涵豐厚、氣氛神秘的獨特魅力參與其中,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一書中認為:“原始人并不是以各種純粹抽象的符號而是以一種具體而直接的方式來表達她們的感情和情緒的。因此,在最初的巫術祭儀中,原始樂舞就成了最有效的方式之一”。1這樣看來,人形舞蹈紋作為黎族先民用來宣泄內心情感和表達內心意愿就不足為奇了。黎族婦女在服飾上通過夸張和變形的創作手法,把族人的樂舞和生活生產場景反映在織物上,使圖案造型視覺化、典型化。讓人驚奇的是織花人物,不僅表現手法多樣,而且還將人物圖形通過打散構成為抽象的連續紋樣或單獨紋樣,這在其他少數民族圖案中實屬罕見。除了織錦之外,采用刺繡創作的人物場景圖,由于表現相對自由,形態變化也十分豐富。

圖一

圖二
生活在這片島上的黎族,從其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中所提煉出的藝術創作更是神秘與吉祥、粗獷與自由交融的智慧結晶。黎族人物圖案不求外形的逼真,不重細節的刻畫,局部看,顯得十分簡單;整體看卻透露出一種活潑鮮跳的內在生命。人物的造型以戴大耳環和高獸冠做裝飾,特征十分突出。表現日常生活中的人形紋有上手上舉、雙手下垂和雙手叉腰的造型(見圖一);舞蹈人物的造型表現人與人雙手相牽,多為群體舞的形式,群體舞的姿態大多延續了黎族先民在集體圖騰崇拜活動中對圖騰物動態的模仿,如青蛙跳躍的姿態,飛鳥展開翅膀的動作等生動、靈活的形象,以象征生命與幸福。在舞蹈中,樂從心發,感物而動。人們既冪想著虛幻世界中各種神秘力量可能出現的容貌與姿態,同時又借用各種模擬性、象征性的形體動作,盡情地表現著她們的心靈體驗。從即娛神又娛人的舞蹈中體驗出神秘卻又充滿生命力的神奇氛圍,將人自身虛幻的精神世界、思想觀念寓于其中,成為黎族整個民族的心理縮影(見圖二)。表現男人和女人舞蹈的紋樣,則通過性別特征的描寫,凸顯男女形態的差別,用象征男女的舞蹈動作和肢體語言,來反映原始先民對生命起源與繁衍后代的強烈追求,是黎族人對“生命力”崇拜的形象的反映和體現(見圖三)。象征孕育的《孕母紋》,在杞方言的紋樣中是經常采用的典型題材,母子的造型為上下兩個人形的重疊,上為母下為子,孩子的上半截身子藏在母親體內,造型生動而富于變化,流淌著母子間的無間親情,是現實生活的寫照,又具有宗教上的莊嚴與肅穆。其中最具有視覺沖擊力的要數潤方言的織錦圖案,人形十分高大和魁梧,尤其是雙臂和雙腿非常健碩,在其胸前和下方各有一個較小的人形紋。有人將這一人形紋稱為“大力神紋”或“祖先紋”,倒也真切地反映出了黎族人也有類似于漢族的“敬天法祖”的思想傾向,在他們心靈深處,應該是通過想象將其神格化的結果。現存于通什民族博物館的《隆閨圖》《婚禮圖》《狩獵圖》等一系列紀事性織繡圖案則表現了黎族婦女傳統的婚嫁場面和部落繁衍、人丁興旺的族群訴求。最有代表性的是《婚禮圖》,主要流行于樂東、三亞、東方等市縣,是典型的人形紋樣,它將黎族婚娶禮儀習俗中的迎親、送親以及送彩禮和拜堂等活動場面織繡在筒裙上,描繪了新郎新娘和前來參加婚禮的眾多村民的畫面。反映了黎族的社會習俗與集體活動,其場面開闊,內容豐富,蔚為壯觀。而在臺方言地區的黎族圖案則以人形紋、青蛙紋居多。有學者通過對蛙紋形態研究后認為:“黎錦紋樣中,絕大多數‘人紋’實際是‘蛙人紋’,蛙紋、蛙人紋幾何紋樣的演變形成黎錦紋樣的‘菱形化’基本形,蛙紋及變形蛙紋占據黎錦紋樣的主要題材,是黎族紋樣的主體和靈魂”,原因在于:“蛙紋既源于原始圖騰崇拜,也是證明先民崇拜蛙圖騰的寶貴實物,是目前各民族織物載體中唯一傳承不斷的蛙圖騰的記憶遺存”。2在黎族人眼里,蛙是雨季的信奉對象,是主要圖騰崇拜物之一,美孚方言的黎族人認為蛙與水有密切聯系,能夠呼風喚雨,保證糧食豐收,因此蛙的紋樣與人的紋樣常常混合在一起。哈方言、杞方言和賽方言黎族婦女筒裙上由蛙形發展成的蛙形人紋最為常見,通常使用織錦、刺繡方式表現出來,較為典型。從中可以看出蛙形人紋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將蛙紋或者代替嬰兒的紋樣置于人紋的腹中形成孕母紋樣;第二種是將蛙紋方人紋的腿部下方組合成母子紋樣,與青蛙產子紋樣的概念相同;第三種是女子紋樣用轉換的手法,直接用蛙紋來代替女子的下本身,或在人紋的下腹部加一個蛙紋簡化的形式,來代表女性,用于表示崇生意識和民族繁衍的思想觀念。這些蛙紋樣是黎族早期社會蛙崇拜習俗的圖騰表現形式,它一方面體現出青蛙強大的生殖力,另一方面又具有非常明顯的儀式化特征,是一種典型的生殖崇拜。從圖形的結構上看,屬于異形同構,目的在于加強對物象深層意義的理解,展示相互間的含義,又利用物形的整合,達到傳達符號信息的視覺效果。

圖三
織繡上祭祀祖先的紋樣有潤黎方言區的較為典型。潤黎支系的婦女把“祖先”的形象設計成外形像一間船形茅屋,茅屋中央有個主體人形紋,在主體人形紋的腹、雙腿、雙臂等又套著體型較小的人形紋,小的人形紋中又套有更小的人形紋,層層疊疊,環環相扣,構成一幅飽滿的復合人形紋。構形方法是人與房屋的圖形同構。黎族人取意為:房子——父親——兒子——孫子(見圖四)。這種復合圖形的表現手法反映了黎族人濃厚的祖先崇拜意識。祖先一直是扮演呵護全村或族群興旺的重要角色,目的既是對祖先的敬仰,同時也期待能得到祖先的庇護,是一種祖先崇拜與圖騰崇拜結合的復合紋樣。美國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在《原始藝術》一書中認為:“在原始人的藝術中存在這兩種因素:一種是單純的形式因素,只靠形式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另一種是形式本身具有某種含義,在這種情況下,含義就賦予藝術品以更高的美學價值。”同時他還提醒我們:“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眾多民族的藝術品,從表面上看僅僅是單純的形式裝飾,而實際上卻同某些含義相關聯。”3因此,黎族的人形紋所表現的舞蹈、生產、生活、婚嫁等,都以此來表示族群平安與人丁興旺,這些無不打上濃厚的民間信仰的烙印。民間信仰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黎族地區由于長期處于原始宗教的發展階段,大部分地區仍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為主,其核心仍然是萬物有靈。在這樣的歷史積淀下所形成的傳統觀念、民族心理特征,在黎族織繡中人物圖形的大量出現并非偶然,正是這一民族心理特征的外在反映。可見,人物符號,也包括動植物符號成為了維系族群認同的一種有效方式和手段,具有團結血緣共同體和識別外族的作用。由于經過上千年的發展演化,又受到漢文化的影響,遂逐漸喪失了其原有的功能而變得世俗化,但其審美形式卻依然保留,代代相傳。

圖四
注釋:
1.見《人論》(德)卡西爾,李化梅譯,西苑出版社,2009.7.
2.見祁慶富.馬曉京.《黎族織錦蛙紋的人類學闡釋》[J].民族藝術,2005(1).
3.轉自孫海蘭《從黎錦蛙紋分析黎族的族源問題》[J]新東方,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