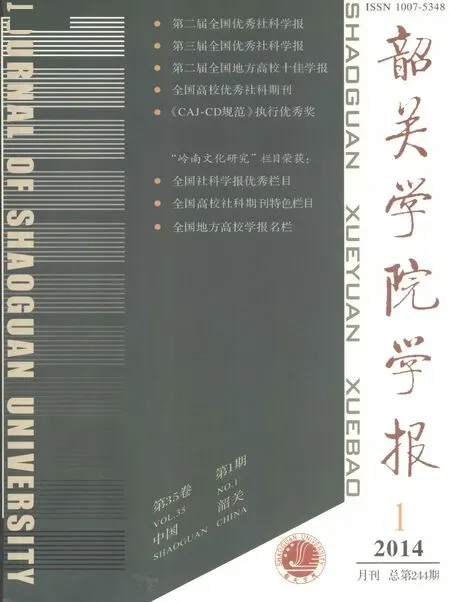關于音樂抽象本質的若干思考
鄧 青
(韶關學院 音樂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一直以來,對于音樂究竟是抽象的藝術還是具體的藝術這個問題,從未停止過爭論,各有各的理論依據。許多鼎鼎大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在論及藝術或美學問題時,都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認為藝術是具體的、緊密反映生活的。如賀拉斯的“藝術摹仿生活”理論,狄德羅的“美在關系”理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理論……這些觀點具有合理的成份。
但另一大批先賢,如柏拉圖、席勒、黑格爾等,卻認為藝術是抽象的(即理念的、先驗的、純粹的等觀點)!如席勒說:“在一件藝術品里,材料必須消融在形式里,軀體必須消融在意象里,現實必須消融在形象顯現里。”[1]100又說 “表現上的純粹客觀性是好的風格的特質,是藝術的最高原則。”[1]78這種觀點也有一定的道理,它符合人們的天然情感,排斥了過多的“意義價值”的功利色彩與沉重的哲學思辯,還原了音樂藝術本身的單純優美與精神屬性。
我們認為音樂由于其無形無蹤的聲波作為物質形態,一直是抽象性最強最徹底的藝術。雖以物質形態為基礎并作用于人的物質器官,有不容置疑的物質具體性,但在起源、創作、心理過程、審美及意義指向方面,只能且必然是抽象性的,否則就失去了音樂的本質美與大部分的存在價值,從一種純粹美感的精神活動與產物變成科技或實用性的東西。
為了更好地說明音樂的抽象本質,下面從幾個方面來詳細論述。
一、從音樂起源及歷史角度看音樂的抽象本質
從音樂的起源來看,其起源與目的并非預設,只為人類的精神愉悅而來,是人類的精神放出的火花。當人類第一次有了閑暇,不用為了填飽肚子整天奔波于叢林、草原,即在滿足直接生活需要而有余力時,才會進行自由的藝術活動。吹骨笛、在巖壁上畫出一只牛或在頭發上插上一朵花,都是無關于生存的活動之一,可算是人類精神活動或審美的第一朵花。原始人在吹響第一聲骨笛時,并沒有學習過所謂的理論、意義與音樂技巧,自然無法想像這骨笛聲會有什么意義;只是以有規律(間或無規律)的樂聲,以人類創造的區別于大自然的聲音,來愉悅自己、愉悅別人,這應是音樂的本原。所以從德謨克利特認為音樂并不產生于需要而產生于正在發展的奢侈(或余力),到近代類似的(席勒和斯賓塞)余力說,都明確指出音樂是超功利性與精神審美的結果。音樂從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具備了天然的抽象性。
從人類歷史角度來看,各種古代文明都曾將音樂放在極高地位,與巫術并列,是國之重器,參與重要的政治決策,就是利用了音樂的天然抽象性與神秘性所具有的力量,其原因有:第一,對音樂無形無蹤的形態不可捉摸與不能理解,且音樂的感受因人因時各有不同,呈現出極強的神秘主義色彩,非常符合當時對事物的神秘主義解釋,因此音樂被認為是上天或神的啟示,成為統治者有力的統治工具。第二,對音樂具有的能量的敬畏。音樂由于能與人的心理契合,能給予人愉快、悲傷、緊張、憤怒等感覺,能讓人安靜冥想,又能讓人激昂奮發。
音樂從誕生時的娛樂到巫到教化,隨著音樂社會功能的擴展,音樂從純粹的東西一步步變成復雜的載體,其實質是人的社會化程度的加深,是人的復雜化。
與此同時人類社會也走過了原始天真的階段步向文明,而文明的后果是復雜化、功利化與思辯色彩的濃重,離藝術的本原與魅力卻越來越遠。柏拉圖是西方最早主張管制音樂的思想家,這種主張曲折地反映了柏拉圖社會理想模式與秩序的思想;亞里士多德的看法與其師相同:“節奏與樂調不過是些聲音,為什么它們能表現道德品質而色香味不行呢?……因為節奏與樂調是些運動,而人的動作也是些運動。……音樂的節奏與和諧之所以反映人的道德品質,是因為兩者同是運動。音樂的運動形式直接摹仿人的動作(包括內心情緒活動)的運動形式,例如高亢的音調直接摹仿激昂的心情,低沉的音調直接摹仿抑郁的心情,不像其他藝術要繞一個彎從意義與表象上間接去摹仿,……從此可見,音樂的節奏與和諧不能單從形式去看,而要與它所表現的道德品質或心情聯系在一起來看的。”[1]221
正因為音樂的抽象性,先賢們意識到其解釋的近乎無限的可能性,才天然地最適合用于闡釋“道德品質”或“心情”此類抽象的概念。而為防止不合規矩的一切思想,必然且必須管制音樂。
需要指出,音樂具有很強的歷史時代特性,當然這并非音樂的本性,而是反映了該時代社會的好惡等情緒。例如得到全世界普遍好感的《藍色多瑙河》,在一戰前的中、東歐斯拉夫民族中就受到排斥。因為這些民族當時處于奧匈帝國的統治下,爭取民族獨立運動與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厭惡痛恨與奧匈帝國有關的一切事物,連本無國界民族之分的音樂也無法例外。又如,進行曲通常給人以奮發向上、斗志昂揚的感受,也常用來描寫年青人的朝氣與活力。一些優秀的進行曲都曾在人類歷史上起過重大的激勵人心的作用,如《馬賽曲》、《義勇軍進行曲》等。但在二戰后的歐洲,基于對戰爭的厭惡與慘痛記憶,很長時間內社會都非常排斥進行曲及類似進行曲的二拍子節奏。
人類歷史的積累與豐富,影響到每個時代每一個人。出生時純粹的個體,被高度復雜的社會所包裹、浸染,已不可能以單純或素樸的心態去聆聽音樂,自覺不自覺而被越來越豐富的意義、聯想所淹沒。以一個復雜的底印去面對音樂時,自然會認為音樂本身具備了各種各樣的意義與具體指向,而忘記了音樂本身的抽象性。
二、從音樂欣賞主體(即人)的角度看音樂的抽象本質
赫拉克利特認為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強調世界的變化與更新。面對藝術(包括音樂)沒有絕對永恒的美或評判標準,視不同歷史時期而有變化;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同一社會里,不同的個體也會造成審美口味與標準的千變萬化,所以休謨說:“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屬性,它存在于觀賞者的心里。每一個人心見出一種不同的美,這個人覺得丑,另一個人可能覺得美。”[1]440人的復雜,導致即使面對一個單純的事物,也會搞得復雜無比。音樂不過成了人的情感轉移與寄托物,起一種聯想的媒介作用,并不是音樂有什么具體性。
正是基于對人的復雜性的了解及音樂抽象性的清楚認識,才在不同歷史時期源源不斷地涌現出大量主張藝術(包括音樂)是抽象本質的思想家,并一直占據西方文藝思想的主流地位:以柏拉圖開創的理念說為淵源,歷經新柏拉圖的普洛丁(靈感說)——康德的美不帶概念的形式主義學說——德國狂飆運動的天才說(歌德、席勒等人為代表)——尼采的酒神說——柏格森的直覺說和藝術的催眠狀態說——佛洛伊德的藝術起源下意識說——克羅齊的直覺表現說——薩特的存在主義說等,這些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從中可以看出,面對復雜的人、神秘的心理與頭腦、無法解釋的種種文藝現象與事實,他們也無法得出一個具體化的、可精確度量的理論,只能訴之于抽象的近乎神秘主義的解釋,其中音樂因其無形無蹤的物質形態,表現得最為突出!
古代中國人常用音樂來表現與闡釋 “天道”、“禪機”,而領悟的多少與深淺,一切全取決于個人的修為與靈性,在形式與內容上也達到神秘、空玄與唯美的極致。這正是基于對音樂的抽象本質的深切領悟與運用。
終極的思考與哲理的冥想或許太高遠了,人們回歸音樂的抽象本質,就是為了回歸音樂的最初目的——娛樂(或游戲)!席勒說:“只有當人是充分的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1]139他明確指出了音樂所帶來的美的欣賞與愉悅,超越了低級本能與利害計較,產生游戲沖動,讓人手舞足蹈、放聲高歌或淺斟低唱,釋放精神與自由,縱情歡笑或落淚。
因此,從欣賞者的角度看,音樂的本質也是抽象的。
三、從審美的角度看音樂的抽象本質
社會越發展,人們的聯想越豐富;個人的水平學識越高,感受越復雜越豐富,但卻離理解與欣賞藝術之道越遠。就像老子所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也印證了佛所說的“著了形跡”或“著了相”。從審美的角度來看,這是最糟糕的現象。科技化與理性主義對藝術的侵蝕,讓人們忘卻了音樂的抽象本質。
古希臘的藝術成就達到人類史上的高峰絕非偶然,它所追求的“古典的靜穆”的理想境界與文藝審美觀,一直深受追捧與信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思想家認為“凝神觀照”是人生的最高幸福!無所為而為,在平靜中欣賞文藝自身所產生的樂趣,在靜觀默想中得到最高的快樂,文藝應表現出神的莊嚴、恬淡、靜穆,才能真正達到最高的風格與成就。
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認為藝術屬于審美范疇,要以直覺作為對待藝術的正確方法與態度。音樂作為一門藝術,須以不帶任何利害計較的心態去面對,追尋心靈的直覺與顫栗,獲得源自靈魂而非單純的感官滿足的審美快感。康德說:“審美趣味是對審判心境的普遍可傳達性的估計,它不是推理的結果,只是一種朦朧的舒適的感覺,具體表現為意識可察覺到的快感。”[1]78又認為“……自由的美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美,不以對象的究竟是什么的概念為前提。”[1]而英國哈奇生說得更清楚:“(音樂)在本原美項下可以列入和諧或聲音的美,因為和諧通常不是看作另一事物的摹本。和諧往往產生快感,而感到快感的人卻不懂得這快感是如何起來的,但是人們知道,這快感的基礎在于某種一致性。”[1]95
藝術需要擺脫一切才能獲得一切。擺脫的是日常繁雜的實用世界,獲得的是單純的意象世界。主張音樂的抽象本質才是正確的審美態度與方式。
以上從多方面闡明了音樂的抽象本質。主張并堅持音樂的抽象性,并非僅僅滿足于理論的爭辯,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有正確的態度與方式去創作音樂、欣賞音樂,專注于音樂形式本身的審美,忘記功利主義,獲取純粹的審美愉悅與心靈凈化。
[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