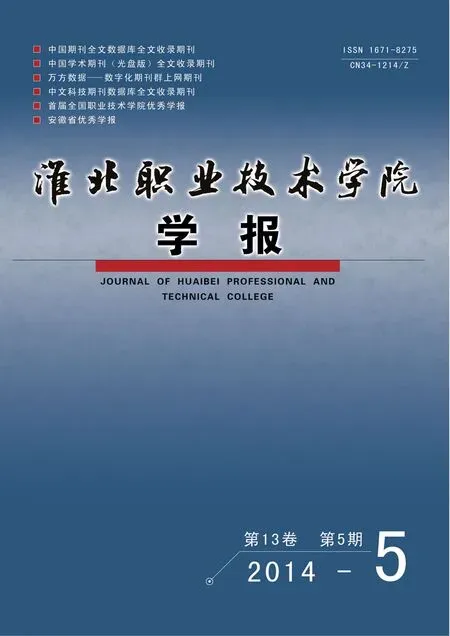向左走,向右走
——孔、莊思想觀照下的個(gè)人命運(yùn)
田婷婷
(淮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安徽淮北 235000)
向左走,向右走
——孔、莊思想觀照下的個(gè)人命運(yùn)
田婷婷
(淮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安徽淮北 235000)
孔子作為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哲學(xué)家,其理論作為我國思想文化的正統(tǒng),兩千年來深深影響著我們的觀念和生活。莊子作為道家學(xué)派的代表,以其博大的思想內(nèi)涵形成我國思想文化的另一主流,并且與孔子思想相互對立相互統(tǒng)一。這兩種思想各有利弊。而在這兩種思想觀照下的個(gè)人,在面對困境時(shí)如何取舍,已然成為一個(gè)微妙的難題。
孔子;莊子;處世;自處;個(gè)人命運(yùn)
個(gè)人存活在世界上,始終處在與世界對抗和與己對抗的困境中。如何處人和自處成為個(gè)人的永恒話題。孔子的思想體系注重人間秩序,注重倫理道德。他最終的目的是恢復(fù)古代禮樂制度,實(shí)現(xiàn)大同社會(huì)。因此,孔子關(guān)注比較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問題,也即如何處世。他對人類個(gè)體的關(guān)照也只是通過處理各種人際關(guān)系來實(shí)現(xiàn)。重視個(gè)人修養(yǎng)、超越自我也只是為實(shí)現(xiàn)太平的人間秩序而服務(wù)的,它只是一個(gè)起點(diǎn)。后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1]的儒家思想就是對孔子這一思想的直接繼承。“修身”的目的即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側(cè)重于教人如何處世,如何做一個(gè)好公民。而莊子的人生哲學(xué),其中心則是追求自我精神的自由,尋求自我解脫,它是直指本心的,側(cè)重于教人如何自處,如何做好自己。李澤厚把儒家所倡稱為“自然的人化”,即人的自然性必須符合和滲透社會(huì)性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把莊子所倡稱為“人的自然化”,即人必須舍棄社會(huì)性,使其自然性不受抑制才能與天地同構(gòu),才能恢復(fù)人的本性。[2]從此點(diǎn)可以看出,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社會(huì)性,莊子注重的則是人的自然性。社會(huì)性和自然性都是人的屬性,二者不能缺其一。只是在不同境遇之下,個(gè)人應(yīng)有所取舍,以應(yīng)所需。
一、孔子的人生哲學(xué)
在孔子的整個(gè)人生哲學(xué)中,個(gè)人總是生活在家庭、朋友、國家等種種人倫關(guān)系之中。個(gè)人的自我修養(yǎng)離不開他人的參與,只有與他人互相影響才能發(fā)展成為全面的個(gè)人。因而個(gè)人必須小心處理好在各種人際圈中的關(guān)系,所以要服從于各種社會(huì)規(guī)范。為此,孔子自己也設(shè)立了種種人際關(guān)系的既定模式。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論語·雍也》);“父母在,不遠(yuǎn)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3]等。由此可見,孔子眼中的個(gè)人要想超越自我必須具備和諧社會(huì)所要求的道德要求即推己度人及愛人等。個(gè)人的完善總是和完善他人同步或者在其之后。有些學(xué)者也把這種理論稱為利他主義。[4]無疑,這種種理論都能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和社會(huì)秩序。總之,孔子的人生哲學(xué)認(rèn)為個(gè)人的自我完善必須包含與他人的和諧相處即必須建立在成功的人際關(guān)系上,并將社會(huì)外在的規(guī)范化為個(gè)體的內(nèi)在自覺。為了獲得這種成功,個(gè)人不得不用種種道德條約和社會(huì)規(guī)范層層來包裝自己。“克己復(fù)禮”為其著名的宣言。個(gè)人為了服從種種社會(huì)規(guī)范和道德上的條條框框,有時(shí)越來越壓抑自己內(nèi)心真正的聲音,離自己的本心越來越遠(yuǎn),甚至?xí)斐晌笕?犧牲自我以討好別人的惡果。但人并不總是活在種種人際關(guān)系之中,人總有拋開一切其他的符號身份之后的本真自我。而如何面對赤裸裸的自我及其如何從自我對抗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孔子哲學(xué)似乎并沒有對此給予解答。
二、莊子的人生哲學(xué)
處在戰(zhàn)國時(shí)期的莊子,面對禮崩樂壞,戰(zhàn)爭頻發(fā)的社會(huì),深深感到現(xiàn)實(shí)的黑暗和險(xiǎn)惡。個(gè)人在社會(huì)時(shí)勢面前是如此渺小,以致不能掌控自我的命運(yùn)。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是如此殘酷和強(qiáng)大,而個(gè)人力量在其面前卻顯得十分單薄,這使莊子不再寄希望于拯救世界以使個(gè)人的境遇有所好轉(zhuǎn),而是直接觀照個(gè)人。莊子的人生哲學(xué)首先是針對個(gè)人的,他要實(shí)現(xiàn)的是如何在外部困境中解脫以實(shí)現(xiàn)真正的自我。他的整個(gè)思想是直指本心的,從關(guān)注社會(huì)轉(zhuǎn)移到關(guān)注個(gè)人的命運(yùn)上,涵蓋了對人類個(gè)體靈魂的安撫和精神的慰藉。《逍遙游》一文就淋漓盡致地詮釋了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有人認(rèn)為他所追求的這種絕對自由,這種不憑借于任何外物的理想狀態(tài)是無法實(shí)現(xiàn)的,屬于空想主義,因此是不可取的。其實(shí)不然。在文章中,莊子層層遞進(jìn)地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不同境界上的自由。從傳說中的大鳥鯤鵬,再到賢士宋榮子,神人列子,他們依靠外物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自由的境界也是不同的。越是依賴外物,越是不自由。他傳達(dá)的是對自由的渴望與向往的精神。這種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人生中是極其可貴的。在這個(gè)世界上,一旦有所寄托,必有所牽掛。而把情感理想寄托在外物上面,是最危險(xiǎn)也是最脆弱的。因身外之物往往不受自己控制,一旦出現(xiàn)變更,寄托有所失去,個(gè)人情感就極易受到影響。而完全無所寄托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應(yīng)適度地把心中的理想和情感有所保留地寄托在獨(dú)立于自我的客觀物質(zhì)上。
莊子教給我們的另一個(gè)人生哲理是如何對待“欲”。佛教理論認(rèn)為人生來就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是人的欲望。要想消除痛苦,必須去除一切欲望。人的生理本能有七情六欲,消除一切欲望是不可能的,因此佛教寄希望于來世。而莊子則不同。他認(rèn)為人的痛苦來自于人世間的種種紛擾,來自個(gè)人對于功名利祿的追逐。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斷地奔波勞碌。然而,欲壑難平,人的欲望總是不斷地出現(xiàn),追逐的腳步始終停不下來。身為外物所累,心為欲望束縛,令人動(dòng)彈不得,只能在自我精神世界中苦苦掙扎。莊子清晰地認(rèn)識到這一點(diǎn),并為我們實(shí)現(xiàn)個(gè)人的解脫指明了出路。那就是卸掉種種世俗社會(huì)的枷鎖,回歸自然。在莊子的哲學(xué)世界中,人與大自然是統(tǒng)一的,即天人合一。大自然無為,卻生生不息涵養(yǎng)萬物。人只有效法自然,才能擺脫種種束縛,回歸到生命最初的勃勃生機(jī)的鮮活狀態(tài)。他認(rèn)為人世間的道德、禮儀、功名利祿等一切“人偽”的東西都是對人的束縛,人們應(yīng)該拋棄這一切,坦率地做回本真的自我,融入到大自然中,才能與大自然合一,小我的痛苦才能漸漸消解,使得個(gè)人得以解脫。他的人格要求是真性情,摒棄一切形式和虛偽,將自我坦蕩地裸露在天地之間。而孔子的理論卻恰恰相反,使人至七十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人始終都活在“矩”內(nèi)而不得自由。
三、孔、莊對人生命運(yùn)的共時(shí)觀照
莊子并不是只注重個(gè)體封閉的生命狀態(tài)。他也意識到人不僅僅是個(gè)體的獨(dú)立存在,人還存在于社會(huì)之中。學(xué)會(huì)怎樣處世亦至關(guān)重要。他的處世哲學(xué)相對于孔子的更加具有彈性和隱性。“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齊物論》)[5]。莊子所處的社會(huì),顛倒黑白,是非不分。他見聞了太多忠貞義士被殺,他清楚地意識到個(gè)人的命運(yùn)在一個(gè)不合理的現(xiàn)實(shí)面前是飄忽不定的,保全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生命一旦失去,一切都將化為烏有。他的這種和光同塵的處世態(tài)度無疑是保身的絕好方法,值得我們深思。在如何保全自身這一問題上,孔子和莊子則不約而同地認(rèn)識到了歸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fā)也,時(shí)命大謬也。當(dāng)時(shí)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dāng)時(shí)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根深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繕性》)[6]“篤信好學(xué),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3]身處惡世,個(gè)人力量無力改變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時(shí),只好歸隱,以保全自己,孔子和莊子都認(rèn)識到了這一點(diǎn),這是他們相同的地方。
孔子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在立身處世中,要求人生不斷進(jìn)取,并且在進(jìn)取中絕不與現(xiàn)實(shí)相妥協(xié)。“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3],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tài)度造就了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和堅(jiān)強(qiáng)的品格。但是社會(huì)是獨(dú)立的外在于個(gè)人的,它從來不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變。有時(shí)個(gè)人命運(yùn)在世界時(shí)勢的漩渦中總是顯現(xiàn)出力量的單薄。總有一些現(xiàn)實(shí)是個(gè)人不可改變的,總有一些困難是無法克服的。而明明知道一些努力是徒勞的,為何還固執(zhí)于此呢?相比之下,莊子的人生哲學(xué)則更加靈活。他認(rèn)為人應(yīng)該順應(yīng)天命。《德符充》[5]:“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這并不是一種消極的悲觀主義。“德者“絕不是消極的無所事事,等待天命的安排,而是爭其必然,順其自然。《大宗師》[5]“得者,時(shí)也;失者,順也。安時(shí)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順著時(shí)勢的變化,隨機(jī)應(yīng)變而不固執(zhí)于一種行為,使人處在這個(gè)復(fù)雜的世界中多一種選擇,多一條解決困境的方法,既而在人生過程中減少一些阻礙和挫折。
四、個(gè)人抉擇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互相依賴互相補(bǔ)充。這種思想格局,自古以來促使無數(shù)知識分子形成外儒內(nèi)道的人格品行。當(dāng)處于人生高潮時(shí),采取孔子積極進(jìn)取的心態(tài);當(dāng)人生跌入谷底時(shí),采用莊子的達(dá)觀知命的心態(tài)。“得志于時(shí)而謀天下,則好孔孟;失志于時(shí)而謀其身,則好老莊”。[6]王夫之如此解釋這種外儒內(nèi)道的精神結(jié)構(gòu)。正是這兩種互補(bǔ)的哲學(xué)理論消除了個(gè)人在命運(yùn)起伏過程中的巨大的心里落差造成的極端的心理沖突與矛盾,使他們的心態(tài)趨于平衡。每個(gè)人不只有一面,當(dāng)面對不同的自我時(shí),應(yīng)用不同的哲學(xué)思想來對待。每種思想都不是完美無缺的,舉其一而遺其一,才能經(jīng)營好自己的人生。學(xué)會(huì)用這兩種思想觀照生命,才能在以后的生命路途中少一份不安,多一份從容。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 深圳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所.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xué)[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
[3]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 杜維明.儒家思想新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的自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5] 陳鼓應(yīng).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
[6] 王夫之.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M].北京:中華書局, 2009.
責(zé)任編輯:張彩云
B22
A
1671-8275(2014)05-0080-02
2014-06-29
田婷婷(1989-),女,河南商丘人,淮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中國古典文獻(xiàn)學(xué)專業(yè)2013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橹袊诺湮墨I(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