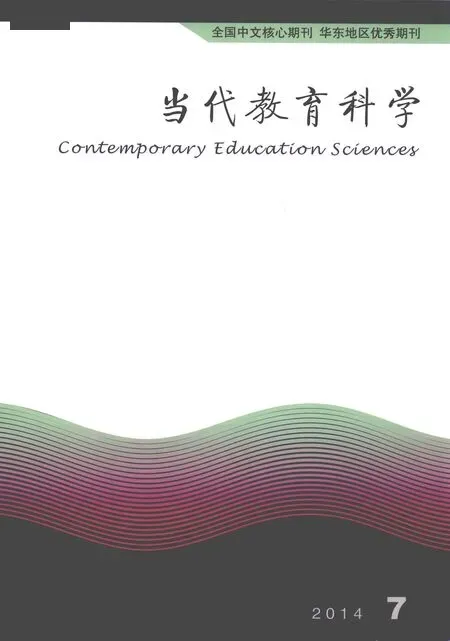價值與風險: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課程改革的影響透視*
●屠錦紅
價值與風險: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課程改革的影響透視*
●屠錦紅
后現(xiàn)代知識觀在當下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的學術(shù)語境中表現(xiàn)出一種較強的話語態(tài)勢。后現(xiàn)代知識觀以其獨特的意蘊,對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確實存有諸多的積極啟示。但后現(xiàn)代知識觀因其“出身”的時代背景與生存場域,注定了它對課程改革的影響并非總是積極的。須警惕:“不確定性”的混亂、“先設(shè)語境”的漠視、“實踐價值”的虛幻、“跨層越域”的脫節(jié)、“反科學知識”的陷阱。審視與估量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課程改革的消極影響,有助于我們在課程改革行動中提高警惕,自覺、努力地去規(guī)避各種風險。
后現(xiàn)代知識觀;課程改革;價值分析;風險評估
當前在我國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的學術(shù)語境中,并存著現(xiàn)代知識觀與后現(xiàn)代知識觀話語,但可以察覺的是,后現(xiàn)代知識觀似乎彰顯出一直較強的話語態(tài)勢。有學者就認為,后現(xiàn)代知識觀是我國當前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的主要理論基礎(chǔ)之一。[1]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課程改革的價值到底何在?其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有哪些?全面解讀后現(xiàn)代知識觀的價值,并估量其對課程改革的潛在風險,對課程改革而言頗為重要。
一、價值: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課程改革的積極啟示
(一)課程目標:超越知識,關(guān)照生命
現(xiàn)代知識觀強調(diào)課程的首要目標在于傳授各種科學知識,其潛在邏輯在于“科學知識是最有價值的知識”。在這種課程目標觀導(dǎo)引下,學生被迫追逐無窮無盡的知識,占有知識成為他們最重要、最緊迫的旨趣。長此以往,學校培育的學生很可能是一個個“單向度的人”,他們?nèi)狈Ω行裕儆徐`性。后現(xiàn)代知識觀宣告了科學知識是惟一真理這一神話的終結(jié),它把對人的關(guān)注放在了首位,不允許知識“異化”人,強調(diào)“意義和價值”不僅是世界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們的組成部分。……后現(xiàn)代科學必須消除真理與德行的分離、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倫理與實際需要的分離。[2]基于這樣的理念,課程目標首先應(yīng)體現(xiàn)的是對人之生命存在的全面觀照與關(guān)懷。教學不應(yīng)是一個逼迫學生侵吞知識的過程,而是一種培育“新人”的實踐活動,應(yīng)以發(fā)展學生的主體性人格為根本旨歸。要真正將人從知識權(quán)威中解放出來,不做知識的奴隸,要在知識的傳授與學習中尋求人的自由精神,尋覓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促使學生生命的和諧生長。
(二)課程內(nèi)容:包容經(jīng)驗,回歸生活
近代以降,以書本知識(主要是理性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范式一直占主流。這種教學最大的問題是容易疏離學生的現(xiàn)實生命,導(dǎo)致學習內(nèi)容與學生的個人經(jīng)驗脫鉤。后現(xiàn)代知識觀用知識的多樣性存在否定了現(xiàn)代知識觀對知識的單一性限定,讓建基于生活世界的各種知識大放異彩。為此,強調(diào)課程內(nèi)容的選擇不僅要關(guān)注科學世界,同時更要朝生活世界敞開。哈貝馬斯指出,“生活世界”是指交往主體通過以語言為媒介、以理解為目的的交往行為而形成的背景場所,是主體間以非對象化的參與態(tài)度介入的生活領(lǐng)域與動態(tài)網(wǎng)絡(luò)。它是由文化、社會和個人生活所構(gòu)成的知識結(jié)構(gòu)。[3]這是理想的課程內(nèi)容應(yīng)追求的基本圖景。科學知識,只是課程內(nèi)容建構(gòu)的一個維度,與此同時,課程內(nèi)容應(yīng)向廣闊的社會生活開放,使課程與社會現(xiàn)實保持密切關(guān)聯(lián);課程內(nèi)容還應(yīng)向?qū)W生生動的個人生活開放,尊重學生自我的體驗與經(jīng)驗,充分顧及學生的個人知識。總之,生活世界是課程內(nèi)容得以建構(gòu)的發(fā)源地,課程內(nèi)容惟有向生活世界敞開、與生活世界接軌與融通,方能體現(xiàn)出教育意義的真諦。
(三)課程結(jié)構(gòu):動態(tài)開放,多元互補
當“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成為一種時代信仰,學校教育對科學類課程的趨之若鶩便是一種必然的歷史現(xiàn)象。但這也引發(fā)了諸多的教育與社會的危機,譬如人文精神式微。人們不禁要追問:到底什么樣的課程結(jié)構(gòu)是適切的?后現(xiàn)代課程大師多爾對此開出的處方是構(gòu)建“四R”(即豐富性、回歸性、關(guān)聯(lián)性和嚴密性)課程結(jié)構(gòu)方案。其中“豐富性”這個詞,是指課程的深度、意義的層次、多種可能性或多重解釋。“為了促使學生和教師產(chǎn)生轉(zhuǎn)變和被轉(zhuǎn)變,課程應(yīng)具有‘適量’的不確定性、異常性、無效性、模糊性、不平衡性、耗散性與生動的經(jīng)驗”。[4]顯然,以“豐富性”構(gòu)筑的課程結(jié)構(gòu)應(yīng)該是動態(tài)開放式的。后現(xiàn)代知識觀所張揚的多元類型知識共存的思想,正契合了這種開放式課程結(jié)構(gòu)的理念。具體而言,后現(xiàn)代知識觀強調(diào),個人知識與公共知識、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等等,它們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構(gòu)筑了“豐富性”的課程結(jié)構(gòu)樣態(tài)。
(四)課程實施:彰顯民主,互動創(chuàng)生
現(xiàn)代知識觀認為知識是確定的、毋庸置疑的存在,教師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只能服從書本,學生在接受知識的過程中只能服從教師。從課程專家到課程計劃,從課程標準到教科書,從教師到學生,課程知識被逐層“精準”下移。這種自上而下、亦步亦趨式的課程實施策略,充滿了專制性與封閉性。而后現(xiàn)代知識觀認定知識本身是不確定的、動態(tài)的、建構(gòu)的,因此,真正的課程是教師與學生聯(lián)合創(chuàng)生的,課程實施本質(zhì)上是在具體的教育情境中創(chuàng)生新的教育經(jīng)驗的過程,既有的課程計劃只是提供經(jīng)驗創(chuàng)生過程選擇的工具而已。在后現(xiàn)代知識觀看來,課程是情景化的、人格化的,因此課程實施絕不是“按圖索驥”的過程,而是一個創(chuàng)造的過程。這有助于發(fā)揮師生的主體能動性,教師與學生都成了課程的開發(fā)者,成為構(gòu)建積極的教育經(jīng)驗的主體。課程實施的過程,因此也就成為教師和學生持續(xù)成長的過程。這種課程實施不是“被壓迫式”的,而是真正體現(xiàn)了教學的民主品性與人文關(guān)懷。
(五)課程評價:體現(xiàn)差異,注重情境
現(xiàn)代知識觀認定知識是客觀的、普遍的以及價值中立的,因此“答案惟一”的標準化考試便成為學校課程評價的主流方式、盛行方式。與此相反,后現(xiàn)代知識觀主張知識的文化性、境遇性以及價值介入性,這就決定了知識的獲得必將是千姿百態(tài)、千差萬別的,用一種評價取向來評定所有的學生必將是有失公允的。因此,關(guān)注個體、尊重差異、促進發(fā)展應(yīng)成為課程評價的根本取向。具體而言,在評價主體上,除了教師評價,還應(yīng)傾聽學生的聲音,要尊重學生的自我評價與相互評價。在評價內(nèi)容上,不僅要考察知識的工具性意義,還要考察知識的價值性意義,不能只看學生占有多少知識,更要看這些知識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學生的身心發(fā)展。在評價標準上,要擯棄評價的唯一性尺度,重點關(guān)注學生個體獲取知識的過程,尊重個體內(nèi)在感受,鼓勵探究發(fā)現(xiàn)。在評價方式上,要注重評價的情境性,要把質(zhì)性評價與量化評價和諧兼顧起來,使口頭的、書面的、操作的、實踐的、體驗的等各種評價手段互補互益。
二、風險: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課程改革的消極影響
(一)“不確定性”的混亂
“不確定性”是后現(xiàn)代知識觀的核心關(guān)鍵詞,它表明知識不是靜止不變的永恒真理,而僅僅是對開放的、復(fù)雜多變的現(xiàn)象的解釋和假設(shè)。為此,后現(xiàn)代知識觀主張為課程提供多種可選擇的解釋,倡導(dǎo)消解中心、多元視角、游戲化闡釋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培養(yǎng)學生質(zhì)疑與批判精神確實是有益的。但這種“不確定性”對課程實施的影響并非總是正向的。需要反思的是:如果課程內(nèi)容是不確定性的,那么,課堂教學什么?如果知識是不確定的,面對確定性的文本,師者何為?譬如,在語文課堂上,上《愚公移山》一課,學生多元解讀、批判質(zhì)疑的結(jié)果是——有學生說:“愚公真是太笨了,為什么不搬家?搬家多方便快捷。”有學生說:“愚公不僅愚笨,而且沒有公德,他在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應(yīng)該加以譴責!”有學生說:“愚公太殘忍、太霸道了,讓子子孫孫重復(fù)這件枯燥的事情,完全不顧他們的幸福。”[5]這不能不說是“不確定性”帶來的悲哀!教學從本質(zhì)上講,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實踐活動,一味地追求不確定性,從根本上講是背離教學內(nèi)在規(guī)定性的,這將導(dǎo)致教學似無根的浮萍,飄忽不定、難以捉摸。“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這一命題,恰恰揭示了“教學”之所以為“教學”——“教學生學”之基本意蘊。
(二)“先設(shè)語境”的漠視
后現(xiàn)代知識觀中的“后現(xiàn)代”一詞業(yè)已示明這一觀念產(chǎn)生的時代語境,即它是在西方后工業(yè)社會形態(tài)中萌生的知識學說。我們在直面后現(xiàn)代知識觀之際,切不可忘卻這一“先設(shè)”的語境。但令人焦慮的是,我們的理論家們,包括課改專家們,常常會深惡痛絕地把現(xiàn)代知識觀大加討伐,而在論及后現(xiàn)代知識觀時,筆下往往流露出過多的溢美之詞,而很少反省這一知識學說的生存場域。事實上我國當下的基礎(chǔ)教育存在的樣態(tài)異常復(fù)雜,“有以農(nóng)業(yè)社會為主導(dǎo)的教育(部分內(nèi)陸不發(fā)達地區(qū),特別是西部地區(qū)),有以工業(yè)社會為主導(dǎo)形態(tài)的教育(中部地區(qū))和以信息社會或所謂的‘后工業(yè)社會’為主導(dǎo)形態(tài)的教育(北京、上海、廣東以及沿海發(fā)達地區(qū))”。[6]即使在我國的發(fā)達地區(qū),后現(xiàn)代知識觀能否完全適合于指導(dǎo)課程改革,也依然是個需要慎思的問題,因為移植的理論與內(nèi)在的文化傳統(tǒng)會發(fā)生不同程度的沖突。后現(xiàn)代知識觀作為一個外域的理論,我們拿來絕不是為了檢驗異域的先進理論,從中演繹些我國的課程改革問題,而須立足我國的實情,基于“中國立場”,對其進行選擇性、揚棄式的濾收。如若漠視后現(xiàn)代知識觀的先設(shè)語境,無視我國多元地域的教育形態(tài),盲目地把這一知識觀奉為圭臬,則很有可能引發(fā)課改的“區(qū)域性”災(zāi)難。
(三)“實踐價值”的虛幻
由于我們一直深信,知識觀的轉(zhuǎn)變,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因此,在所謂現(xiàn)代知識觀向后現(xiàn)代知識觀轉(zhuǎn)變的歷史脈絡(luò)中,我們對后現(xiàn)代知識觀在課程改革中的實踐價值的認定,似乎很少質(zhì)疑。然而,“目前對于后現(xiàn)代知識狀況的研究多是在理論領(lǐng)域,并沒有進行多少實踐,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思潮雖然波及很廣,但是西方國家并沒有以此來指導(dǎo)本國的基礎(chǔ)教育改革。”[7]這確實須引起我們高度警覺。事實上,后現(xiàn)代知識觀在西方科學界和一般公眾中的影響是有限的,并且一直受到多方面的質(zhì)疑、責難。由于它“不正視和理解科學活動的一些樸素但卻基本的前提,就使它自己淪為一種純粹為了自圓其說、遠離科學實踐和社會生活的封閉的‘學術(shù)’觀點,因而缺乏現(xiàn)實的生命力”。[8]被稱為后現(xiàn)代課程大師的多爾其所謂的“四R”課程結(jié)構(gòu)模式,事實上頗為籠統(tǒng)抽象,缺乏實際操作性。我們很難奢望語焉不詳?shù)摹八腞”方案能給課程改革帶來多大的“行動”意義。欲基于后現(xiàn)代知識觀來建構(gòu)一個可操作的、具體的課程設(shè)計,看來多半是縹緲的鏡中月、水中花。可以斷言,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課程改革“實踐關(guān)懷”是乏力的。如若被其炫目的理論外衣迷倒,可能會把課程改革推向烏托邦。
(四)“跨層越域”的脫節(jié)
后現(xiàn)代知識觀是在哲學層面對知識的拷問,由此得出關(guān)于知識的若干假說。需要反思的是,作為哲學層面的知識假說,能否“直接”、“自然”地用來指導(dǎo)教育層面的課程改革?不可否認,知識觀與課程改革之間存有種種關(guān)聯(lián),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當談到這些關(guān)聯(lián)時,作為哲學層面的知識觀總是凌駕于課程改革之上,課程改革總處于被“說教”之中。有學者就指出:“現(xiàn)在對知識觀與課程關(guān)系的研究大多屬于一種單向的應(yīng)用研究,即立足于一定知識觀的假設(shè)前提來審視和改革課程。這造成了課程研究的被動”。[9]課程與課程改革有其自身內(nèi)在的規(guī)律,這種“內(nèi)因”是不允許任何外在的學說(包括后現(xiàn)代知識觀)僭越的。事實上知識觀本身并非自足的,也絕非自明的,它隨時代和思想家的改變而轉(zhuǎn)型。課程改革如何看待知識觀轉(zhuǎn)變的問題,“這要求教育首先要明確自己的性質(zhì),明白自身的目的和責任,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應(yīng)該什么是不應(yīng)該,從而知曉它要傳授的是何種知識,該接受何種知識觀的影響。”[10]而不能一味地跟隨知識觀的轉(zhuǎn)變而盲動。無論知識觀如何變革,課程改革均不可“隨波逐流”,它須有自己的改革邏輯。后現(xiàn)代知識觀的那些種種懷疑、否定、解構(gòu),也許在哲學層面有其充分的“批判性”價值,而一旦跨越到教育與課程改革層面,成為理論“基礎(chǔ)”,則很有可能導(dǎo)致應(yīng)然與實然的背離,致使理論與實際的脫節(jié)。
(五)“反科學知識”的陷阱
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尤為激烈,表露出一種“反科學知識”的傾向。波普爾就明確指出:“所有的科學都建立在流沙之上”。[11]這種“反科學知識”傾向,對于學校教育而言應(yīng)小心應(yīng)對。科學知識是人類精神的財富,它凝聚著人類在不斷進化中所進行的精神層面的艱辛努力與探索。雖然,既存的科學知識并非一定是科學真理,但人類在追求科學真理的過程中,首先得“知道”、“學會”既存的科學知識,這是難以繞開的。學校教育情境中,或許在科學知識的教學過程中存有一些問題,如教條灌輸、死記硬背、本本主義,這說明我們須改造科學知識傳授和使用的方式與態(tài)度,但并不代表摒棄科學知識。看看兩段歷史插曲:前蘇聯(lián)在20世紀20年代進行教育改革時,他們輕視乃至否定科學知識,以生產(chǎn)勞動取代課堂教學,結(jié)果導(dǎo)致學生整體素質(zhì)直線下降;而美國20世紀30年代受進步主義改革思潮的影響,他們也輕視科學知識,以兒童的生活及其經(jīng)驗來組織課程進行教學,結(jié)果導(dǎo)致教育質(zhì)量嚴重下滑。上述均是前車之鑒。事實上,布魯納早就警告過世人:杜威、泰勒以來的課程思路都是“反知識主義”的,而教育的真正“酵母”乃是“卓越性的觀念”,即科學家的知識結(jié)構(gòu)。[12]任何一個時代倘或宣稱已無需科學知識,那一定是很荒唐的。科學知識的傳授,無論如何都應(yīng)是基礎(chǔ)教育的基本使命與重要職責。
[1]胡志堅等.終結(jié)?抑或繼續(xù)?——對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成敗探討的哲學反思[J].教育科學研究,2011,(5).
[2][美]大衛(wèi)·雷·格里芬.馬季方.后現(xiàn)代科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95.
[3]嚴翅君等.后現(xiàn)代理論家的關(guān)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357-358.
[4]小威廉姆·E·多爾.王紅宇.后現(xiàn)代課程觀[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250.
[5]屠錦紅.中國閱讀教學的十年審視[J].教育學術(shù)月刊,2011,(8).
[6]朱成科.真實的“虛幻”與虛幻的“真實”——論中國比較教育學的學科邊界、價值定位與實踐尺度[J].外國教育研究,2005,(2).
[7]潘新民,張薇薇.必須走出后現(xiàn)代知識觀[J].教育學報,2006,(4).
[8]李志江.走出后現(xiàn)代知識觀[J].河北學刊,2002,(5).
[9]岳定權(quán).知識觀與課程關(guān)系研究的現(xiàn)狀與反思[J].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07,(6).
[10]翟楠.知識與知識觀及其演變的教育意涵[J].教育學報,2008,(1).
[11]Karl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M].London:Routledge,1962,34.
[12]鐘啟泉.課程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39.
(責任編輯:孫寬寧)
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guī)劃教育部重點課題“‘有效教學’視域下我國當代語文教育范式的審理與重建”(DHA120229)階段性成果。
屠錦紅/宿遷學院教育系副教授,南京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主要從事課程與教學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