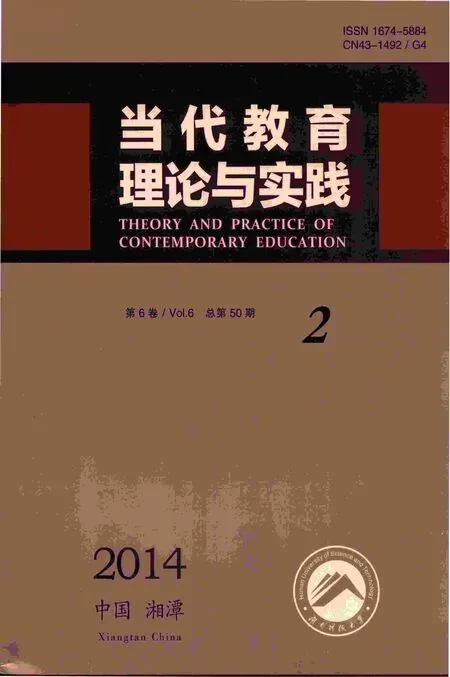《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的女性主義敘事策略*
李 婷
(湖南科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湖南湘潭 411201)
《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的女性主義敘事策略*
李 婷
(湖南科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湖南湘潭 411201)
林白的《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回顧林多米從5、6歲到32歲的經(jīng)歷,以元小說(shuō)的框架,自傳式的視角進(jìn)行女性自我獨(dú)白。小說(shuō)通過(guò)多變的敘述視角及對(duì)敘述時(shí)間的巧妙處理體現(xiàn)出女性主義小說(shuō)的形態(tài)。從敘事學(xué)角度來(lái)解讀這篇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作品。
《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女性獨(dú)白;敘述視角;敘述時(shí)間
1994年林白的長(zhǎng)篇《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在《花城》首次發(fā)表,以私人化的女性姿態(tài)給新時(shí)期女性主義文學(xué)帶來(lái)一股新潮。她以迥異于以往男性文學(xué)話語(yǔ)和主流文學(xué)話語(yǔ)的私人化敘事,為中國(guó)女性主義文學(xué)創(chuàng)作開(kāi)辟了新的道路。
1 自傳式的女性獨(dú)白
大多數(shù)女性主義作家都傾向于以自傳的形式進(jìn)行創(chuàng)作,她們用自傳式的寫作來(lái)剖析作為女性的獨(dú)特生命個(gè)體。她們?cè)谧詡魇降奈淖掷飳⒆约旱纳铙w驗(yàn)甚至是私密的情緒也寫進(jìn)去,向讀者們特別是讀慣了男性話語(yǔ)形態(tài)作品的讀者們展示了女性的生活體驗(yàn)以及女性的真實(shí)(隱秘)內(nèi)心。
“自傳是有關(guān)個(gè)人成長(zhǎng)或自我如何演變的故事”[1]82,《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以第一人稱敘事來(lái)展示女主人公林多米從童年到30歲左右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由于兒童時(shí)期父親的缺席和母親的無(wú)暇顧及,多米成為孤單的孩子。她習(xí)慣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她也會(huì)拉上同齡女孩玩性游戲。長(zhǎng)大后的多米還經(jīng)歷了詩(shī)歌抄襲、外出旅游遭誘奸、與女學(xué)生發(fā)生曖昧關(guān)系、與一個(gè)錯(cuò)誤的男人戀愛(ài)受傷后逃離愛(ài)情,最終來(lái)到北京工作與一個(gè)老人結(jié)合等事情。由于敘事是以第一人稱回顧性視角進(jìn)行,就形成一種明顯的自傳式傾向,特別是敘事中有許多關(guān)于剖析女性內(nèi)心的情節(jié),細(xì)致而隱秘,引起讀者以一種窺探敘述者隱私的心態(tài)去閱讀。
《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中某些情節(jié)確實(shí)能夠在林白的自述性小說(shuō)中找到相似點(diǎn),比如她在《前世黃金—我的人生筆記》中寫到:“我出生在一個(gè)邊遠(yuǎn)省份的小鎮(zhèn)上,3歲喪父,母親長(zhǎng)年不在家。我經(jīng)歷了饑餓和失學(xué),7歲開(kāi)始獨(dú)自生活,一個(gè)人面對(duì)這個(gè)世界”[2],這和多米的童年生活極其相似。可以說(shuō)林白把自己的童年移植到了林多米身上,使自己的經(jīng)歷在林多米身上重新演繹,使作品看上去是真實(shí)的。連林白自己也說(shuō)過(guò):“《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中的一些大事件是我真實(shí)經(jīng)歷過(guò)的。”事實(shí)上林白確實(shí)在做這樣的工作,將自己親身經(jīng)歷過(guò)的一些事件寫入文學(xué)作品中,而且大多數(shù)時(shí)候都是以第一人稱來(lái)敘寫,使作品與生活產(chǎn)生一種“互文性”,真實(shí)感特別強(qiáng)烈。
《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能成為一部典型的女性主義作品,不單單在其自傳性上,還由于它是一部女性的內(nèi)心自白書。小說(shuō)將女性的內(nèi)心、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敘述者甚至將自己私密的寫作狀態(tài)也公之于眾,這是以往男性作家或男性立場(chǎng)的女性作家所無(wú)法也不敢觸及的。少女時(shí)期就開(kāi)始的手淫、赤裸上身進(jìn)行私密創(chuàng)作、對(duì)女性身體的迷戀與窺視、與女子的同性戀情結(jié)、幻想著被強(qiáng)奸等等,敘述者把這些關(guān)涉私人隱秘的情節(jié)一一暴露出來(lái),從女性的視角觀察獨(dú)立的女性,而不是從男性的權(quán)威視角去建構(gòu)受統(tǒng)治的女性。
但是,林白創(chuàng)造的林多米畢竟不完全是她自己,小說(shuō)仍然必須是虛構(gòu)而不是完全紀(jì)實(shí)。林白在這部小說(shuō)中特別地運(yùn)用了元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美國(guó)批評(píng)家馬丁指出:“正常的陳述……存在于一個(gè)框架之內(nèi),而這類陳述并不提及這一框架。這類陳述有說(shuō)者和聽(tīng)者,使用一套代碼(一種語(yǔ)言),并且必然有某種語(yǔ)境,……當(dāng)作者在一篇敘事之內(nèi)談?wù)撨@篇敘事時(shí),他(她)就好像是已經(jīng)將它放入引號(hào)之中,從而越出了這篇敘事的邊界。于是這位作者立刻就成了一位理論家,正常情況下處于敘事之外的一切在它之內(nèi)復(fù)制出來(lái)。”[3]229我們可以簡(jiǎn)單理解,元小說(shuō)的作者會(huì)在敘述中把自己“敘述行為”本身講出來(lái),如果把小說(shuō)看作是一種虛構(gòu)的話,元小說(shuō)則是“關(guān)于虛構(gòu)的虛構(gòu)”。
元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的運(yùn)用會(huì)產(chǎn)生的一個(gè)效果就是,讀者能夠很明確地認(rèn)識(shí)到作者的寫作行為本身,而且這種行為是在虛構(gòu)一個(gè)故事。如果《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是一部自傳式的小說(shuō),讀者會(huì)不自覺(jué)地將林多米的世界與作者的世界進(jìn)行對(duì)照,認(rèn)為林多米就是林白。而事實(shí)上,林白不可能完全按照曾經(jīng)發(fā)生過(guò)的事實(shí)來(lái)書寫。元小說(shuō)的運(yùn)用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虛構(gòu)的世界,拉開(kāi)了讀者與人物的距離,而拉近了讀者與敘述者之間的距離,讓讀者隨著敘述者的視角去審視人物。在《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里,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句子:“現(xiàn)在我要告訴你去年夏天發(fā)生的一件事情”、“現(xiàn)在我們來(lái)說(shuō)多米”、“讓我回到母親和故鄉(xiāng)的話題上”、“讓我接著本章的開(kāi)頭,敘述我的路途”、“讓我們?cè)倩氐杰囌尽薄ⅰ白屛也暹M(jìn)第二個(gè)男孩的故事”、“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寫一個(gè)序,這個(gè)序使我回顧了過(guò)去,我也就不會(huì)想到要寫這樣一部長(zhǎng)篇”,……這些類似的句子不斷地提醒讀者,敘述者是在寫小說(shuō),不是在回憶生平往事。
并且,敘述者自己還會(huì)在敘述過(guò)程中懷疑自己敘述的可信性,來(lái)提醒讀者,這種所謂的自傳也不過(guò)是帶有猜測(cè)式的回憶,具有不確定性、虛構(gòu)性,形成一種“不可靠敘事”。比如說(shuō):“但那場(chǎng)大火把回憶和想像搞混了,我確實(shí)不知道是否真有一個(gè)北諾,除非她本人看到我的小說(shuō),親自向我證實(shí)這一點(diǎn)。”她也會(huì)強(qiáng)調(diào)“在這個(gè)長(zhǎng)篇里,我不能窮盡我的所有秘密。”將自己的經(jīng)歷進(jìn)行置換自然是虛構(gòu),而隱瞞一部分事情不說(shuō),同樣也是虛構(gòu)的一種方式:“真相是多么容易被隱瞞啊!只要你堅(jiān)決不說(shuō),只要不說(shuō)就什么也沒(méi)有發(fā)生,只要不說(shuō)就什么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堅(jiān)信沒(méi)有發(fā)生過(guò)什么事情,誰(shuí)(連你自己在內(nèi))又能找到證據(jù)呢?”
所以說(shuō)《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可以被當(dāng)做是女性真實(shí)自我內(nèi)心的展現(xiàn),但絕不能被稱作自傳體小說(shuō),正如陳曉明所說(shuō):“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實(shí)的女性獨(dú)白。”[4]
2 敘述視角的轉(zhuǎn)換——對(duì)女性的多向度審視
作為自傳式的女性主義小說(shuō),其視角限制在主人公身上,也就是女性身上。她們只關(guān)注、體驗(yàn)女性的生活,只探察、剖析自己的內(nèi)心,所以她們?cè)趯?duì)自己情緒、心理的描述時(shí)會(huì)非常細(xì)致、敏感,為探究女性的內(nèi)心提供廣闊天地。男性被退居幕后,作為女性眼中的觀察對(duì)象出現(xiàn)。他們有些甚至連名字都沒(méi)被記下,只能以代號(hào)的形式被保存。在這里男性不是社會(huì)的主宰,他們因?yàn)榕缘拇嬖诙嬖?他們只在女主人公的記憶中需要出現(xiàn)的時(shí)候出現(xiàn)),大多成為符號(hào)性的動(dòng)物或者背景。女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與其他人無(wú)關(guān)。《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正是用這種自傳式的第一人稱敘事強(qiáng)調(diào)女性的獨(dú)白,但是她又不局限于單純的內(nèi)聚焦的人物視角,而是有所變化,從多個(gè)角度審視女性內(nèi)心以及女性的行為,顯示出女性主義作品的獨(dú)特風(fēng)貌。
《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采用的是第一人稱回顧性敘事,必然要涉及到兩個(gè)敘事視角的問(wèn)題:第一個(gè)是“作為人物正在經(jīng)歷事件時(shí)的視角”,第二個(gè)是“作為敘述者正在回顧往事的視角”[5]102。這兩個(gè)敘述視角在小說(shuō)里面交替使用,首先一般作為人物的“我”—多米是故事內(nèi)敘述者、同故事敘述者,她直接參與到故事情節(jié)當(dāng)中,用她的眼光去看這個(gè)世界和世界里面的人,此時(shí)敘述者與感知者合二為一,都是人物—多米。如“我”與鄰居莉莉玩同性游戲、“我”在產(chǎn)房窗戶外偷看女人生孩子、“我”在鏡子里面看自己的身體等等。當(dāng)讀者隨著人物的視角去看其他人以及身邊的所有事物時(shí),讀者與敘述者的距離親密無(wú)間,這正是內(nèi)視角敘事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提供最真切的真實(shí)感。林白就是利用這樣一種人物內(nèi)聚焦的形式把女性的內(nèi)心、視野以最大的真實(shí)性展示給讀者看,這些被展示的內(nèi)容大多是男性作家或主流敘事無(wú)法做到的。
但是作為正在回顧往事的敘述者“我”——小說(shuō)“隱含作者”會(huì)經(jīng)常出現(xiàn)并且打斷作為人物正在經(jīng)歷的事件,她時(shí)不時(shí)地會(huì)跳出來(lái)對(duì)人物,也就是曾經(jīng)的自己的行為進(jìn)行評(píng)述:
現(xiàn)在離我寫作《日午》的時(shí)間又過(guò)去了幾年,我懷疑我從來(lái)沒(méi)有看到過(guò)姚瓊的裸體,那個(gè)場(chǎng)面只是存在于我的想像中。不管怎么說(shuō)……我希望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在一個(gè)同性戀者與一個(gè)女性崇拜者之間,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從這里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作為現(xiàn)在敘述者的“我”對(duì)曾經(jīng)的“我”迷戀女性身體的行為的懷疑與否定。這時(shí)的“我”是一個(gè)故事外的敘述者,是第一人稱的外視角。一般來(lái)講這個(gè)敘述者的視角是成人視角,與前面講到的人物參與式的視角不同,她總是顯得更加理性,會(huì)分析當(dāng)初種種行為的得失,也會(huì)介紹當(dāng)初行為的結(jié)果,當(dāng)然有時(shí)也起到為自己行為做辯白的作用。
小說(shuō)里還有一種情況,敘述者聚焦的對(duì)象雖然還是在女主人公身上,但卻使用了“她”或者以名字代替的限制性第三人稱敘述視角,此時(shí)感知者和敘述者發(fā)生分離—人物是感知者,但是敘述者凌駕于人物之上,她將讀者同故事、人物的距離拉開(kāi)了,形成一種“疏遠(yuǎn)型”敘述干預(yù)(前面那種可以被稱為“吸引型”敘述),敘述者完全處在異故事敘述層,仿佛所敘的人物和事件與自己無(wú)關(guān),人物成了“她者”。
比如在講到多米幻想著被強(qiáng)奸、被王姓男孩企圖實(shí)施強(qiáng)奸、與《四川日?qǐng)?bào)》的一個(gè)男記者交往、與矢村度過(guò)初夜那一段等等,都采用的第三人稱限制性視角,和其他地方的第一人稱內(nèi)視角敘事產(chǎn)生極大反差。雖然敘述者同樣是隱含作者,卻故意營(yíng)造了敘述者與人物、讀者與人物的距離感。對(duì)此可以有多重闡釋,第一是避免作者自身落入被直觀窺視的對(duì)象,畢竟這是一部帶自傳特色的小說(shuō),讀者閱讀這些一般人羞于啟齒、難以言說(shuō)的場(chǎng)景時(shí)也許會(huì)指向作者本人,造成對(duì)作者的不良印象。第二“是為了使其對(duì)這兩個(gè)性場(chǎng)景敘述更具備清醒的觀察功能,及讓作品中的敘述者作更客觀的自我反省。”[6]筆者認(rèn)為兩種考慮都可以成立。一方面這是許多作家包括男作家在自傳體小說(shuō)中常見(jiàn)的處理辦法,比如郁達(dá)夫在寫作《沉淪》時(shí)為避免讀者們將小說(shuō)主人公同作家自己對(duì)號(hào)入座而選擇了第三人稱敘事,同樣,我們可以理解林白在這部小說(shuō)中也作了如此的考慮。從另一方面講,距離的拉開(kāi)為更理性的審視提供了條件,畢竟小說(shuō)的目的就是剖析與審視女性行為、女性內(nèi)心,將女性世界公之于眾。用第三人稱的敘事能夠使敘事者站在一個(gè)更客觀的角度審視與反省人物的行為,轉(zhuǎn)換成第三人稱限制性敘事,既能對(duì)人物內(nèi)心進(jìn)行觀察,同時(shí)又保持了一個(gè)相對(duì)客觀的態(tài)度。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的視角變換非常頻繁,里面沒(méi)有整章的第一人稱內(nèi)視角或第一人稱外視角,更沒(méi)有整章都用第三人稱限制性視角。小說(shuō)里這三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而且在轉(zhuǎn)換時(shí)沒(méi)有非常明確的轉(zhuǎn)換標(biāo)志。加上元敘事的結(jié)構(gòu),使得整個(gè)敘事結(jié)構(gòu)復(fù)雜化,避免了單調(diào)的敘事給讀者帶來(lái)的審美疲勞感,而是帶來(lái)相對(duì)較大的閱讀“障礙感”與“新鮮感”,而且有時(shí)候敘述者和人物還以一種互相“窺視”的情形對(duì)話。這樣多種視角不斷轉(zhuǎn)換,敘述者和讀者都得以從多個(gè)角度審視女性心理和行為。
3 敘述時(shí)間的處理——私人回憶的跳動(dòng)
“敘述者在講述中往往有意打破事件的自然順序,按照敘事需要而進(jìn)行排列。因此,敘事話語(yǔ)中的時(shí)間是非線性的”[7],《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的敘事時(shí)間就是片段式、意象式的,“時(shí)間倒錯(cuò)”現(xiàn)象十分明顯,“敘述在過(guò)去、過(guò)去中的未來(lái)、未來(lái)中的過(guò)去與敘述主體此刻的現(xiàn)在之間往復(fù)跳躍”[7],頗有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風(fēng)范。從整個(gè)的敘事框架來(lái)講,這種自傳式小說(shuō)當(dāng)然主要是運(yùn)用倒敘的手法,如按時(shí)間順序敘述多米從童年到30多歲時(shí)的人生經(jīng)歷。然而如果僅僅是以林多米從兒童到少女到女人的自然時(shí)間順序來(lái)敘述多米的經(jīng)歷,只會(huì)引起讀者的厭倦,《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打破的線性時(shí)間,讓故事情節(jié)豐富起來(lái)。
以敘述者現(xiàn)在回憶這個(gè)動(dòng)作為起點(diǎn),我們可以把小說(shuō)敘述的事件分成各個(gè)時(shí)間段。首先小說(shuō)的主體是回憶的內(nèi)容,除去敘述主體此刻其他的都是回憶,基本用倒敘手法。但作者并不滿足于倒敘這單一的處理辦法,而是將時(shí)間切成一段一段,分散地排列在行文當(dāng)中,充分運(yùn)用倒敘、插敘、預(yù)敘等多種手段,將過(guò)去的事按照敘述者斷斷續(xù)續(xù)的回憶串起來(lái)。比如在第一章中主要是敘述兒童時(shí)期的故事,然而卻由8歲時(shí)對(duì)死亡的疑惑,插進(jìn)一段對(duì)在“我”21歲時(shí)認(rèn)識(shí)的北諾的介紹,這是從過(guò)去跳到了過(guò)去的未來(lái)。然而敘述者在講完北諾之后并沒(méi)有直接回到8歲的童年,而是進(jìn)入到敘述主體的此刻,懷疑起北諾是否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我”生命中,接著又?jǐn)⑹隽艘患叭ツ晗奶彀l(fā)生的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又是曾經(jīng)被“我”寫進(jìn)另一部小說(shuō)里的一件并不一定發(fā)生過(guò)的離奇事件。敘述完以后才又回到童年時(shí)期害怕天黑害怕鬼、幻想被強(qiáng)奸的情形。在幻想的情節(jié)中,作者又巧妙運(yùn)用預(yù)敘的手法,“這是多米在童年期想像的一幕,就像多米在幼年時(shí)所做的夢(mèng)到了成年之后往往有所對(duì)應(yīng)一樣,被強(qiáng)奸的幻想在她的青春期也變成一件真實(shí)而帶有喜劇性的事件。”將未來(lái)即將發(fā)生的滑稽事件預(yù)先告知了讀者,然而這只是一種概括的預(yù)告,引起讀者強(qiáng)烈的好奇心去挖掘那段往事。爾后作者就自然又轉(zhuǎn)到那件滑稽有愛(ài)的強(qiáng)奸事件了。
對(duì)事件發(fā)生順序的安排穿插,作者做的各種處理使得這部自傳式小說(shuō)的內(nèi)容無(wú)限地豐富起來(lái),這也再現(xiàn)了作為敘述者的一位“女性作家”回憶本身的片段性、意象性、跳躍性特點(diǎn),也正是女性在處理敘事時(shí)間時(shí)的常見(jiàn)手法。
在小說(shuō)的敘述過(guò)程中,作者還十分注重故事時(shí)間與敘事時(shí)間之間的關(guān)系,讀者閱讀時(shí)能明顯感受到時(shí)間節(jié)奏上的跳動(dòng)。敘事時(shí)間不可能與故事時(shí)間同步,必然是或快或慢的。在敘事上,作者刻意拉長(zhǎng)自我內(nèi)心活動(dòng)的敘述,又故意縮短甚至省略對(duì)男性的描述,以此來(lái)突出女性的主體地位。
比如敘述林多米小時(shí)候一次被迫與“肥頭”睡一張床的情形時(shí),林多米與母親女同事的對(duì)話是明顯的“零時(shí)距”,此處用的自由間接引語(yǔ)表明沒(méi)有完全“還原”對(duì)話,頂多算一種“再現(xiàn)”,也就是說(shuō)雖然是再現(xiàn)當(dāng)時(shí)場(chǎng)景,但絕不是完整的場(chǎng)景復(fù)述。有關(guān)“肥頭”這個(gè)男生的個(gè)人表現(xiàn)被完全“省略”掉,未著一字。“肥頭”當(dāng)時(shí)的表現(xiàn)是害怕、哀求?這些要靠讀者去揣測(cè)。這種省略是故意的,因?yàn)樽髡咭庠趶?qiáng)調(diào)在“我”對(duì)不得不與另一個(gè)人分享本屬于自己世界的小床所表現(xiàn)的不情愿,對(duì)作為男性的“肥頭”的不屑一顧,以及因“我”比“肥頭”有出息而生的虛榮感。所以在敘述林多米的表現(xiàn)時(shí),采用了拉長(zhǎng)敘事時(shí)間的辦法,強(qiáng)調(diào)“出息”對(duì)我的吸引力。
當(dāng)然這只是整篇小說(shuō)中一處小例子,還可以從其他的行文處看到作者的這種有意的處理。比如在林多米與N的戀愛(ài)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筆墨來(lái)描寫多米怎樣等待N以及等待時(shí)的種種焦慮與渴望的心情,她會(huì)將這種等待時(shí)間拉得很長(zhǎng),敘事時(shí)間明顯大于故事時(shí)間。然而對(duì)N的表現(xiàn)則用筆省之又省,讀者閱讀時(shí)也是一晃而過(guò),這一長(zhǎng)一短就造成了閱讀時(shí)的節(jié)奏感。從這種閱讀的節(jié)奏感中讀者也可以明顯感受到小說(shuō)的女性主體地位,男性只是陪襯物。
4 總結(jié)
可以說(shuō)《一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在敘事上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特點(diǎn),很好地展現(xiàn)了女性作家的寫作風(fēng)貌,展示以革命性姿態(tài)書寫的女性人物,對(duì)男性作家以及以男性話語(yǔ)為范的以往女性作家唱出了獨(dú)立之歌。
[1]華萊士·馬丁.當(dāng)代敘事學(xué)[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0.
[2]林 白.前世黃金-我的人生筆記[M].長(zhǎng)春:時(shí)代文藝出版社,2006.
[3]華萊士`馬丁.當(dāng)代敘事學(xué)[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0.
[4]陳曉明.不說(shuō),寫作和飛翔——論林白的寫作經(jīng)驗(yàn)及意味[J].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2005(1):23-34.
[5]申 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xué):經(jīng)典與后經(jīng)典[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6]葉志良,李 梅.敘述:1990年代以來(lái)女性自傳體小說(shuō)敘事的深化[J].麗水學(xué)院報(bào),2011(2):60-67.
[7]林崗.創(chuàng)立小說(shuō)的形式批評(píng)框架[J].暨南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1997(1):99-108.
I207.4
A
1674-5884(2014)02-0157-03
2013-10-25
湖南科技大學(xué)研究生創(chuàng)新基金項(xiàng)目(S130038)
李 婷(1990-),女,湖南醴陵人,碩士生,主要從事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
(責(zé)任校對(duì) 許中堅(ji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