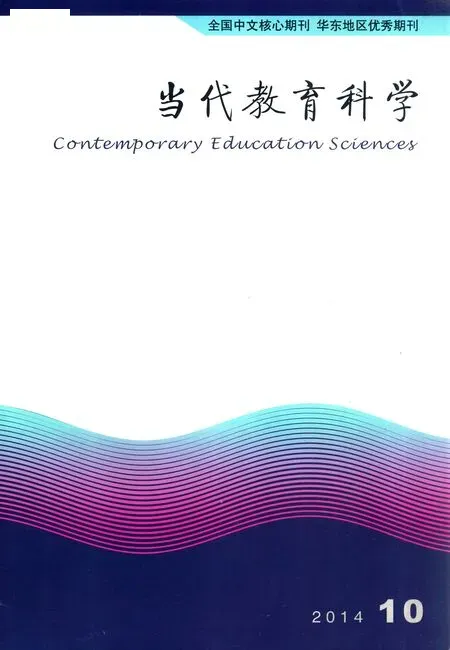教師為什么不愿意合作
——以學校場域中的教師慣習為研究視角
●潘婉茹
教師為什么不愿意合作
——以學校場域中的教師慣習為研究視角
●潘婉茹
學校場域由行政場域、教學場域等構成。每個場域的行為主體都有行使其權力的邊界,有著不同的慣習,形成了不同的行動邏輯。各種不同的思維活動和行為表現相互交織構成了學校的生態環境。適應時代對教育的要求,需要打破傳統的教師慣習,建立教師專業共同體。
學校場域;教師慣習;合作;專業共同體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Bourdieu)在建立“反思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活動中,提出慣習、資本、場域等概念,建構了公式(慣習、資本)+場域=行動作為,為解讀日常社會生活的行動提供了分析范式。布迪厄的公式同樣適用于對教育教學場域中的教育活動進行解析。本文試圖以學校場域的教師慣習為分析視角,通過對案例的剖析,解讀教師之間不合作的因素。
一、問題的緣起:教師之間的不合作
在S中學調研過程中,高一年級王老師向我們講述了令她煩惱不安的一件事。
臨近期末時,省里組織語文教學比賽,學校鼓勵全校教師積極報名參加,但主動報名的卻寥寥無幾,多次動員也不行。后來,教學校長、教研組長和備課組長集體商議“推選”新入職教師參加比賽(我也被推選參加比賽),需要老教師及備課組長組織前期培訓,講解參加比賽的注意事項,幫忙審閱教學設計、說課稿及講稿,參與試講并提出建議,當時這些教師口頭都答應了。但等我把教案設計出來,找相關老師幫忙時,他們總是借故推脫;另外兩位同事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拿著教案找到老教師,要么吃“閉門羹”,要么被敷衍。隨后,我們找到備課組長,請求解決,組長說她本人會給我們輔導,但對于其他教師不愿意輔導的行為也是無能為力。
S中學屬于市級(地級市)重點中學。各年級學科設有備課組,由學校各學科教研組負責管理。訪談過程中,幾位新入職教師對學校指令他們參加比賽一事,均表示了不情愿的心態。一位教師表示,“平時參加許多活動已經占用了我們大量時間。對于參加教學比賽一事,我們有熱情,但這次恰逢期末考試,參加教學比賽勢必會影響期末復習進度,影響班級的‘兩率一分’;老教師對我們參加比賽不予指導,我們可以理解,但心里確實委屈。”王老師提及的老教師也明確表明,“若在平時,大家都會盡力幫助這些新入職教師準備比賽的,都是從年輕時候過來的。自從新課改以后,我們對教材及考試命題的熟悉程度也大不如從前,學校又實行按成績發放酬金制,稍有不慎,原有的教學成績就可能保不住了。”備課組長表示,礙于領導的指示、自身的職責及學校的發展,只能推薦新入職教師不斷參與各級比賽,對于老教師的“不合作”行為也表示理解,他們也是因為害怕影響班級的期末考試成績才不愿意指導新教師。
二、因素分析:學校場域與教師慣習
在場域的界定上,布迪厄認為場域屬于相對自主的空間,具有自身法則的小世界。場域如同一個網絡,其間的行動主體會依照各自位置的存在狀況,以其所有的權力,形成特殊的客觀關系。學校作為社會系統的子場域,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小世界,有其自身的生存、發展邏輯和規則,成員依其慣習、據其資本類型及總量,展開不同的行動策略。
從具體操作的意義上講,如何分析一個場域?布迪厄認為至少有三個步驟。首先,必須分析所研究場域相對于權力場域的位置。每個場域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遵循著自己的邏輯和必然性,從關系主義的立場出發,完全自主和孤立的場域是不存在的。[1]S學校場域中,關涉教師的權力場域主要是由行政場域、教學場域構成。每個場域都有其權力行使的邊界,形成獨有的行動邏輯。行政場域中,權力體現為校長群體、職能部門、年級主任等工作人員對各種行政權力的把持;教學場域內,權力體現為教師的教學權力。在S學校場域中,行政場域處于核心位置,部分行政人員掌管著學校中各項資源的分配,如人事、財務、事務決策、評獎評優及教師職稱的晉升,維護著學校各項工作的正常運轉;部分身兼行政與教學職位的人員擁有管理教學場域的權力。教學場域的行動邏輯是進行正常的教學活動。教師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有著自己的權力空間;各學科教師在完成自己教學任務的前提下,還要接受學校行政場域的制約;擔任班主任的教師具有管理學生的權力和責任,同時協助相關部門的學生管理工作。此次“指令”新教師必須參加教學比賽就是行政場域權力行使的體現。同時,行政場域和教學場域又受共同的邏輯——學校的聲譽(主要是指每年的高考升學率,或重點大學的入學率)所制約。事實上,學校各場域之間的關系鏈條就是由學生成績(包括平時成績和高考成績)所聯接的。
其次,必須勾畫出場域中各個位置之間關系的客觀結構。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為了控制場域中特有的正當形式的權威,相互競爭和較量。由此發生的關系,制約著不同位置的行動者的策略選擇。[2]在S中學教師群體中,以王老師為代表的新入職教師無疑處于學校權力中最底層的位置,不具備任何行政權力,其話語權僅限于在教學場域內行使,在與學校其他教師及行政群體進行博弈時難免顯得蒼白無力,結果只能是“被推薦”或“被指導”。案例中的備課組長,由骨干教師之中選拔,不屬于學校的干部編制,也不具有所謂的行政干部身份,沒有正式制度的保護。工作職責一般是參加有關部門召開的學科教學培訓或會議;將會議相關精神和要求傳達給組內普通教師;制定本學科的年級教學計劃;組織組內教師集體備課或與教學密切相關的活動。他們對教師沒有任何制約性權力,但因具有與學校主管領導溝通的機會,比普通教師多一些獲得榮譽和晉升的可能,其位置有時成為教師之間競爭的目標。備課組長只能是建議新教師參加比賽,老教師進行比賽輔導。當老教師對新教師的求助不予理睬時,備課組長更多是無奈。此案例中的老教師深諳學校場域中的“規則”:高分是教師較好生存的唯一保障。更進一步說來,對于老教師而言,幫助新手教師審閱教案或指導教學比賽,雖有利于彰顯自己的價值,但與自己最直接的利益期待——提高學生成績無關,他們勢必會采取漠然與推脫的態度。
最后,必須分析行動者的慣習。慣習是“由持久的、可以轉化的性情傾向構成的系統,是結構化了的結構,可以發揮促結構化的作用。”[3]慣習是一種持久的傾向,具有創造、建構或再造性。對于行為個體來說,慣習是過去歷史的整合,源于家庭、團隊和階層。相似階層的人,通過相似的物質環境,能獲得相近的經驗,會促進某些行為規范的約束。[4]就行為群體而言,慣習不僅僅是個體的特質,更是一種規范群體的互動機制。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慣習的形成與場域里的社會位置息息相關,是對客觀位置的主觀調適。正如布迪厄指出的,“像科層組織這樣的社會集合體,具有一些內在固有的本質傾向,要維持它們的存在。這是一種類似記憶或忠誠的東西,就是行動者的慣習行為的‘總和’。這些約束深刻地存在于各種力量關系之中,這些關系構成了行動者參與其中的場域,構成了使他們彼此對立的爭斗。”[5]
教學場域與行政場域的行動者所具有的慣習不同,對同一事件思考與行動的視角注定也會不同。承擔授課任務的教師更多關注的是本班學生的成績,遵循的實踐邏輯是通過知識的傳授和持續的練習加強學生對知識的內化。教師的慣習是在學校依據“兩率一分”實施教學評估等組織行為的宰制下逐漸固化,形成隱性的競爭意識。其正面效應有激勵教師追求工作業績的一面,但負面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在調查中發現個別教師為了學生成績而發生言語爭執,傷害了教師間的感情,惡化了教師彼此間本應和諧互助的工作關系,教師與教師間的合作不能順利進行,教師專業發展嚴重受阻。
不同的行動者的慣習存在差異,每個行動者不同時期的慣習同樣會發生變化。備課組長就任組長之后,她的慣習也發生了變化。誠如她所言:換個角度考慮,自己若為普通新入職教師也不會主動參加比賽,與此同時,她對老教師的“不合作”行為也是持理解態度的。他們遵循著相同的實踐邏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及“一切為考試讓路”。對于教師而言,學校場域內的“分數之爭”是束縛他們的殘酷現實,久而久之,內化為慣習。進一步分析,鑄成“分數之爭”又源自學校場域運行機制的再生產,而這種機制的再生產又是高考目標實現的保證。在學校場域內,如果教師個體行為不會對學校利益產生重要影響,為自己帶來資本收益或者說教師個體需要為學校利益付出成本時,勢必采取回避或拒絕的方式。利己始終是行動者行動的最初邏輯選擇,不管場域中的人采取何種方式,可以說都是場域生存的需要。[6]
S學校場域之內,實現權力的是“類”科層制,具有科層制的表象和特征,兼糅了一些人文關懷的性質傾向。各個行動者要想在這個場域內生存并且更穩固或者相對好一些,必須牢記和遵循自己所處層次的行動邏輯。學生成績是決定教師權力位置和相互關系博弈的砝碼;高考升學率和優秀率決定著學校領導位置的牢固與升遷與否。這是學校領域中的行為目的和“總和”。也正是這些約束的“在場”,使得許多本應實施的行動(如參加教學比賽和指導新教師的教學活動)不得不回避和“退場”。
慣習之所以發揮作用,恰恰在于它的緘默性,不為人所意識且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是扎根在人們在場域內行為的模式,是時間結構和空間結構共同的產物,慣習的形成為行動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7]慣習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在同一場域中占據相同位置的個體行為人,會因受到相同制約因素的支配,形成相似的慣習(如S學校教師對考試成績的“狂熱追求”)。S學校的教師群體所持有的慣習就是在“強迫性”的壓力之下產生的,逐漸固化在各個體的實踐行為之中,在學校場域中沿著相對確定的軌跡表現和發揮出來的。
三、破解路徑:建立教師專業共同體
觸動S學校教師不合作問題發生的另一個因素是新課程改革推行后,學校的各項活動發生變化,反映到教學中最直接的就是學校的教材發生變化,老教師歷經多年教學實踐所形成的慣習特別是“教學權威”遭遇到了質疑和挑戰,他們開始為自己的教學成績“擔憂”,他們的專業發展也受到了考驗,故在自己的利益(學生的考試成績)與指導新教師參加比賽之間,選擇了前者。新課改帶來的這種“外來壓力”直接要求學校的教學場域進行變革,意味著必須打破傳統的教師慣習,改變舊有的教學模式和考試模式。
新課改的推行要求學校教師之間構筑“合作性”同事關系(collegiality),建立學習型“教師專業共同體”。構筑學習共同體,意味著基于競爭的、相互保守教學秘密的同事關系將要發生變化,合作與共享成為交往的主題。在我國中小學校中,教師專業共同體的日常形式主要表現為年級組和教研組兩種方式,還包括各種名師工作室、教師培訓團體等。我們不妨以年級組為例,說明教師專業共同體在促進學生發展,教師專業成長以及教師間合作的形成中的作用。教師專業共同體由年級學科召集人(非行政領導,而是具有號召力與學術能力的優秀骨干)、學科骨干教師及普通教師構成。有學者認為,理想的專業發展共同體的運作包括三個部分:設立教學計劃和備課計劃;有效的測試手段;借助測試結果進行練習。[8]所有教師在開學初,根據學校發展愿景,設立本學期本年級組的教學計劃。在年級組教學計劃確定的基礎上,依據學科特色來劃分不同模塊的具體任務,不同任務交由不同教師承擔;設定年級組備課方案,成立由處在不同專業發展階段的教師共同組成的備課小組,專門研究教材和設計教案;教材研究成果和教案在年級組間共享,以年級組為單位建立資料庫,所有教師根據自身及班級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可以將調整后的教案和教材分析增添入資料庫;在對學生進行測試時,年級組開會討論各學科考試范圍,使師生明確復習的范圍;測試結束后,教師分別搜集本班學生存在的問題,在年級組間討論匯總測試中存在的問題;根據反饋的問題,編制有針對性的訓練,這樣反復進行補充,利于年級組教學計劃的順利開展。這種方式可以使得處于職業倦怠期的老教師更多地參與到共同體中,在共同體中發揮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在運行過程,教師專業共同體的負責人需要采取措施保證共同體的順利運行,使每位參與者都能從中獲益(教師個體教學水平得到助益,學生成績得到提高);需要消解“成績”帶給教師的壓力,調動教師合作交往與共享的積極性。
僅是教學場域的獨自變革,缺少行政領域的共變,不會改變整個場域的共同邏輯。精英主義為取向的評價標準之下,學生的成績依然是決定性要素,因此社會觀念和學校教學目標的轉變是構筑共同體的前提條件。此外,召集人的學術魅力和組織才能是構筑共同體的要件。作為優質資源相對集中的學校,師資水平和人員素質較高,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師資力量薄弱的學校,又如何實施變革呢?作為其它參與變革的成員,如果個體對共同體的效用不認同,勢必會采取“敷衍”的方式進行合作。因此,教師和學校中人員的素質是構筑教師專業共同體的決定性因素,這也將是我們日后進行討論的課題。
[1][2][3][7][法]皮埃爾·布迪爾厄著.劉成富,張艷譯.科學的社會用途[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15,15,19,19-20.
[4]譚光鼎,王麗云等.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393.
[5][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33-134,185.
[6]馬維娜.退”場”主動:學校場域中的一種生存策略[J].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3,(5).
[8]許永華.學校變革:構建專業發展共同體[N].中國教育報,2008-2-5.
(責任編輯:劉君玲)
潘婉茹/吉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教師教育及課程與教學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