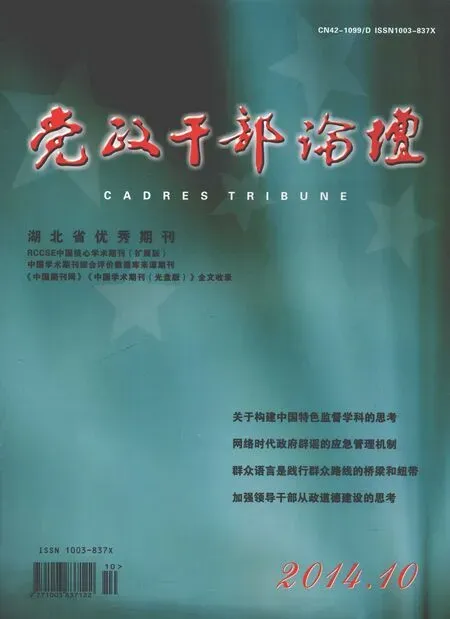我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力調整中的集權與分權——基于國家統治和管理效率的雙維度分析
○ 熊 燁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力關系調整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難點,中央和地方關系的任何一種模式——集權或分權——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權有利于樹立中央的權威,進而有利于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卻具有體制僵化和損害地方自由的危險;地方分權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發展,但卻有產生地方保護主義進而危害國家統治的危險。基于國家統治和管理效率的雙重目標,我國應該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限,并使這種權力調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過有選擇的集權和制度化的分權,構建相互合作和依賴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關系,實現集權和分權的平衡。
一、相關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了適應對外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需要,中央主動改革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引起的中央與地方經濟關系的調整,也不斷影響著社會主義傳統的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推動著傳統政治體制進行緩慢的調整和改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的調整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王紹光在《分權的底限》一書中寫到:“集權招人厭惡,如今是分權的時代,現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一個國家不高唱分權的調子。”[1]第三世界國家為擺脫經濟困境,紛紛搭上分權的快車。發達國家也不例外,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都采取了分權化的改革措施,有集權傳統的法國也開始了分權的實驗。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央與地方權力調整的思路是“簡政放權”,即把原先屬于中央的財權、投資審批權、利用外資權等權利下放給地方。“簡政放權”式的改革一方面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推動了現代化建設的進行,也增加了一些改革的動力。另一方面由于新舊體制的轉換磨合,地方分權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產生了政府財力分散、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宏觀調控能力減弱等一系列負面效應。在我國中央與地方權力調整的實踐中存在“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情況,集權與分權的選擇成為中央和地方權力調整的中的巨大難題。中央集權樹立中央的權威,有助于國家的統治,卻又限制了地方的積極性。分權給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行動空間,大大增強了地方改革發展的動力,卻又帶來了地方保護主義,地方惡性競爭,甚至阻礙中央的宏觀調控。
如何擺脫“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筆者認為,分權化改革引發的新問題,并不能徹底否定分權化的合理性,我們要跳出分權與集權的思維圈子重新審視我國的分權化改革,中央分權的前提要理清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邊界,沒有一個清晰的權限劃分,在改革中往往出現中央權力地方化和地方權力中央化的怪象。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權力的調整需解決的問題不是該不該分權,而是要理清哪些權力該集中到中央,哪些權力該下放到地方,在權力調整中有集有分,并使權力調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過有選擇的集權和制度化的分權,構建相互合作和依賴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關系,實現集權和分權的平衡。
二、集權下的危機
(一)集權可能導致決策過程的非理性化
由于集權者不可能全面掌握決策所需的信息,集權要么流于形式,要么隨意性,滋生官僚主義。決策者對各方信息的了解太粗疏,無法因地制宜,難以確保政策的科學性。當民主監督體制未建立或不健全時,集權體制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中央決策者權大無邊,卻不受他人制約。在這種情況下,一旦中央領導人頭腦發熱、決策有誤,很難加以制止,其危害性也比在民主的分權體制下大得多。許多決策失誤就是發生在集權體制上的。前蘇聯斯大林時期的“集體農莊”、“清洗政策”,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即是明證[2]。
(二)中央政府成為各種矛盾沖突的中心
權力和責任是一對孿生兄弟的政治現象,一定的權力必定連帶著一定的義務,集權下的中央政府掌握了過多的權力,也使其擔負起過多的責任。在傳統的中央集權模式中,中央政府包攬各種社會資源、經濟發展、百姓生計于一身。雖然擁有絕對的權力,但同時各種社會矛盾沖突亦集中于中央。中央政府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中心,這一結構造成了社會壓力集中于中央,加劇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裂痕,甚至導致雙方對抗的狀態。
(三)集權造成政府成本的高昂和管理的低效率
集權體制下往往出現中央政府什么事務都能管但管理效率低下的情況,政府掌握的資源有限,不可能承擔所有的事務,而對于一些必須由中央政府承擔的全國范圍內的事務,如擴區域的資源調配和環境保護等,中央政府卻又投入不足。而一些理應由地方政府負責的事務,如地方的治安、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等事務,卻因為地方政府財力的匱乏或自主性的缺失,無法有效完成。根據統計資料,從總量上看,我國的行政管理絕對支出增長較快,從1978年的49.1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5639.1億元,增長了97.5倍;從相對比重看,行政管理支出占總的預算內財政支出的比重從1978年的4.37%增加到2005年的14.25%,增加了9.88個百分點;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1.35%,增長到2005年的2.64%,增加了 1.29個百分點。按當年價格計算,行政管理支出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18.53%。我國的行政管理之處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重要的一點就是集權的體制下的低效率。
三、“簡政放權”下的困境
我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經過了多次的收權和放權,但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是以向地方放權為主的,對集權體制弊端的恐懼在理論界、政府官員、人們群眾中形成了一種誤解:認為改革就是放權讓利,就是減少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干預。比較典型的說法就是“改革就是簡政放權”[3],地方權力太小的呼聲,增加了地方政府不適當地對增加自身權力的預期,然而,事實上我國地方政府行使了很多不應該有它行使的權力,承擔了很多應該由中央政府及其職能機關獨自承擔的職責[4]。我國的“簡政放權”并非制度化的分權,在各個層級政府缺乏整體職能規劃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具有零和博弈的特點,一方權力的“得”意味著另一方的“失”。我國分權化改革存在著以下困境。
(一)中央政府權威下降
非制度化的分權讓利、新舊體制的并存以及配套改革未及時跟上等因素,造成中央政府權威削弱,宏觀調控乏力,使得中央政府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中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中央財政陷入困境,宏觀調控能力嚴重不足。分權化改革以來,地方財政凈上解收入占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1980年地方凈上解收入占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為32.2%,到1985年降為12.5%,1988年進一步降為10.8%。從198年實施大包干制以后,中央財政從地方財政每年新增加收入中,得到的份額僅是一個零頭,90%以上新增收入為地方所得。在這種分權化的制度框架中,中央財政收入既不能與國民經濟發展同步,也不能與財政增長總規模同步,其收入相對來說處是處于萎縮的不正常狀態[5]。
2.宏觀調控難以落實,中央政策失控。中央汲取財政能力是中央宏觀經濟調控的基礎,前者下降必定導致后者隨之下降。中央對地方的約束無力,地方向心力的發育與離心力的抑制失去了基礎和依托。中央財政陷入困境使中央政府失去可宏觀調控所必須的財力,導致國家財力的分散,削弱了調節地區間財力的能力。在分權過程中,一方面,中央政府的產業政策、貨幣政策、金融政策、投資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調控政策嚴重失控和失真,造成經濟上的大起大落,宏觀經濟不穩定。另一方面,由于財政借款與透資數額巨大,中央無力給予落后省份以財力支持,再加上“諸侯經濟”影響全國市場的統一,給全國協調發展帶來了重重障礙,這使得中央與地方關系呈現出新的不平衡狀態,嚴重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權威,造成國家能力的下降。
(二)地方政府的非正當利益行為膨脹[6]
在分權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扮演著地方經濟增長主要推動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也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在經濟的發展中往往以本地區的利益為重。地方政府的有些經濟利益行為超越了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全社會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非正當的利益行為。
1.追求預算最大化。官僚經濟理論認為,任何政府機構都具有專注于利益再分配和預算最大化的特點。地方政府對自主權力的追求導致其存在投資擴張最大化的沖動。追求預算最大化和投資行為擴張化交互作用,促進地方政府竭力開辟新財源:對上級政府想方設法證明本地條件差、困難大,跑“部”進“京”,爭取款項;金融體制的缺陷使當地銀行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分稅制實行后盡量少收稅多收費,或濫用減免稅政策。
2.本地利益壟斷化。分權化使地方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得到加強,這也為行政性壟斷創造了可能。以追求壟斷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地方保護主義日益猖獗。政府設立關卡,阻止本地緊俏的生產要素外流或外地優質商品流入;或對本地的“利稅大戶”實行特殊的保護政策,即使生產假冒偽劣的產品也大事化小;或動用司法執法力量為本地經濟”保駕護航”。從而加劇了地方的分割和相互封鎖,限制和阻礙了資金、資源、商品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使本來應該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市場,被分割成許許多多的塊塊[7]。
(三)擴大了區域間的差距
權力下放不均等所形成的梯度分權格局,拉大了區域間特別是東西部的差距。權力的下放向東南沿海一帶傾斜,使東部地區的發展速度較快,而西部地區,由于權力下放幅度較小,不像東部地區那樣享有較多的優惠政策,因而,其發展速度遠遠低于東部。權力下放的傾斜表現在一些地方享有特殊權力和優惠政策,例如,1980年頒布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合營企業盈利所得稅率為30%,并附繳納所得稅額10%的地方所得稅。但在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則減半征收,地方征稅也可由地方機動掌握減免。顯然,這就使得經濟特區和開發區的中外合資企業與其他地區的中外合資企業處于競爭的優勢地位。特殊權力和優惠政策在調動一部分地區的積極性的同時,抑制了另一部分的積極性,西部地區在看到東部地區享有那么多權力和優惠政策的時候,其積極性必定受到壓抑。分權的不均等在某種程度上導致資源配置和流向的不合理。由于東南沿海享有許多優惠政策和特權,使中西部地區的人才和資源紛紛流向東部地區,特別是經濟特區,雖然極大地促進了東南沿海一帶經濟的迅速發展,但卻使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的發展陷入了更大的困難,東西部的差距也越擴越大。
四、集權分權的均衡路徑
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各有其長處和弊端:中央集權有利于樹立中央的權威,進而有利于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卻具有體制僵化和損害地方自由的危險;地方分權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發展,但卻有產生地方保護主義進而危害國家統治的危險。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一定的集權是必要的,而要提高發展的效率,也必須需要地方的分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是否就是絕對對立的呢?并不如此。事實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都可以得到合理發展,例如,在英國等一些傳統分權的國家,其中央控制也十分有力。而在一些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地方政府也都擁有處理地方具體事務的某種權力。在我國當前的改革中,不應片面追求分權化,而應該尋求集權與分權相對平衡的途徑。
(一)合理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限
合理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限是實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集分平衡的前提,屬于中央政府的權力,一定要堅決地集中。屬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事務,一定要充分地放權。如同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凡屬全國性質的問題和需要在全國范圍內作統一決定的問題,應當由中央組織處理,以利于黨的集中統一;凡屬地方性質的問題和需要由地方決定的問題,應當由地方組織處理,以利于因地制宜。”[8]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限的劃分應以在堅決維護和保證中央的權威、強化中央調控能力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間的摩擦。在財權和事權的劃分上,應堅持事權相對分散、財權適度集中的原則。綜觀世界各國,不論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還是實行單一制的國家,都把財權控制作為對地方進行監督的重要手段。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在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都比較高,一般在50%以上,高的甚至達到70%-80%。地方財政對中央財政依賴性較大,地方財政的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中央的財政補貼、借款、貸款等[9]。我國在調整中央和地方關系時,也必須重視中央對地方的財政控制問題,進一步完善分稅制,改變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過低的狀況,逐步建立起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以提高中央政府的財政控制能力,對地方實行有效的監督。
(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調整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長期以來,各級政府的權力劃分是一種行政行為,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于中央政府或者上級政府的行政性授權,收權和放權都缺乏法律依據,收權和分權都由中央決定,集權——分權——再集權的現象反復出現在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調整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央下放給地方的權力,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沒有從法律的意義上加以保障。法國在中央與地方權力調整中充分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1982年 3月,法國頒布了《關于市鎮、省和大區的權力和自主權的法令》,法案明確規定,大區、省和市鎮三級地方議會除有權決定本級預算,決定本地區公共機構的設置,批準本地區經濟合同和社會救濟及經濟補貼的方案外,還有權處理教育、交通、城市規劃和住宅建設等法律明確規定的事務。而作為聯邦制的代表,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權限、職能在法律規定上涇渭分明、互不侵犯。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劃分的原則、內容、監督機制以及程序有必要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使之法律化規范化,以實現有法可依。一方面,用法律規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盡快修訂完善現行的組織法,制定《中央和地方關系法》等專門法,依法明確劃分各個層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職責權限。另一方面,用法律規范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程序和手段,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更改。
(三)選擇性集權和制度性分權相結合,構建相互依賴的中央和地方關系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只是整個政府體系的一部分,都不能單獨對整個社會起作用。中央再怎么集權,也不能沒有地方政府;同樣,地方政府再怎么分權,也不能離開中央政府。雙方都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我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調整不能制造權力與權力對抗沖突的機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不是依托各自權力進行利益博弈的關系而應該是一種合作和相互依賴的關系。我國的中央集權應該有選擇的有限度的,不能打擊地方政府發展的經濟積極性,而我國的地方分權應該制度化,地方政府的權力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內不至于損害中央的統治權威。有選擇的集權和制度化的分權是基于國家統治和管理效率的雙重目標下的選擇。
選擇性集權是指有選擇地把那些對國家整體利益至關重要的權力集中起來。只有通過選擇性集權,中央政府把應該屬于自己履行的職責切實履行好,把一些主要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才能增加中央的權威。只有在中央政府保持巨大的權威和合法性的前提下,才能推行制度化分權,沒有中央權威的分權,不是分權而是“分裂”。在選擇性集權的基礎上才可以逐步推進選擇性分權,一方面要克服分權的無序和混亂,中央政府的分權必須制度化規范化;另一方面,要使下放給地方的權力規范有效地運作,必須要有一定的制度支撐。這就需要我們完善我國的地方自治制度,提高我國地方政府行使權力的效率。此外,在中央政府的力量制度性后撤后,還需要發展地方民主監督和完善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監督制度,來規范和制約地方政府擴大的權力。
[1]王紹光:《分權的底限》,中國計劃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2][5]金太軍、趙輝:《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的建構與調諧》,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09頁。
[3]梁若晧:《改革就是簡政放權就是放開搞活》,《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4]周振超:《當代中國政府“條塊關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頁。
[6]張方華:《轉型時期地方政府非正當利益行為的有效控制》,《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7]薄貴利:《集權分權與國家興衰》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頁。
[8]《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頁。
[9]陳嘉等著:《各國地方政府比較研究》,武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