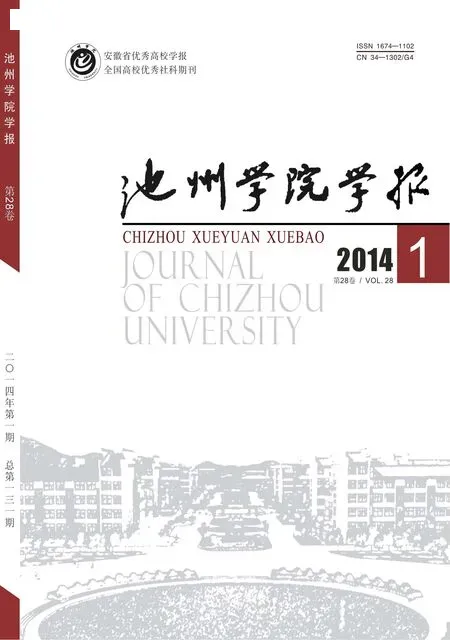何為“科學的研究精神”
——以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為例
李加武
(武漢大學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430072)
何為“科學的研究精神”
——以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為例
李加武
(武漢大學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430072)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科學的研究精神”主要體現為實事求是、善于懷疑、注重創新以及“為學問而學問”等四方面的精神。實事求是,主要體現為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擇取:在研究對象上,表現為“從書上求實”,“從事上求實”;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無征不信”的治學態度。善于懷疑的精神具體展開為兩個向度,即對研究對象和主體自身的懷疑:對研究對象的懷疑,集中表現為對古人之言和經典文本的懷疑和不輕信;對主體自身的懷疑,表現為“虛己”和破除“己弊”。創新的精神表現為實證的歸納法的運用。“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是學問能夠獨立,并得以發展的根本要素。
實事求是;懷疑;創新;“為學問而學問”
《清代學術概論》是梁啟超所著的一部以闡述清學源流為主要內容的論著,它也是我國首部系統總結清學史的專著。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氏認為,衡量一時代學術價值的根本依據是這一思潮代表的研究精神,而不是它研究的具體對象,“語一時代學術之興替,實不必問其研究之種類,而惟當問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謬者,則施諸此種類而可成就,施諸他種類而亦可以成就也”[1]158。其所以特重清代學術,即在于“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1]2。他認為后世應加以繼承和發揚的,正是這一精神:“今清學固衰落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勢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無所容其痛惜留戀,惟能將此研究精神轉用于他方向,則清學亡而不亡也矣”[1]9。他更將這一精神運諸《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中,在涉及自我評價的章節中,說:“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啟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啟超也。其批評正當與否,吾不敢知。吾惟對于史料上之梁啟超力求忠實,亦如對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1]3。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科學的研究精神”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
1 “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事求是”即“求真”,梁氏云:“可以知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獲。所謂研究精神者,歸著于此點”[1]160。他之所以特重戴震,將其作為清學的集大成者,即在于戴震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而“戴震之精神”即“清學派之精神”。他引述凌廷堪為戴震作事略狀的評語,“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也;吾所謂非,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1]55。這種以“實事”為依歸的治學態度正是清學的精神。
梁氏貶抑惠棟學派,認為其不足以代表清代學術,“茍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1]50,即因其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將惠派的治學方法概括為“凡古必真,凡漢皆好”[1]47,“夫不問‘真不真’,惟問‘漢不漢’”[1]49。所以,他將惠派理解為“純粹的漢學”,將其宗旨歸結為“凡學說出于漢儒者,皆當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則目為信道不篤也”[1]49。惠派“膠固、盲從、褊狹、好排斥異己”[1]49的習氣與清學實事求是的精神格格不入。這也是梁氏認為清學非漢學的理據。
“實事求是”的精神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選取上。梁氏認為,理學之所以遭清學之反動,即因理學的研究對象,“乃純在紹紹靈靈不可捉摸之一物”[1]12。致使“浮偽之輩,摭拾虛辭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禪’一派,至于‘滿街皆是圣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道德且墮落極矣。……其極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閉塞不用,獨立創造之精神,消蝕達于零度”[1]12。所以,清學啟蒙期諸大家對理學的反動,表現在研究對象上,即“從書上求實”,“從事上求實”[1]42,并具體展開為三種路徑:“其一,顏元、李塨一派,謂‘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劉獻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處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黃宗羲、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為根據,而推之于當世之務。其三,王錫闡、梅文鼎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此諸派者,其研究學問之方法,皆與明儒根本差異”[1]6。無論是從“書上求”,還是從“事上求”,都是學風“由空返實”的表現,也是“實事求是”精神的展現。
“實事求是”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無征不信”的治學態度。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年二十九始屬稿,五十乃成,無一日中輟”[1]36,自言:“舟車所經,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1]36。這種實證的態度正是“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也是“現代科學精神”的體現。清初大學者劉獻廷的治學經歷也體現了他“無征不信”的態度:“脫身遍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觀其土俗,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聞見,而質證其所學”[1]36。
梁氏對“實事求是”的精神持之甚堅,故對其師康有為也頗有微議,“時時病其師之武斷”[1]118,誠有“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之意。其云:“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于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1]118。在梁氏看來,“實事求是”乃治學的基本態度,也是構建堅實學術體系的根本要素。舍此徑路,更無它途。可見,“以實學代虛學”[2]乃清學的本質特點。
2 懷疑的精神
梁氏在評介戴震學術特點時說:“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茍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圣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1]52。對任何人,“不肯漫然置信”,“雖圣哲父師”亦在此列,“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此一治學態度絕類于近代唯理派哲學家笛卡爾“普遍懷疑”[3]的精神。
這一懷疑的精神具體展開為兩個向度,即對研究對象的懷疑和對主體自身的懷疑。對研究對象的懷疑,集中表現為對古人之言和經典文本的懷疑和不輕信態度,“必求其所以然之故”。這必然要求對研究對象層層追溯,不斷探尋其本。這也肇清學“復古”思潮之端:“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啟之”[1]9。以追求真理為最終目標,對一切成說均抱懷疑的態度,不盲從、不偏狹,這才能達致對舊思潮、權威的“解放”之實。可見,懷疑并不是最終的目的,而只是手段。
懷疑的最終目的是破除權威、解放思想、營造自由的學術氛圍、開啟科學的研究方法。這從梁氏對《尚書古文疏證》和《易圖明辨》兩書的重視,可窺一端。單從這兩本書本身的價值而言,誠不符如許之注目,“此兩書所研究者,皆不過局部問題,……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蕪雜,為后人所糾者不少。……阮元輯《學海堂經解》,兩書皆擯不錄”[1]20。然梁氏何故如此重視呢?這是因為,《尚書》作為六經之一,“千余年來。舉國學子人人習之,七八歲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視為神圣不可侵犯;歷代帝王,經筵日講,臨軒發策,咸所依據尊尚。……自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以來,國人之對于六經,只許征引,只許解釋,不許批評研究。……若對于經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議,便自覺陷于‘非圣無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網、憚清議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許作為學問上研究之問題”[1]20。而閻若璩竟將其作為一問題加以研究,非特“成為問題而已,而研究之結果,乃知疇昔所共奉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實糞土也”[1]21,這對于六經的權威,誠是毀滅性的打擊。“自茲以往,而一切經文,皆可以成為研究之問題矣”[1]21。其對于權威的破除,自由學術氛圍的營造,科學研究法的開啟,居功至偉:“后此今古文經對待研究,成為問題;六經諸子對待研究,成為問題;中國經典與外國宗教哲學諸書對待研究,成為問題;其最初之動機,實發于此”[1]21。“以吾儕今日之眼光觀之,則誠思想界之一大解放”[1]21。
胡渭《易圖明辨》的主旨是“辨宋以來所謂《河圖》、《洛書》者,傳自邵雍。雍受諸李之才,之才受諸道士陳摶,非羲、文、周、孔所有,與《易》義無關”[1]21。這似乎為一個局部的小問題,梁氏何故視之甚重呢?這是因為,“所謂‘無極’、‘太極’,所謂《河圖》、《洛書》,實組織‘宋學’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氣,言數,言命,言心,言性,無不從此衍出”[1]21。“渭之此書,以《易》還諸羲、文、周、孔,以《圖》還諸陳、邵,……而宋學已受‘致命傷’。自此,學者乃知宋學自宋學,孔學自孔學……學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謂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別有其途。不寧唯是,我國人好以‘陰陽五行’說經說理,不自宋始,蓋漢以來已然。一切惑世誣民汨靈窒智之邪說邪術,皆緣附而起。胡氏此書,乃將此等異說之來歷,和盤托出,使其不復能依附經訓以自重,此實思想之一大革命也”[1]22。《易圖明辨》的價值,正在于對權威的破除、對自由研究的開啟。
梁氏特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二書,即因“《偽經考》既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為劉歆所偽托,《改制考》復以真經之全部分為孔子托古之作,則數千年來共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1]120。康氏“雖極力推挹孔子”,然其將“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之創學派”[1]120,目為“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于諸子之列”[1]120。自茲以往,“所謂‘別黑白定一尊’之觀念,全然解放,導人以比較的研究”[1]120。同時,康氏排擊“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對于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以開自由研究之門”[1]8。這種對古人之言和經典文本的懷疑和不輕信,正是解放思想,開啟自由研究之門的基礎,也是科學研究的依歸。
懷疑的精神也體現為對研究主體自身的反思。蓋研究主體在具體研究過程中,或受已有知識、成見的影響,陷入先入為主之見中而不自知;或受特殊利益、目的的制約,影響了客觀的判斷。這特殊的利益和目的即“名”。戴震嘗言:“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見,其蔽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賢以附驥尾。……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為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1]52。……內在的成見和外在的名利都會影響科學的學術研究之展開,而如何達成“隨時以變,而皆不失于正”[1]28的客觀研究呢?其方法即在“虛己”[1]66。梁氏在總結王念孫、引之父子的治學方法時,云:“既獲有疑竇,最易以一時主觀的感想,輕下判斷,如此則所得之‘間’,行將失去。考證家決不然,先空明其心,絕不許有一毫先入之見存,惟取客觀的資料,為極忠實的研究”[1]66。這類似于荀子所說的“虛一而靜”[4]的功夫。而“虛己”只是一個抽象的原則,其體現為具體的功夫,并可運用于實際研究,即戴震所說的破除“己弊”之法。
梁氏認為,戴震的這一治學方法正是科學家的態度。因其尊重客觀事實和證據本身,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初得一義,未敢信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為近真焉,而憑藉之以為研究之點,幾經試驗之結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于十分,于是認為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為假說以俟后人,或遂自廢棄之也”[1]54。對客觀事實的尊重,對主觀成見的破除,正是戴震治學方法的精髓。
3 創新的精神
創新是文化發展的動力,也是舊學術思潮蛻變、衰落的根本因素。梁氏以佛教語“生、住、異、滅”來形容一期學術發展的四階段。而學術思潮由全盛期(住)進入蛻分期(異)的原因,即“(現有學術思潮的)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辟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于別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1]3。在這里,創新精神是一期學術由宏大敘事型的研究轉向“窄而深”的研究的內在動力。而學術思潮由蛻分期(異)進入衰落期(滅),其根本亦由舊思潮的代表人物缺乏創新精神,而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富有創新意識所致,“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后,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浚發無余,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杰之士,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1]3。如梁氏所言,“凡啟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范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1]15,正此理也。
以清學啟蒙期為例,其代表人物無不極富創新意識。梁氏概括顧炎武的研究精神為“貴創”、“博證”、“致用”。將“創新”作為炎武精神的神髓,這恐怕是顧氏成為清學正統派“不祧之大宗”的根本原因。顧氏特別反感晚明學風的獎勵虛偽、缺乏創新,其云:“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5]1037。他更厭惡時人著文的摹仿依傍,其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5]1060。又云:“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韓歐。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亭林文集·與人書十七》)因此,他對自己在這方面要求異常嚴刻,“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而后為之”[5]1046。其《日知錄》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5]1。梁氏對顧氏在此方面的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故凡炎武所著書,可決其無一語蹈襲古人。其論文也亦然”[1]16。
然新學術之開創,其尤為重要者,在新研究方法的建設。學派上之“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冥證”[1]11,從根本上都由研究方法決定。而清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建設,最顯著的就是實證的歸納法的應用。梁氏總結清學研究特點時說,“(清人)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1]70,“既立一說,絕不遽信為定論,乃廣集證據,務求按諸同類之事實而皆合,如動植物學家之日日搜集標本,如物理化學家之日日化驗也”[1]66。其中,搜證、比較即是歸納法的應用,而歸納的最終目的是獲得普遍性的“公則”。歸納法應用到具體的著書立說中,即“札記冊子”在清學者間的流行。梁氏云,“大抵當時好學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記冊子’,每讀書有心得則記焉。……推原札記之性質,本非著書,不過儲著書之資料,然清儒最戒輕率著書,非得有極滿意之資料,不肯泐為定本,故往往有終其身在預備資料中者。……夫吾固屢言之矣,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1]92。“札記冊子”當是歸納的“搜證”階段。另外,梁氏推重顧炎武“博證”的治學方法,亦因其是善用歸納法的典型,“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5]1。梁氏認為,“蓋炎武研學之要訣在是,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韻之學也,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音論》)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學的研究法。乾嘉以還,學者固所共習,在當時則固炎武所自創也”[1]16。其中,“近世科學的研究法”即實證的歸納法。而顧氏之所以成為正統派的“不祧之大宗”,根本原因就是他開創了實證的歸納法。
梁氏對歸納法的環節進行了細致地考察,并將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系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1]92。其中,第一步乃提出問題,確定研究的對象。第二步即搜集證據的階段,并將證據集中起來,加以概括歸納。第三步,在比較、歸納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普遍性的原則,以原則統攝零散的資料。第四部,在實踐中檢驗這一原則。如果原則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則成為“定說”;倘若不能,則棄之。梁氏認為,“凡今世一切科學之成立,皆循此步驟”[1]92,這也是他將歸納法稱為“科學的研究法”的緣由。
4 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
梁氏認為,大凡學術上要有所創獲,“皆當為學問而治學問”[1]71,“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1]159,這也是“真學者之態度”[1]71。如果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將學問作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則學問就不能獲得其自在的價值。故梁氏云,“其實就純粹的學者之見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與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獨立,不能發達。夫清學派固能成為學者也,其在我國文化史上有價值者以此”[1]71。學問能夠獨立的根本要素,即學問本身是目的,而非手段。
梁氏特重清學正統派“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1]6的治學態度,他說,“一,讀諸大師之傳記及著述,見其‘為學問而學問’,治一業終身以之,銖積累寸,先難后獲,無形中受一種人格的觀感,使吾輩奮興向學。二,用此種研究法以治學,能使吾輩心細,讀書得間;能使吾輩忠實,不欺飾;能使吾輩獨立,不雷同;能使吾輩虛受,不敢執一自是”[1]70。只有抱著“為學問而治學問”的態度,才能忠實于學問本身,才能拋卻一切私心成見、客觀深入地解讀文本,才能養成獨立的問學精神。而這一嚴謹的治學態度,又可使他人生“一種人格的觀感”,從而營造出良好的學術氛圍。
相反,抱著“經世致用”的目的以研究學問,往往導致學問的荒疏。他在評價章炳麟時,說:“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過其師,然亦以好談政治,稍荒厥業”[1]9。可見,將學問作為政治的手段,學問亦不得長進。他反思自己早期的治學經歷,“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1]8。在他看來,學問要獲得發展,必有賴于“為學問而學問”的人,“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1]160。
進一步,梁氏對“經世致用”的說法加以反思。何為有用,何為無用,本無一定之論。他說,“莊子稱‘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為用不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義也,則同是一學,在某時某地某人治之為極無用者,易時易地易人治之,可變為極有用,是故難言也”[1]71。可見,抱著“經世致用”心態的學者,似難逃狹隘、膠著的詬病,故云:“為學問而治學問者,學問即目的,故更無有用無用之可言”[1]71。
除了以上四點,梁氏認為促成清學繁盛的原因,還有以下兩點:
學者的道德。梁氏云:“茲學盛時,凡名家者,比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1]97。突出表現為當時的學者比較有責任感。他評價顏元,說:“其尊重自己良心,確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對于宋學,為絕無閃縮之正面攻擊”[1]32;他引用梅文鼎自述之語,曰:“吾為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后而后得簡易。……惟求此理大顯,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不憾”[1]36;他引用劉獻廷之語,云:“人茍不能斡旋氣運,利濟天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能謂之人”[1]38。這都是清人敢于擔當、獻身的“粹然學者態度”的體現。此外,清人以“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為不德”[1]70、“采用舊說而不明引之為不德”[1]70。正是由于以上因素,才使清學“創獲甚多”。以彼時反觀今日,梁氏認為,所應學者甚多,“將現在學風與前輩學風相比照,令吾曹可以發現自己種種缺點。知現代學問上籠統影響凌亂膚淺等等惡現象,實我輩所造成。此等現象,非徹底改造,則學問永無獨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學問社會以外。吾輩欲為將來之學術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鑒前代得失以自策厲”[1]160。
平等的問學精神。梁氏認為,較前代而言,“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1]7。這一氛圍為學問的自由交流提供了契機,“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1]70,“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1]70。這一氛圍也培育出學者獨立思考的精神,“凡屬學問,其性質皆為有益無害,萬不可求思想統一,如二千年來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學問不厭辨難,然一面申自己所學,一面仍尊人所學,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學風之弊”[1]162。正是這一“無國界、無主奴之見”的平等學術氛圍,造就了清學獨盛的局面。
[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0.
[2]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M].朱維錚,校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19.
[3]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M].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16.
[4]梁啟雄.荀子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294.
[5]顧炎武.日知錄校注[M].陳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章建文]
What“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Research”Is A Case Study ofAn Introduction to the Academic in Qing Dynasty
Li Jiawu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InAn Introduction to the Academic in Qing Dynasty,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research”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seeking truth from facts,spirit of suspicion,innovation,learning for learning.The main performanc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 method.The research object includes seeking truth from books and facts;th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attitude of no credibility without evidence.Spirit of suspicion includes a skeptical attitude to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esearcher.In the aspect of the research object,the main performance is skeptical about the ancient words and classic texts,and the researcher should keep an open mind and abandon one’s disadvantages.Innovation is the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induction.“Learning for learning”is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Spirit of Suspicion;Innovation;Learning for Learning.
C09
A
1674-1104(2014)01-0042-05
10.13420/j.cnki.jczu.2014.01.011
2013-11-14
李加武(1985-),男,安徽舒城人,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