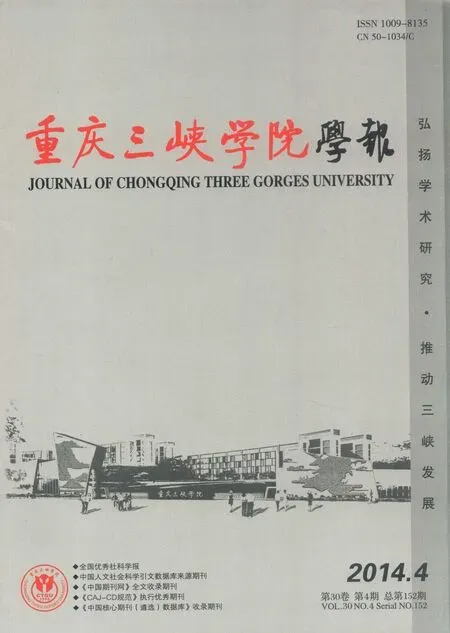淺論黃宗羲墓志銘“破體為文”現象
李愛賢
(蘭州大學文學院,甘肅蘭州 730020)
淺論黃宗羲墓志銘“破體為文”現象
李愛賢
(蘭州大學文學院,甘肅蘭州 730020)
黃宗羲打破墓志銘四言銘文的固定句式,在銘語中大量使用虛詞;改變墓志銘固定的寫作程式;在具體的寫作中運用了議論、抒情等手法;一改前人稱美不稱惡的寫作體例;在記敘墓主生前事跡的同時加入了對自我的強烈觀照。這些“破體為文”的做法,突破了墓志銘“用”的功能價值,提升了墓志銘的審美價值和文學地位,對后世的墓志銘創作具有借鑒意義。
黃宗羲;墓志銘;破體為文
一、破體
破體,原本是書法用語,是區別于“正體”而言的一種寫法,是對“正體”的突破和創新。唐代張懷璀《書斷》謂:“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云:“始從破體變風姿”[1]113。“唐李頎《贈張詩》有:‘小王破體咸支策’,小王指王獻之,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引徐浩語云:‘鐘(繇)善真書,張(旭)稱草圣,右軍(王羲之)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2]可見,在書法寫作當中,破體便是“小縱繩墨”,而使字體富有創造性。
在文學創作中,這種破體現象早已有之: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中說:“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聞類賦之貶。”[3]3313蕭齊時的張融也在《門律自序》中指出:“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常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吁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辣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4]729可見,張融自覺地突破文體限制,融各體之長,文章為世人所驚,收效甚好。這樣的例子很多,如錢鐘書《管錐篇》中:“名家名篇,往往破體,而文體亦因以恢弘焉。”[5]66周振甫《文章例話·破體》中:“破體就是破壞舊的文體,創立新的文體。”[6]213這些都是文學創作中破體的現象。
一般而言,自文體被劃分開來以后,一文一樣,每個文體大體上都有自己獨特的寫作規范、文體特征及用途。然而,一種文體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與其他文體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情況下完成的,正如吳承學所說:“在文體史上,各種文體的產生、發展和演變都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7]107后世很多作家在進行某種文體創作時,會不時地融入其他成熟文體的創作元素,打破文體原有的穩定性和固定創作范式,使文體表現出不同于原有文體的特點來。這看似是對原來文體的破壞,其實不然,因為“破體,往往是一種創造或者改造。不同文體的融合,時時給文體帶來新鮮的生命力。”[7]110在很多情況下,“破壞”也就意味著創新,這種“破壞”正是新文體的審美價值所在。
二、黃宗羲墓志銘破體為文的表現
明末清初的偉大思想家黃宗羲在進行墓志銘創作時也不自覺地運用了其他文體的一些表現手法,使得其墓志銘表現出新的氣象來。黃宗羲墓志銘“破體為文”現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黃宗羲的墓志銘打破了原有墓志銘四言銘語的固定句式,并在銘語中大量使用虛詞。墓志銘一般由兩部分組成:墓志和墓銘。“志”的部分就是序,多用散文記載墓主人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部分多用沉雅肅穆的四字韻語,以延續“志”部分的未盡之意,來表達對逝者的悼念和贊頌。而黃宗羲的很多墓志銘打破了墓銘固有的四字韻語句式,表現出靈活多變的特點來。如《唐烈婦曹氏墓志銘》三言銘語曰:“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冢,慎勿逸。”[8]272《瘦庵徐君墓志銘》中的雜言銘語是“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鑿腐朽以利刃。松耶柏耶,尚以利其后胤。”[8]237再如《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志銘》的銘語“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8]230整個銘語用雜句,靈活自由,使感情顯得自然充沛。黃宗羲的一些墓志銘銘語甚至出現了小說家的描述語言,如《時禋謝君墓志銘》的銘語為:“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于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磷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8]224通過鬼魅遇謝時禋也退避三舍的故事來表現時禋的忠孝之德。全銘語用散體語言,如講故事,讀之親切感人。黃宗羲墓志銘中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在此不多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銘語中還使用了大量虛詞,如“而”、“耶”、“兮”、“也”、“嗚呼”、“矣”等,這種現象是漢魏墓志銘中極為少見的,而黃宗羲有意這樣寫作,無疑是對原有莊重典雅的銘語的“破壞”。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論墓志有正體變體,說:“其為文則有正變二體。……又有純用‘也’字為節段者,有虛作志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9]149黃宗羲在其墓志銘中使用了虛詞,那么就是其墓志銘“破體為文”的表現。虛詞的使用,為原來固定四言銘語注入了新鮮血液,使文章情感更加抑揚頓挫。劉師培曾在《文章原始》中指出:“古代之初,虛字未興,罕用語助之詞,故典謨誓誥,無抑揚頓挫之文。”[10]8漢魏六朝的碑志文,尤其是銘文很少使用虛詞,文風顯得古板凝重。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肯定了文章中虛詞的使用,說“文必虛字備而后神態出”[11]9,就是說虛詞用得好,能使文章情感有聲有色,跌宕抑揚,收到尺水興波,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的妙效。如黃宗羲《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銘語曰:“采藥何許,侯潮山矗。日之出兮,以晞吾發;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闐闐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8]214中“兮”、“耶”等虛詞的使用,一唱三嘆,作者的悲痛悵惘之情娓娓道來,郁勃淋漓。
其次,黃宗羲改變了墓志銘的寫作程式。“程式本是文章各種組成要素按照某種特定規則組合起來的一種相對穩定的質,程式的變更與調整自然導致一種新質的產生”[12]21。傳統的墓志銘往往按順序依次敘述墓主姓名、里籍、先祖、行治(仕宦及行績)、卒葬(卒日、葬日、葬地、年壽)、子嗣,最后再寫銘文,而黃宗羲的墓志銘并沒有固定的模式。如《進士心友張君墓志銘》中作者開頭并沒有寫墓主的姓名、里籍,而寫張心友逝后,眾人含哀,哀心友張君“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8]186。隨后又寫時風眾寡,很多人醉心于科舉之業,而忽視科場之外的經世之業,表現其對汲汲于功利之學的不滿。而后才將筆觸轉向墓主,寫其生平事跡,一生成就,最后寫卒葬年月、子嗣,再寫墓銘,表達哀悼和贊頌。再如《敬槐諸君墓志銘》,在文章之始,作者并未提及墓主諸敬槐,而是就用細膩的筆觸回憶甲寅之年,群盜滿山,自己和耄耋老母顛沛流離,寄住在諸來聘(諸敬槐之子)家之書室后與敬槐家人的融洽生活,文章中間才寫及墓主姓氏、生平事跡等有關墓主的信息。另外,如《李杲堂先生墓志銘》、《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銘》、《萬充宗墓志銘》等文章,都打破了常規墓志銘的程式,是黃宗羲有意打破文章之體式而“破體為文”。黃宗羲的很多墓志銘都一反常規寫法,信手拈來,意到筆隨,完全沒有碑版之文死氣沉沉的跡象。
再次,黃宗羲在墓志銘創作中善于運用議論、抒情等多種手法,也是其墓志銘“破體為文”的表現。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論墓志有正體變體:“其為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9]149方苞《古文約選》中評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時云:“墓志之有議論,必于敘事纓帶而出之。此篇及王深甫志則全用議論,以絕無仕跡可紀,家庭庸行又不足列也。然終屬變體,后人不可仿效。”[13]3994議論手法融入到墓志銘創作當中,打破了墓志銘常規死板的敘述,屬于墓志銘的“變體”。因其相比于原體有所突破,被視為破體。黃宗羲的墓志銘,以敘事為主,以議論為輔。如《鄧起西墓志銘》,作者首先寫起西舉鄉試,以母喪不去,母喪之后任不仕之事;接著寫起西為師守喪之事,隨后寫作者避居讀書,起西跋山涉水來訪黃宗羲一事。而在文章之末,作者大發議論曰:“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于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于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于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即鄧牧、張雨,亦不愿為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8]216-217通篇有三分之一都是議論,籍以表達自己對不得志時逃往釋氏之人的不滿和對鄧起西苦身持力,守其師說,無愧師門的贊揚。該議論大氣磅礴,振聾發聵,耐人尋味,頗具雜文風格,亦是破體之表現。
黃宗羲很注重文章的抒情性,他在《論文管見》中說:“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志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8]481可見,文章不僅以理為主,如果忽略了情的存在,那么文章也不會打動人心。黃宗羲的很多墓志銘中都蘊含著濃濃的深情,如《敬槐諸君墓志銘》中“來聘求余志墓,余初辭之。念少時意氣奔放,離別都不在心,亂后瘁于哀傷。吳霞舟先生舟中別我,余行二十里,先生復掉三板送之,嗚咽濤中;沈眉生書尺往來,紙有淚痕,舟發虞山;鄧起西立忠烈祠邊,涕淚交下;陳錫公來學,去之日,手巾拭面,而淚不能止,其臨水黯然者不在此數。清風朗月,思之不可為懷。君河渚之淚,如何消破?因援筆為之銘。”[8]194君子之間情深意切,臨風送別,涕淚交流,讀來凄楚蘊藉,感人心脾。念及敬槐先生當年“老淚縱橫,徙倚河渚”[8]193送別的情景,百感交集,不能釋懷,遂提筆為之屬銘,悲涼可涕。
再次,不虛美,不隱惡也是黃宗羲墓志銘“破體為文”的表現。墓志銘往往是受人所托而作,一般情況下稱美不稱惡,其意圖在于表明孝子賢孫的心意,樹立家門風范,宣揚家族的鴻威懿德。劉勰在《文心雕龍·誄碑》中道:“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14]128因此,在后來墓志銘的創作過程中,稱美不稱惡已經成為一種慣式。然而,黃宗羲在墓志銘中卻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虛美、不隱惡。如《高旦中墓志銘》中毫不避諱,說:“蓋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于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亦未必純以其術也。”[8]147又言“日短心長,聲名就剝”[8]149。有人建議他可以將上面的語言稍加修改,使其變得圓潤不尖銳,而黃宗羲執意不改,并說:“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為法,寧不喜于今人,毋貽議于后人。若鄙文不滿高氏子弟之意,則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損;尹氏銘文,其家別為墓表。在歐陽公且不免,而況于弟乎?此不足道也。”[8]462黃宗羲個性剛正不阿,即使高氏子弟請求其修改鋒芒,但還是堅持“其人行應銘,法則銘之;其人行不應銘,法則不銘”[8]461的原則,直書不隱。黃宗羲墓志銘有褒有貶,打破墓志銘稱美不稱惡的定式,則亦是破體。
最后,黃宗羲墓志銘還表現出了強烈的“自我觀照”意識,這也可視為其墓志銘“破體為文”的表現。傳統墓志銘都采用第一人稱的限制視角,一般都是“外審型”,即“‘我’視‘人’”的敘述視角。而限制視角有多重內涵,如還有“內省型”即“‘我’視‘我’”的視角。黃宗羲的墓志銘敘事視角特點不但表現出傳統的“‘我’視‘人’”的敘述視角,更表現在“‘我’視‘我’”這種視角上的靈活運用。如《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銘》中黃宗羲之所以對東林之后魏子一先生推崇備至,是因為魏子一先生尚經世、務博學,對當時房社、科舉之業不屑一顧又自視甚高,正是黃宗羲所推服的豪杰人格。魏子一好尚旁通藝事,自然是不拘一格之人物:“顧子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于天子,銳意問學,遠駕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里。加之旁通藝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楊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絕妙,一時盛名,無處其右。……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發交游,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昆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8]198從上述這些話我們可以得知,黃宗羲主要寫魏子一其人其事,并對魏子一評價甚高,然最后的“余束發交游,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昆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8]198卻暗含著黃宗羲對自己的定位,也包含著黃宗羲以豪杰人格自許的潛在意蘊。
三、結 語
黃宗羲堅持大體須有,定體則無的宗旨,“破壞”了墓志銘四言銘語的固定句式,并在銘語中大量使用虛詞;改變了墓志銘固有的寫作程式;在墓志銘創作中融入了議論、抒情等散文常用的表現手法;一反前人稱美不稱惡的墓志銘寫作慣式;在寫墓主其人其事時隱含著對自我身心的強烈觀照。這些新的突破,使黃宗羲的墓志銘表現出獨特的審美價值。黃宗羲的這種“破體為文”的做法,一改墓志銘只有“用”的功能[15],突破了墓志銘原有的創作藩籬,提升了墓志銘文體的審美價值和文學地位,對后世墓志銘創作和批評提供了借鑒意義。
[1]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曾棗莊.中國古典文學的尊體與破體[J].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64-65.
[3][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下)[M].北京:中華書局,1958.
[4][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張融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2.
[5]錢鐘書.管錐編·全漢文卷十六(補訂重排本)[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6]周振甫.文章例話[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7]吳承學.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8]黃宗羲.黃梨洲文集[M].陳乃乾,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9][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M].羅根澤,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10]王鍾陵,主編.彭黎明,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文精粹·散文賦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清]櫆劉大.論文偶記[M].郭紹虞,羅根澤,主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12]侯吉永.韓愈破體為文論——以其碑志文體為中心[D].河南:河南大學,2006.
[13]王水照.歷代文話[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14][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注釋[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5]汪悅.北宋婦女的婚姻與生育——以墓志銘為研究樣本[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74-79.
(責任編輯:鄭宗榮)
An Analysis of the “Po-ti” Phenomenon in Huang Zongxi’s Epitap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is Epitaph
LI Aixi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Huang Zongxi has changed the fixed four-character writing formula of epitaph, and widely used function words in his epitaph. He used discussion and lyric style in the specific writing, and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highlighting the beauty but cancelling the ugliness.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life story of the dead his own reflection is m ingled. This untraditional writing style has broken free from the “Use” function of ep itaph and enhanced the aesthetic and literary value. It ha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later epitaph writing.
Huang Zongxi; Epitaph; “po-ti” Phenomenon
I207.6
A
1009-8135(2014)04-0080-04
2014-05-07
李愛賢(1987-),女,甘肅古浪人,蘭州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元明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