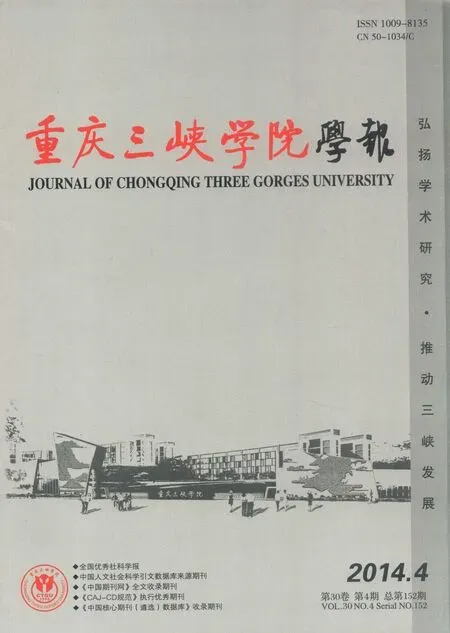論董其昌繪畫理論對汪野亭瓷板畫的影響
鄭依晴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論董其昌繪畫理論對汪野亭瓷板畫的影響
鄭依晴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以汪野亭山水瓷板畫為研究對象,結合董其昌的繪畫理論,從汪野亭山水畫師古與師造化的創作歷程、對以書入畫創作手法的繼承和“天真幽淡”主導下兼擅南北宗山水風格三方面入手,探求董其昌繪畫理論對汪野亭山水瓷板畫,尤其是其后期獨創的青綠山水粉彩瓷畫的異代影響,以期為汪野亭瓷板畫創作研究提供另一有益角度。
董其昌;汪野亭;師古與師造化;以書入畫;南北宗
一、創作歷程:由“師古”、“師造化”漸至“心造”
汪野亭(1884—1943)生活于清末民初,其時淺絳山水瓷畫一統天下,成為市場主流和消費主體。而作為景德四大傳統名瓷之一的粉彩瓷在乾隆后期因消費市場變化及自身工藝陳舊盛極而衰,粉彩山水瓷畫作為粉彩瓷器的重要題材之一同樣也面臨僵化的嚴峻現實,并且隨著晚清極具文人氣息的淺絳山水瓷畫的興起,粉彩山水瓷畫危機益重[1]。粉彩瓷畫的青黃不接和淺絳山水瓷畫的曲高和寡成為擺在汪野亭面前的兩大挑戰。因此,如何改革山水瓷畫,使其更好地融合市場需求和文化氣息就成了汪野亭亟需解決的問題。在理論取法和實踐操作中,他將目光投向了異代書畫家、理論家——董其昌。
董其昌主要活躍于晚明末年,在某種程度上,汪野亭面臨的歷史挑戰與董其昌有異代同向之處:晚明時代,就繪畫界而論,一方面,盛行于明初中期的浙派和吳派山水走向了技法僵化、風格停滯的衰落期,亟需變革;另一方面,以關彬、陳洪綬為代表的畫家則走上了追求新奇、怪異作風的“異派”一途,矯枉過正而終究無法挽回畫壇風氣[2]。面對舊過舊、新過新的畫壇局面,董其昌以“文人畫”為武器,溯源清流,在南北宗論的主調下重申趙孟頫“以云山為師”、“作畫貴有古意”和“書畫同源”的理論主張,并進一步系統提出繪畫創作理論上的“師古”說和“師造化”說,認為畫家需要“初以古人為師,后以造物為師”,終于“心造”,才能融合古人萬家所長,集其大成,進而綜合創作者主觀情意,“自出機杼”。汪野亭在相似的創作困境中明智地選擇汲取董其昌“師古”、“師造化”理論精華,并針對陶瓷這種特殊材質,融入主觀發揮,“以形寫意”,最終成功地由“積劫成菩薩”漸至“一超直入如來”,心悟成而大師起。
首先,汪野亭的創作由“師古”起步,逐步經歷了從“集其大成”到“自出機杼”的過程。汪野亭天資聰穎,自幼時私塾開始,終其一生始終堅持學習傳統文化,豐富學識儲備,提高藝術修養,并在祖父汪享榮的影響下向民間藝人學習繪畫技巧,利用身邊資源臨摹家鄉寺廟壁畫,培養了繪畫興趣,初步具備繪畫理論修養和實踐技巧。1906年,汪野亭成功報考中國陶業學堂,師從潘匋宇、張曉耕、汪曉棠等人,并取法“清四家”尤其是王翚清麗厚實的繪畫技巧,細筆山水近似王翚面貌,粗筆山水得王鑒筆法,初步掌握了粉彩、古彩、青花等陶瓷工藝制繪,題材上兼及花鳥、山水創作,風格上此時汪野亭主要取法程門一派,善用干碎筆墨,著色柔和淡雅,皴法嚴謹不茍,歸于淺絳山水一路,尚未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3]。
藝術的生命力在于創新,而師古只是汪野亭藝術創作的第一步,即董其昌所謂“畫家以古人為師,已自上乘”,欲求更高境界則應“進此當以天地為師,每朝看云氣變幻,絕近畫中仙……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4]29。隨著汪野亭閱歷的加深、畫藝的不斷精進,他同時也希冀在摹古之外探求更多的藝術可能和藝術創造,綜合“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尋求自己獨特的風格特征。1921年,汪野亭參加了景德鎮的“瓷業美術研究社”,汪野亭逐漸看到傳統粉彩山水瓷畫因設色富麗、工藝陳舊、缺乏創新而失去生機、脫離時代,萌發了藝術創新的意愿;同時,汪野亭自幼成長于樂平鄉間,熟悉的南方山水給了他寫生、體驗的機會,南方山水清秀韻潤、自然天成的風光同時給予他改變傳統粉彩瓷畫繁復厚重風格的靈感;加上汪野亭素日喜好郊游尋寺、談佛論禪的習慣也提高了他的修道悟道和藝術境界。這些變化自然而然反應到其創作中,于是延至中晚期,汪野亭創作逐漸趨向新變,改設色淡雅的水墨風格,前期淺絳風格變為雅俗共賞的青綠山水粉彩瓷畫,新粉彩山水瓷畫應運而生。具體而言,汪野亭此時本于心跡,師于造化,憑借對江南山水的切身體悟和早期嫻熟深厚的淺絳山水功底,取文人之法繪瓷,以水墨設色,尤顯淡雅精致、意氣飛動;同時兼采傳統青綠山水豐富華麗的色彩感覺,明麗而不俗艷,迎合時代風尚,合佛儒境界,創雅俗共賞的青綠山水粉彩瓷畫,形成汪派瓷畫獨特的藝術風格。
汪野亭服膺董其昌以“古人為師”、以“造化為師”的創作理念,結合當時瓷板畫創作現狀,以自己深厚的人文修養和匠心獨運的創新技術,推陳出新,最終達到了董氏所謂之“心造”境界,創作了明凈淡雅、意境溫婉又不失“意氣縱橫”、空曠寂寞的“汪派山水”,影響深遠。
二、創作手法:以書入畫
以書入畫實由書畫同源變體而來。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中最早提出“書畫同源”說,據其記載,“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是時,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5]3,初步奠定了書傳意、畫寫形的審美品格。在歷史發展中,書畫同源說不斷被歷代文人轉述、豐富,理論內涵累代而增。自元趙孟頫開以書入畫之端后,董其昌集其大成而深化之,對文人畫尤其是文人山水畫影響極大。
概言之,董其昌由敏銳的藝術眼光出發,大刀闊斧,分山水畫為南北二派,建立起了“以淡為宗”的書畫一體審美觀。進而在理論上全面引書入畫,包括將書法的筆法用法、取勢、取法與變法等觀念滲入繪畫創作,又以繪畫墨法變革書法用墨,并形成“書畫一事”的書畫融通觀點[6]。延及本文,考慮到汪野亭藝術創作集中于繪畫,其書法雖自成一格,也是為服務繪畫而存在,因此這里主要單向擷取董其昌的引書入畫理論闡述汪野亭瓷板畫創作。
汪野亭瓷板畫作為文人畫的典型代表,本身就具有傳統的集合詩、書、畫、印為一體的文人畫審美特征,詩書畫印四元素在汪野亭每一幅畫作中都具備并達到了和諧統一。具體而論,首先,出于文人畫傳統,汪野亭每幅作品均有畫旁題寫詩句后落款的慣例,其或化前人詩句為畫、或化用典故為詩或直接原創題詩,風格典雅厚重,如《古剎鐘聲》圖瓶,汪野亭在全圖黑白潑墨的典雅古潤中復題詩“古寺晨鐘響入云,客帆風箏喜潮平。林泉到處皆名勝,山水之間有妙人”,更在全圖古寂蒼茫中增添了一份清幽淡雅的文人情懷。其以詩入畫,詩畫交相輝映、互相生發,獲象外之象、意外之意的傳神效果,達到了董其昌所謂經“印泥”、“印水”及至“印空”的境界。其次,與汪野亭畫風從秀色氤氳的早期風格到真純幽淡、蒼邁勁古的中晚期風格對應,其書法也經歷了早期洗凈娟秀至中晚期剛勁豐腴的發展,書畫風格變化幾乎同步,相得益彰,同步經歷“工”而漸趨“淡”。再次,董其昌的引書入畫理論,技法上主要體現在筆法、筆墨意趣之上,即董氏言“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4]28不難看出,董其昌認為文人畫除了應當用奇字之法之外,更應該根據不同畫境襯之以行書、篆書、隸書,使書畫境界相融相生。具體繪物上,董其昌強調為樹“只在多曲”,“畫石需用皴”,極推董北苑以“米氏落茄”點綴成樹并以為法。以此觀之,則如前所述,汪野亭粉彩山水畫主要以南方山水為主,體現了典型的南派山水風格,山石多以披麻皴和折帶皴帶出,間或以尖筆、短線刻畫旁邊斷石危崖;繪葉則多用雨點皴,側鋒出筆,有圓有方,力度非常,山石擺勢棄絕平正,“以奇為正”,具有鮮明的以書法之筆繪圖勾勒風格。最后,落款作為中國傳統畫組成部分,既是創作者心性修養及藝術成就的顯現之一,也是書法藝術的另一體現。汪野亭作為一名文人氣息濃厚的瓷板畫畫家,印章也是其藝術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據統計,汪野亭印章款式多樣,方圓不一,繁簡各異,題款則有“傳芳居士野亭”、“野亭汪平于珠山客次”[7]等,風格或規矩或隨意,作畫時則因時因畫而取;其印章書法或行草灑落,或篆隸平整,字體風格同樣配合畫面創作意境和題款風格而落,“或長行直下,使畫面增長氣機;或攔住畫幅邊緣,使布局緊湊;或補充空虛,使畫面平衡;或彌補散漫,增強交叉疏密的變化”[8],印章與詩、書更好地配合畫境,達到和諧統一。以汪野亭《山清水秀》圖瓶為例:畫作以簡潔疏淡的筆風寥寥畫出江南山水明和之氣,青綠山水秀潤清雅;與此對應,其落款以娟秀工整的“山清水秀,仿友人法”行書出之,愈見瀟灑;再配以圓整的方形印章,落紅一角,襯得畫面靈動秀逸,詩書畫印互相生發。
“書畫用筆同法”經張彥遠的理論倡導和蘇軾輩的草創、趙孟頰輩的初步嘗試、元四家到吳門的實踐開拓,終于在董其昌這里結出理性的果實[6]。在董其昌看來,以書入畫不僅在筆法上使畫家用筆更加靈動,深化“以意畫形”,得文人畫三味。對畫面結構經營而言,以書入畫也為山水畫更好地借鑒書法章法體式、意跡運勢等筆墨手法,完善山水畫構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方法。具體操作上,董其昌先總論作書應“有合有收”“似奇反正”,重在“取勢”二字。同理而引,繪畫構圖優劣也重在分合取勢之間——用董其昌的話就是,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整體構圖上需“能分能和,而以皴法足以發之”,才會有“八面玲瓏之巧”;筆法上,董其昌則分而論之,主張繪山水神情用“皴法、渲染法”以達到“似奇反正”效果,若筆法秀峭需學倪云林“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樹“須以轉折為主……如寫字之于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再配之筆法的虛實、肥瘦、濃淡對比,完成山水畫的氣勢安排。其完整的運書入畫理論對汪野亭瓷板畫創作意義重大,尤其不同于平面繪圖,汪野亭面對的是形制不一、凹凸有致的陶瓷制品,其構圖章法必須依物賦形,才能配合器物造型空間,發揮畫作最大的審美價值。汪野亭粉彩山水瓷板畫創作,往往將布畫陣勢放在首位,大多構圖完整,主次分明,講究形式美;近景突出、中景明晰、遠景氤氳;并且吸收書法用筆簡要精煉,使畫面簡潔有致、疏落浩渺;樹多采用皴法鋪就,彎曲折疊而少有樹干筆直高聳之作,轉筆極多,以書法入畫,體現了典型的南方樹型特征。可以說,汪野亭達到了董其昌所謂詩文書畫“少工老淡”至“淡勝工”的境地。
三、創作風格:“幽淡天真”,兼擅南北
說到董其昌,難以繞過的是其影響極大而又毀譽參半的南北宗論(按:對南北宗的提出者學界多有爭論,除董其昌外,有莫是龍說,陳繼儒說,莫衷一是。本文刪繁就簡,采董其昌說)。此舉在融合儒釋道三派思想基礎上,通過對近千年的山水畫的分析總結,不僅為由唐至明的山水畫“派”分門別宗,更權威性地樹立了文人山水畫的審美標準,以文人之雅摒棄匠人之俗,導引其后三百年中國畫走向,造成文人畫與工匠畫的長期對立。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卷二》中引禪入畫,正式提出南北分宗問題:“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干、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勾斫之法,其傳為張躁、荊、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馬駒、云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云峰石跡,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于維也無間然。知言哉”[4]37。董其昌認為,南北二宗并不是依據畫家籍貫區分,而是按照其不同的繪畫技法及畫作風格而言,北宗由李思訓、李昭道父子開宗,延至南宋畫院、明畫院及浙派畫家群體接續之,技法上以勾斫為主,色彩艷麗,風格繁復,不值得提倡。南宗則追溯到唐代典型的文人畫家王維,續之以五代董源、巨然,延至元四大家以至明代吳門畫派,技法上變北派的勾斫之法為渲染,以墨變五色表現陰陽濃淡,風格古淡清雋,有嵐色輕煙之氣。故以此董其昌更引出崇南抑北論,貶斥北宗為匠人之作,以南宗為正統。
以南北山水視之,汪野亭瓷板山水畫創作,不論是其早期創作還是中晚期創作,主要體現了典型的南派山水風格,包括以意統領構圖,繪畫技巧多用皴法、主要描繪南方典型的煙云吐霧、山川浩渺之景,富有筆墨趣味,“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水入腳澄明,水源來歷分曉”[4]34,幽淡天真,符合董其昌的審美要求和審美趣味。但同時,汪野亭深得董其昌“師古”理論精髓,并不以董其昌之論為桎梏,限制自己的藝術取法和審美取向。也就是說,汪野亭摒棄了董其昌的抑北言論,以平正之心消除宗派之見,博采眾長。在表現南方山水時,汪野亭同時兼采北方畫派合理之處,不時借鑒宋代中國山水圖式,在“幽淡天真”的審美意蘊統一下,也追求大山大水雄峻的體式,風格柔中帶剛。甚而學習被董其昌目為“簡率”的馬遠、夏圭等人半邊取景、含蓄不露的構圖之法,因圖所適,注重取勢的輕重變化,更顯空靈疏秀。在其所開創的“汪派山水”創作上,汪野亭更是在賦色上大膽借鑒北派山水青綠設色,以文人山水之法調和傳統青綠山水過于鮮明富麗之色,將自董其昌以來分門對立的青綠山水和文人山水兩個畫派完美結合,統一在以“淡”為主要審美特征的新粉彩青綠山水瓷畫下,既消除了傳統青綠山水瓷畫過度的匠氣和俗氣,又調和了淺絳山水曲高和寡的舊式文人氣,從而達到秀色明潤,雅俗共賞的審美品格。如以汪野亭新粉彩瓷畫代表《修竹茅亭圖》為例,此圖狀溪岸、平臺、茅亭、綠水、青山,通體以青綠二色為主,青蔥可人,體現了北派山水設色特點;同時,青綠二色又在瓷器光潔而帶有一層淡紫覆色下除去突兀之氣,顯得溫厚柔和;圖中兩位高士坐于茅亭之中,相對而談,盡顯文人意趣;畫面求神不求形,以意尋跡,嵐氣氤氳,又極具南派山水特征;而就畫作整體風格來看,高古而不失淡雅,蒼邁中不乏清秀,于簡練中透出粗獷,是為兼擅南北二宗山水長法,“淡”而有味。
在審美意蘊上,汪野亭粉彩瓷畫服膺于董其昌的南宗山水風格,以“幽淡天真”取勝。然而其畫作也蘊藏著不少北派技法,這既與董其昌對北派山水行畫技法多有取材相一致,但更多體現了汪野亭師于己心、追求獨立風格的創新意識,因而其創作風格和審美趣味兼擅南北之風。
四、結 語
在董其昌“師心不師古,在意不在跡”觀點的影響下,以中國古代南宗畫派的眾多代表性人物為師法對象[9],以南派山水為宗,同時廣泛取法北派山水技法,融南北意趣為一體,寄樂于畫,由“師古”而“變古”,真正經“集其大成”而至“自出機杼”境界,開創青綠山水粉彩瓷畫一派,惠澤后世。
[1]何靚,秦俊.論汪野亭新粉彩山水瓷畫的地位與影響[J].中國陶瓷,2011(8):67—72.
[2]方聞.董其昌與正統畫論[J].郭建平,譯.民族藝術,2007(3):65-73.
[3]曲立民.傳芳居士——汪野亭[J].陶瓷研究,2007(4):19—21.
[4]董其昌.畫旨[M].毛建波,校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5]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全譯[M].承載,譯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6]任曉明.董其昌的書法與繪畫關系的研究[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7]徐明歧.解讀汪野亭(上)[J].收藏家,2009(2):67-70.
[8]汪艷.汪野亭粉彩山水瓷畫構圖研究[J].陶瓷研究,2008(3):48-50.
[9]夏斯翔.淺析汪野亭瓷板畫藝術的風格特征[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3(6):66-70.
(責任編輯:鄭宗榮)
The Influence of Dong’s Painting Theory on Wang’s Porcelain Painting of Landscape
ZHENG Yi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ang Yeting’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s of landscape under Dong Qichang’s theory of painting. It specifical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Dong’s painting theory on Wang’s porcelain painting of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ang’s inheritance of the old, “writing mingled into drawing” technique and his excellent command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painting styles under the naivety theme. It also researches into the cross-generation i nfluence of D ong’s painting t heory o n Wang’s t l andscape pai ntings, es p. on his t urquoise overglaze landscape paintings, which offers another useful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Wang Yeting’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s.
Dong Qichang; WangYeting; creating experience from facsimile to sketching; writing mingled into drawing; southern and northern style
J202
A
1009-8135(2014)04-0071-04
2014-05-27
鄭依晴(1991-),女,浙江義烏人,華中師范大學2013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