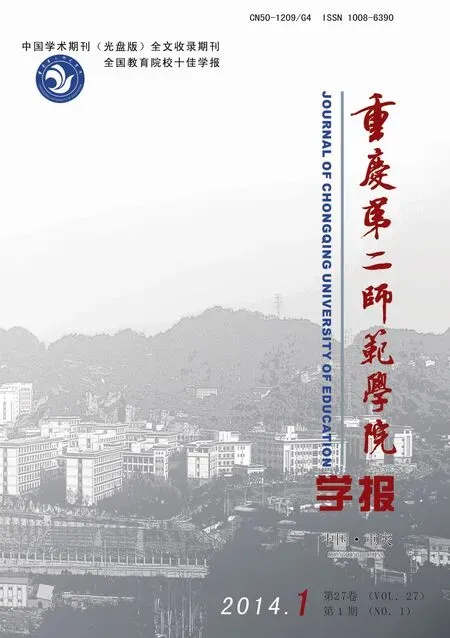“學衡派”教育思想述評
何 娟
(重慶市實驗中學,重慶 401320)
學衡派因1922年1月在南京創辦《學衡》雜志而得名。《學衡》雜志從創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刊79期。梅光迪、胡先骕、吳宓等為主要編撰者,也是學衡派的代表人物。因其多從國外留學歸來,接受了國外先進的教育思想,歸國后在高等院校任教,且多出任教學行政管理職位,對中國教育有自己的獨特思考,不乏真知灼見。梳理總結學衡派諸人的教育思想,對當下中國教育發展不無借鑒意義。
一、學校應為學術之地而非功利之土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社會風氣日益腐化,各種救國思潮此起彼伏。從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到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再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教育方面都提出了相應的革新措施。一次世界大戰后,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世界范圍內興起,梅光迪、胡先骕、吳宓等主持的《學衡》雜志也在此時創刊,其宗旨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并形成“學衡派”。他們認為學校應為人世間一片凈土,無論社會如何,都不應受政治的影響,教育應該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在政治之上,“吾國古代圣賢之理想,蓋主張由教育發生政治,而不使政治之權凌駕于教育之權之上,固一國之中惟教育之權最高”。[1]
對于中等教育,學衡派指出,“中等教育,上承大學,下接小學,為教育成敗之中樞,為學生優劣之關鍵,為世運隆污之機紐,為文明興衰之管輪,為國家治亂之權衡”、“中等教育者,全國青少年所經之要路也,青年之生命養育于是,青年之精神培于是,青年之心維護發于是。”[2]由于青少年正是人生觀、價值觀形成之時,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作為學生精神的培育之地,學校應該不受世俗的影響。對于大學,學衡派認為大學主要之務在于治學。《學衡》第1期,劉伯明《論學者應具之精神》中就闡明大學生應該潛心研究學術,不要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在以后的教育文章中,學衡派反復強調“自新文化運動以來,青年學子心理日趨浮躁,不復知有苦學之事,其學校大抵開會之時多,讀書之時少”。[3]雖然政治并未進入正常的運行軌道,但是學校教育并不能如此,他們認為“真正的學者仍然是昔之書生,書呆子,埋頭于實驗室,圖書館中,專供其所學,自賞其心德,于世俗無影響也”。[4]這并不是說他們不愛國,只是相對而言對于救國之事有比較冷靜的思考,“救國之事全國之人應共負其責,特教育界可為先導,而又必有充分之準備。循序為之,持之以恒,不憑一時含混之熱忱”。[5]在當時兵荒馬亂的特殊時期,“飯碗”競爭日盛,在教育界“亦有視校長位置為優差,角逐經營,駭人聽聞。既得之,復患失之”。[6]很明顯,這是對當時浮躁社會的一種批判,同時也是對學校脫離其本質的一種擔憂,學校特別是大學應為純粹研究學問之地。而中學學生比較年幼,學識經驗相對于比較淺薄,最應該做的事是治學,不宜受到外部的驚擾,不可以視學校為販賣證書的機關、販賣知識之所,應該視為研究學理的機關。
二、學校教育首在育人
上世紀初葉,隨著物質文明日益興盛,教育價值也越來越傾向于功利主義。與此同時,中國本土興起了全盤西化的思潮,教育也盲目地跟風迎合世界“功利主義”潮流。面對此種情景,學衡派扛起反對“全盤西化”的大旗,不惜站在新文化派的對立面,指出教育的大病有四端:“模仿之弊、機械之弊、對外驚鳴之弊、淺狹的功利主義之弊”。[7]如今社會是“物質之學大倡,而人生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微,人不知所以為人之道,于是眾惟趨于功利一途,而又流于感情作用。忠于詭辯只說,群情激擾,人各自是,社會之中,是非善惡之觀念將絕,而各國各族則常以互相殘殺為事。科學發達不能增益人內心之真福,反成為桎梏之刀劍,哀哉,此其受病之根。”[8]可見學衡派堅信道德建設才是人類發展的最高目的。
《學衡》雜志的主編吳宓在《我的人生觀》中,認為人生觀有三種,“一者以天為本,宗教是也;二者以人為本,道德是也;三者以物為本,所謂物本主義是也。處今之世,以第二種之即人本主義為最適,故吾崇信之。”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即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教人以為人之道。第4期發表的胡先骕《說今日教育之危機》最能證明。文章強調“教育之陶冶人才,嘗有二,一為養成其治事治學之能力,一為養成其修身之志趣與習慣”,“二者缺一,則為畸形之發達”。向紹軒亦指出,“夫教育之目的,不外教人做人”。[9]學衡派認為,立國之本在于立人,中國立國之根基在于道德,中國雖然號稱民國,但是名不副實,全國一盤散沙,究其原因是國民大都缺乏應有的人格,要振興中國就必須使青年養成浩然正氣,“今日世界之情形也,所以救治之法奈何?白璧德先生以為但事治標逐末,從事于政治經濟之改革,資產權力之分配,必且無濟。欲求永久之實效,惟有探源立本之一法。即改善人性,培植道德一法是已。”[10]歸之一句,教育中首要之事即注重道德精神。
三、中西匯通,培養通才
學衡派諸人大都曾留學英美,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特殊的情愫。他們不僅在傳統文化的道德精神中汲取新文化建設的養料,而且還把目光投向西方宗教道德遺產,主張新文化必須融中西文化之精華于一爐。胡稷成指出:“欲挽救中國之隳風,必采取批評的態度,將東西文化思想,篩剔提煉,留其精粹,去其秕糠,然后再以博大深遠眼光,探究人生意義,而另立真正價值之標準,以為解決政治社會問題之指鋮。”[11]
學衡派諸人受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影響很深。在白璧德看來,中國儒家思想和亞里斯多德倫理觀才是人類文化的精華。《學衡》雜志從創刊起就對白璧德人文主義進行了熱情謳歌,在38期中吳宓特別翻譯了《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文中指出:“孔孟之人本主義,原系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今取以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下之學說相比較,融會貫通,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歷代名儒巨子之所論述,熔鑄一爐,以為吾國新社會群治之基。如是,則國粹不失,歐化亦成,所謂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兩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此非旦夕之事,亦非三五人之力,其艱難繁巨,所不待言。今新文化運動,如能補偏趨正,肆力于此途,則吾所凝目佇望,而愿馨香感謝者矣。此吾所擬建設大綱,邦人君子,尚乞有以教之。”[12]
學衡派諸人都是博古通今的大學者,他們主張大學里應該培養通才,不能限制學生的發展。柳詒徵的《自由教學法》中就有明確的強調,學校的課程“由教育部制定,某種學生必習,若干科目,且學至和程度,頒行國內,使其劃一,其某時學某科,某年學某科,不必劃定,敏者一年或數目了之可也,鈍者積若干年或學完亦可也”。[13]學生各方面的知識都要有,文史哲與社會科學需要有自然科學知識,學習自然科學知識也要有文史知識,這樣才不至于囿于一隅。學衡派諸人并不是空喊口號的理論家,他們將其教育思想運用于實踐當中,吳宓在主持清華大學外文系時就將其“博雅教育”付諸實踐,并培養出了季羨林、錢鐘書等一批大學者,都是通才。
四、教之有方,因材施教
學衡派諸人非常強調教育的方法,在52期中聶其杰就撰寫了《論教有義方》一文,認為教育應該“善立方法”,認為好的教育方法才能培育出優秀的人才,并對于啟發式教學法異常推崇:“今之評論學校者,每并其以書中事實灌充兒童之心胸,而不發展其智力。真正的教育家其最有效之方法在啟發學生之想象。”[14]真正的好老師不能是呆板地給學生灌輸書本知識,應該注重激發學生的興趣,引發學生的想象,使學生學會舉一反三,最終學會研習的方法,讓學生學會自己鉆研而不拘泥于課本。為此柳詒徵還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教學方法,集中體現在《學衡》1931年第75期上發表的《自由教學法》一文中。柳詒徵認為,“現行的學校教學,限以時間,制以科目,裁以單位,囿以一學期或一學年……”,這樣的學制嚴重限制了人才的培養,同時使學生和教員都感覺到比較痛苦,教員為未教完自己應教之知識而痛苦,學生則為未學習應學之知識而痛苦。“窮則變,變則通”,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學法”的大膽構想:在課程、師資、學生、儀器、圖書、考試、職業六方面都有涉及。教育部對總的課程設置可以有所限定,但是學生學習時間則看自己的學習能力而定;教師可以教授什么科目則要經過嚴格的考試,并且教育部要頒發相應的資格證;學生修習各門課程則無須限定順序與時間,學生自小學畢業后,聽其自由求師;學堂停辦,教師可自由授徒,國家組織嚴格的考試,各門課程及格者,授予相應的文憑。同時,國家在各省市縣設立公共的科學儀器館、圖書館及各類音樂美術體育設施,適當收費或免費供學生使用。柳詒徵的“自由教學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機械的學校課堂教學,還學生和教員一個自由學習和教學的空間。
學衡派諸人還主張因材施教,在不放棄差生的同時,學校應該有精英教育,以為國家培養真正所需人才。他們指出“夫謂學校為全體人民而設,受全體人民之供給,是以當為全體人民之子弟著想,刺眼固甚合理,謂雖下材亦不當棄,惟當如其資質而培育之,此言亦合乎人道,然若良莠不辨,高下不分……又豈合乎人道耶?”[15]如果教員不能分辨良莠,會導致蠢者愈蠢,慧者也不能很好地施展他們的才華,這樣會有百害而無一利。好的學校教育應該是在學生剛入學時,對其進行相應的測定,以便了解他們所需之學,對于低能兒童應該另設學校、另開班級,教給他們所需要的學問,“若犧牲才者依舊不才,棄將來社會之中堅以成就將來社會之贅瘤,此豈所以為義,豈所以為愛國?”[16]學衡派諸人提出要救中國就必須培育出真正的人才,這也是學校教育應該完成的工作。青年學生亦要能知行合一、學以致用,“有學識而無技能則坐而不能起行者也,有技能而無學識則從之而不知所以者也。”[17]學校教育中應該有專門的職業教育,為以后的實踐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并且職業教育可以不需要學習普通的文理科目,重視實習,國家應為職業教育創造良好的條件,由國家指定若干農場、工場或銀行公司,學農者師農,習銀行者應該師從銀行員。
綜上所述,學衡派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教育應該為最高權力機關,不受政治制約,凌駕于政治之上,國家應該給予學校教育多方面的支持,為培養人才提供良好的條件。學校教育首要在于育人,然后治學,教員應該因材施教,教之有方,為國家培養真正需要的人才。這其中不乏偏頗、激進之處,但是許多教育思想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在如今物質利益日盛的社會,青年道德思想日益缺乏,我們需要實行“人文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時學生負擔日益加重,學習越來越功利化,我們應該給學生創造出自由的學習環境。
參考文獻:
[1]柳詒徵.教育之最高權[J].學衡,1924,(28).
[2]劉永濟.今日中等教育界之緊急問題[J].學衡,1923,(20).
[3][6]向紹軒.學校考試與教育前途[J].學衡,1924,(29).
[4]柳詒徵.學者之術[J].學衡,1924,(33).
[5]劉伯明.論學風[J].學衡,1923,(16).
[7]汪祖.現實我國教育上之弊病與其救治之方略[J].學衡,1923,(22).
[8]吳宓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J].學衡,1922,(3).
[9]向紹軒.今日吾國教育之責任[J].學衡,1924,(29).
[10]吳宓譯.白璧德論民治與領袖[J].學衡,1923,(32).
[11]胡稷成.批評態度的精神改造運動[J].學衡,1932,(75).
[12]吳宓譯.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J].學衡,1925,(38).
[13]柳詒徵.自由教學法[J].學衡,1932,(75).
[14][15][16]張蔭麟,葛籣堅.論學校與教育[J].學衡,1925,(42).
[17]楊成能.學識與技能[J].學衡,192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