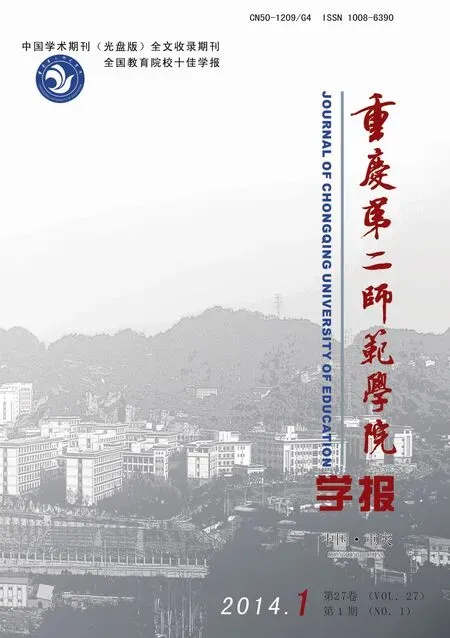反東方主義視野下的《灶神之妻》
王小燕
(福建中醫(yī)藥大學(xué) 管理學(xué)院,福建 福州 350108)
譚恩美在1989年發(fā)表了第一部小說(shuō)《喜福會(huì)》(TheJoyLuckClub)之后,1991年又發(fā)表了第二部小說(shuō)《灶神之妻》(TheKitchenGod’sWife)。這部小說(shuō)雖然沒(méi)有《喜福會(huì)》那樣倍受追捧,但也好評(píng)連連:《星期日電報(bào)》評(píng)論“譚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她把那些不為我們熟知的色彩、氣味、味道和風(fēng)景編制成令人目眩的網(wǎng)”;[1]《每日郵報(bào)》則評(píng)論稱“《灶神之妻》中最吸引人的不僅在于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故事情節(jié),而且在于關(guān)于中國(guó)的生活和傳統(tǒng)的細(xì)節(jié)描寫(xiě)”;[2]《今日美國(guó)》也說(shuō)“不同的聲音使這本書(shū)串聯(lián)起來(lái),充滿細(xì)節(jié)的描寫(xiě)使讀者好似立足于另一個(gè)世界”。[3]從評(píng)論可以看出,媒體和讀者似乎關(guān)注的是一個(gè)充滿異國(guó)情調(diào)、神秘色彩和與西方世界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中國(guó)。
《灶神之妻》的主人公溫妮(江韋麗)出身豪門(mén),是父親第二個(gè)太太的女兒。因?yàn)槟赣H的出走她被寄養(yǎng)在叔叔家。長(zhǎng)久以來(lái)缺少關(guān)愛(ài)的她在18歲那年嫁給了文福。婚后發(fā)現(xiàn)自己的丈夫是個(gè)性格暴戾、自私貪婪、索求無(wú)度且毫無(wú)道德感和責(zé)任感的人,她跟隨入伍的丈夫穿行于戰(zhàn)時(shí)的中國(guó)多年,在自己的三個(gè)孩子相繼夭折后,她毅然決然地離婚并且嫁給了美籍華人吉米·路易,最終贏得幸福。這部小說(shuō)沿襲了譚氏寫(xiě)作的諸多風(fēng)格和特點(diǎn),例如母女關(guān)系以講故事的形式展開(kāi)來(lái)化解兩代人之間的文化隔閡;書(shū)中對(duì)于中國(guó)的風(fēng)土人情、飲食、鬼故事、陰陽(yáng)、婚姻、算命、迷信、節(jié)日傳統(tǒng)等有著大量的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描寫(xiě),在讀者面前展開(kāi)的是一幅充滿異國(guó)情調(diào)的幻境與現(xiàn)實(shí)、記憶與幻想的神奇畫(huà)卷。不難看出,《灶神之妻》中的“他者”中國(guó)形象是吸引讀者的一大亮點(diǎn),這部小說(shuō)具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
什么是東方主義?愛(ài)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在1978年發(fā)表的著作《東方學(xué)》(Orientalism)里清晰表達(dá)了這一概念。東方主義被視為一種根據(jù)東方在西方經(jīng)驗(yàn)的位置而處理、協(xié)調(diào)東方的方式。在這個(gè)方式里東方被包含在歐洲物質(zhì)文明和文化中,是歐洲得以建立的他者。對(duì)于歐洲而言,東方既不是自然存在也不是歐洲的純粹虛構(gòu)。東方主義是一種被認(rèn)為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理論和實(shí)踐體系,不可能拋開(kāi)漫長(zhǎng)歷史累積下的物質(zhì)層面的內(nèi)容而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東方主義就是指東方的一些本質(zhì)性的東西的集合體:東方的專制主義傾向,異常的精神狀態(tài),其習(xí)慣的不準(zhǔn)確,落后等。”[4]
一、譚恩美與中國(guó)文化
譚恩美作為已經(jīng)融入美國(guó)主流文化的華裔女作家,具有濃厚的中國(guó)情結(jié)。母女關(guān)系、家庭關(guān)系、親情血緣和華裔婦女的社會(huì)地位是她創(chuàng)作的焦點(diǎn)。她雖長(zhǎng)著東方的臉,卻擁有西方的眼。她在很多場(chǎng)合一再?gòu)?qiáng)調(diào)自己是美國(guó)人。與趙建秀、黃哲倫等有著強(qiáng)烈民族文化使命感的作家不同,譚恩美似乎更加注重文學(xué)作品的美學(xué)功能,不愿添加更多的社會(huì)和政治功能于作品中。譚恩美在一次訪談中說(shuō):“迫使作家肩負(fù)代表一種文化的職責(zé)是沉重的負(fù)擔(dān),一些作家他們的小說(shuō)并不是指向某一特定的人群,他們只是在寫(xiě)一個(gè)故事而已。”[5]
譚恩美對(duì)于中國(guó)和中國(guó)文化到底了解多少?單從這部小說(shuō)里我們便可探知一二。關(guān)于主人公溫妮和花生之間親密關(guān)系的描寫(xiě),譚恩美用到“糖姐”(sweet sister)一詞,這顯然是作者將“糖”和“堂”混淆不清的結(jié)果。當(dāng)溫妮和胡蘭討論牛郎織女的故事的時(shí)候,溫妮糾正胡蘭說(shuō)“織女是灶神的七個(gè)女兒之一”。[6]顯然中國(guó)人耳熟能詳?shù)呐@煽椗墓适略谶@里又有了一次篡改。織女是玉皇大帝的最小的七女兒,在這里怎么變成了灶神的女兒。作者沒(méi)有向讀者解釋清楚,傳達(dá)出正確的信息,她改編了中國(guó)神話。當(dāng)溫妮向女兒描述自己跟胡蘭一度關(guān)系很差的時(shí)候,她用到了“四分五裂”(four splits and five cracks)一詞。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四分五裂”一詞意思是“不完整,不集中,不團(tuán)結(jié),不統(tǒng)一”[7]。此詞來(lái)源于《戰(zhàn)國(guó)策》。《戰(zhàn)國(guó)策·魏策一》:“張儀為秦連橫說(shuō)魏王曰:‘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是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8]根據(jù)釋義,我們知道在中國(guó)文化里人們不用這樣的詞語(yǔ)來(lái)描寫(xiě)兩個(gè)人的關(guān)系的破裂。顯然譚恩美的用詞不夠確切。但是對(duì)于缺少中國(guó)文化知識(shí)的西方讀者而言,譚恩美的書(shū)寫(xiě)是可信的、真實(shí)的。因?yàn)樗兄A人身份和特有的中國(guó)文化淵源,她是代表來(lái)自內(nèi)部的聲音。《灶神之妻》甚至被有些人認(rèn)為是中國(guó)歷史及社會(huì)學(xué)的教科書(shū)。“從背景中……我們更加認(rèn)識(shí)了中國(guó)社會(huì)媒妁之言婚姻的本質(zhì)及原配夫人和姨太太之間相處的情形。讀這本書(shū)就像是被邀請(qǐng)到一間堆滿舊物的房間內(nèi),有機(jī)會(huì)一睹其往日的風(fēng)采。我們了解到在美國(guó)的中國(guó)社會(huì)是如何發(fā)展的……譚恩美給了我們一把鑰匙去開(kāi)一扇緊鎖的門(mén)。”[9]但是,她的書(shū)寫(xiě)的真實(shí)性是值得商榷的。恰恰相反,因?yàn)樗奶厥馍矸菀约皶?shū)寫(xiě)的特殊內(nèi)容掩蓋了她書(shū)寫(xiě)的非真確性。
黃秀玲在《“糖姐”:試論譚恩美現(xiàn)象》一文中指出:“譚恩美透過(guò)她所擔(dān)任的文化詮釋及文化認(rèn)同的角色成功地吸引了這些讀者。從表面上看,譚恩美的角色具有真確性的權(quán)威——雖然她對(duì)中國(guó)事物的認(rèn)識(shí)是在美國(guó)生長(zhǎng)的華裔經(jīng)過(guò)多重中介以后的產(chǎn)物。”[10]顯然讀者不會(huì)考究這些細(xì)節(jié)的真確性,因?yàn)轭愃频拿枋霾⒉挥绊懽T恩美令人欲罷不能的敘事技巧或是整個(gè)故事幽默風(fēng)趣的編排。其實(shí)作者也大可不必這樣濃墨重彩的把這些細(xì)節(jié)介紹出來(lái)?但是它們的確有著特殊的功用,當(dāng)溫妮用英語(yǔ)向女兒解釋時(shí),讀者也有了一個(gè)了解異質(zhì)文化的機(jī)會(huì),而且是符合他們審美情趣和取向的異質(zhì)文化。他們關(guān)注的是異質(zhì)文化的“他者”形象能讓他們站在一個(gè)居高臨下的位置去閱讀。而女兒是土生土長(zhǎng)的美國(guó)人,“美國(guó)化的女兒實(shí)際上是主流讀者群的替身”。[11]
趙建秀對(duì)此進(jìn)行了批評(píng):“湯婷婷、雷祖威、譚恩美是有史以來(lái)所有種族中第一批,也無(wú)疑是亞洲種族中第一批敢于篡改最廣為人知的亞洲文學(xué)和知識(shí)體系用以偽造一批知名作品的作家。為了讓他們的偽造合法化,他們又不得不偽造所有的亞裔美國(guó)歷史和文學(xué),并辯解說(shuō)在美國(guó)定居了多年的中國(guó)移民已然失去了與中國(guó)的聯(lián)系,預(yù)示他們結(jié)合自己殘缺的記憶與新的體驗(yàn)寫(xiě)出傳統(tǒng)故事的新版本。歷史的這個(gè)版本是他們對(duì)(中國(guó)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stereotype)的助長(zhǎng)。”[12]一再篡改的中國(guó)文化失去了其原本的質(zhì)感。但是陸薇認(rèn)為:“對(duì)民族文化在異質(zhì)文化中有目的改寫(xiě)實(shí)際上打開(kāi)了民族文化封閉系統(tǒng),使靜止、固定的文化系統(tǒng)開(kāi)始進(jìn)入流動(dòng)的循環(huán)。這不但不會(huì)妨礙它的民族文化在異國(guó)的傳播和發(fā)展,而且會(huì)有助于民族文化在異質(zhì)文化的語(yǔ)境中得以不斷的繁衍生息。”[13]如果這樣的改寫(xiě)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然而然的發(fā)展,客觀的改寫(xiě),對(duì)于民族文化的發(fā)展是有益的。對(duì)于作家來(lái)說(shuō),如果帶有目的性的改寫(xiě)民族文化、歪曲事實(shí)以博得讀者目光,民族文化肯定會(huì)失去其原初性和本真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民族文化被異邦族群所接受,這樣的文化也只能在異國(guó)形成一種文化偏見(jiàn),從而對(duì)其元文化帶來(lái)災(zāi)難。
二、“他者”中國(guó)
(一)貧窮、落后、閉塞
小說(shuō)《灶神之妻》以倒敘的方式回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shí)期的中國(guó),在溫妮的眼里那時(shí)的中國(guó)是野蠻的、落后的、無(wú)任何長(zhǎng)處可言。而這種描述恰恰迎合了西方讀者認(rèn)為“他者”東方和中國(guó)“貧窮、落后、閉塞、愚昧”的成見(jiàn)。當(dāng)溫妮告訴自己的女兒她所居住的那個(gè)島上的人幾乎每一家都很窮,而且大家認(rèn)為這樣一富百窮的狀態(tài)是命運(yùn)的安排,是理所當(dāng)然的。讀者會(huì)認(rèn)為中國(guó)人喜歡認(rèn)命,骨子里就有著這樣的氣質(zhì)。而且她一再?gòu)?qiáng)調(diào)“這就是中國(guó)”。[14]當(dāng)溫妮“逃難”經(jīng)過(guò)貴陽(yáng)時(shí),不得不住進(jìn)一個(gè)旅館。她說(shuō)“我告訴你吧,太可怕了,那兒旅館簡(jiǎn)陋又骯臟。我問(wèn)浴室在哪兒,她們回答‘外面’。原來(lái)她們說(shuō)的外面,真的就是外面!野地里一個(gè)非常臟的地方,大家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方便”。[15]讀者不僅看到了中國(guó)的臟、亂、差,更加關(guān)注到了中國(guó)人的生活習(xí)慣——在大庭廣眾之下如廁。他們也許會(huì)想“難道中國(guó)人都沒(méi)有羞恥心嗎?”這大概就是東方主義想達(dá)到的一種效果吧。我們?cè)倏纯礈啬輰?duì)昆明的一個(gè)湖的描述:“聽(tīng)說(shuō)這個(gè)湖看上去很美,也許曾經(jīng)是這樣。可我看到,城里最窮的窮人全在這兒洗澡、洗衣服,還干一些說(shuō)不出口的事情。”[16]這說(shuō)不出口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讀者的胃口一再被吊起,當(dāng)然是以異化中國(guó)形象為代價(jià)的。
當(dāng)江韋麗一行人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沙的時(shí)候,她這樣描述:“這就是你們美國(guó)人經(jīng)常在電影里看到的中國(guó)——貧窮的鄉(xiāng)野,人們戴著帽子來(lái)遮陽(yáng)。”[17]“一路走來(lái),我們經(jīng)過(guò)了各個(gè)不同部落民族,他們頂著骯臟的帽子在頭頂。”[18]譚恩美的這些描述似乎是在為美國(guó)媒體提供證言——美國(guó)媒體忠實(shí)地再現(xiàn)了中國(guó)的落后。諸如此類的描述,使得中國(guó)和中國(guó)人被一再異化成了他者形象。作者還通過(guò)溫妮之口將東西方作了比較:“那時(shí)的中國(guó)不像美國(guó)——自由、自強(qiáng)、獨(dú)立思考、做你想做的,違背你的母親。”[19]作者借他人之口表達(dá)了對(duì)落后、封閉、骯臟中國(guó)的厭惡和唾棄,而對(duì)于美國(guó)的自由、富有生氣的則贊美有加。“我們也不抱怨很多,中國(guó)人知道怎樣適應(yīng)任何一種事物……你應(yīng)該慶幸你出生在這個(gè)國(guó)家。”[20]華人“模范”民族的形象再一次得到很好的印證——從不抱怨,知道適應(yīng)。在譚恩美的描述中,被消解又被重構(gòu)的想象性的東方成為驗(yàn)證西方自身強(qiáng)大的“他者”,并將一種“虛構(gòu)東方”形象反過(guò)來(lái)強(qiáng)加于東方,將東方納入西方中心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西方無(wú)疑是先進(jìn)的、自由的、理性的,而東方是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這樣的對(duì)比更加凸顯了西方世界無(wú)可爭(zhēng)議的優(yōu)越性,也使譚氏的讀者帶有強(qiáng)烈的文化優(yōu)越感去閱讀這部小說(shuō)。
(二)謎、謠言、鬼故事
與譚恩美的其它小說(shuō)相似,《灶神之妻》這部小說(shuō)充滿了迷幻色彩,包括很多未解之謎、謠言和鬼故事。在譚恩美的另外一部小說(shuō)《百感神秘》里,鄺借尸還魂、給奧利維亞講鬼故事、用神秘百感挽救了奧利維亞與西蒙瀕臨破裂的婚姻、她有著不可思議的祛除病痛的能力等。這些都是與科學(xué)和理性不相容的。而在《灶神之妻》開(kāi)始部分,作者就給讀者設(shè)定了一個(gè)謎,是關(guān)于溫妮的母親。她到底是跟人私奔、離家出走,還是死去了?我們不得而知。“就這樣我的母親成了一個(gè)謎,每一段流言蜚語(yǔ)都讓我腦子有了另外的未解之問(wèn)題。如果她死去了,為什么沒(méi)有葬禮?如果她還活著為什么不回來(lái)找我?如果她離家出走了,那她去了什么地方呢?”[21]并且給讀者這樣一種印象:中國(guó)人似乎有一種特異的傳播流言、謊言、笑話的能力。雖然對(duì)于母親的去向沒(méi)有定論,但是這并不妨礙人們把這位消失的二太太作為茶余飯后消遣的談資。“仍然,他們談?wù)撝K麄兌颊務(wù)摗ɡ蠇鹉铮聥鹉铮迨搴退麄兊呐笥选诤炔璧臅r(shí)候、吃飯的當(dāng)口、午后小憩之后。很多年來(lái)我的母親成了可笑和惡劣的榜樣、可怕的秘密和羅曼蒂克的傳說(shuō)”。[22]母親的去向固然成了一個(gè)謎和一個(gè)不確定性的事件,但是人們的談?wù)撌欠窀幼屛鞣阶x者覺(jué)得中國(guó)人的低俗可惡呢?
小說(shuō)多次出現(xiàn)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guó)人的房事被扭曲變異,以滿足西方讀者窺視東方的獵奇心理。故事講的是:有一個(gè)男子迷戀上了一個(gè)父母都不接受的女子,并且娶她為妻,原因是她有著特別的性技巧。后來(lái)男子在與女子行房事時(shí)昏死過(guò)去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身體怎么也不能和女子的身體分開(kāi)。人們解釋說(shuō)因?yàn)檫@個(gè)女子太“陰”了。讀者的好奇心和窺視欲再一次得到了滿足。西方世界往往認(rèn)為,在東方人們有一些落后而奇怪的性觀念和性風(fēng)俗,而女性則是深受壓迫和欺凌的對(duì)象。另外還有一則故事有著異曲同工之效果,江韋麗14歲的女仆在被文福強(qiáng)奸之后,為了墮胎“她用土方法。從笤帚上抽取一根稻草戳進(jìn)自己的子宮直到流血,可最后卻是血流不止”。[23]最后這個(gè)女孩因?yàn)閴櫶ザ廊ァ_@樣的事情讓中國(guó)讀者瞠目結(jié)舌,當(dāng)然能博得西方讀者的眼球。當(dāng)然這些事情不是江韋麗親眼所見(jiàn),是謠言傳到了她的耳朵。第一個(gè)故事是花生聽(tīng)叔叔跟朋友聊天的時(shí)候講到的,然后告訴了江韋麗。而第二個(gè)事情則是胡蘭告訴她的。她不得不把這些奇奇怪怪的中國(guó)人和中國(guó)人的事情告訴自己的女兒和西方讀者。
飛行員甘告訴江韋麗,自己曾經(jīng)看到過(guò)鬼魂,鬼魂告訴甘他會(huì)在甘24歲生日之前再次到來(lái),而且說(shuō)甘的死亡將會(huì)是沒(méi)有痛苦的死亡。為了讓甘相信,鬼魂預(yù)測(cè)了在甘生命結(jié)束之前還會(huì)發(fā)生的其它八件事。甘說(shuō)“但是現(xiàn)在那八件鬼魂預(yù)測(cè)的事情都一一應(yīng)驗(yàn)。我現(xiàn)在想第九件正在到來(lái)。還有四個(gè)月虎年就會(huì)到來(lái)。”[24]果然,甘在24歲之前犧牲了。鬼神之說(shuō)向來(lái)是譚氏小說(shuō)不可或缺的敘事手法。學(xué)者周蕾曾用“大金剛癥狀”作比喻:“第三世界是個(gè)像巨大怪物的原料生產(chǎn)地,其目的是為第一世界制造既有些娛樂(lè)價(jià)值,又可充實(shí)其精神生活的東西。”[25]母親的神秘去向、年輕夫婦的奇怪性行為還有14歲女孩的墮胎事件是流言還是謊言?還有鬼神之說(shuō)的神秘似乎是中國(guó)人熱衷于傳播的內(nèi)容。就如賽義德所言:“精確與東方人的思維水火難容……歐洲人是縝密的推理者。……東方人對(duì)謊言有著頑固的癖好,他們‘渾渾噩噩,滿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貴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26]
三、“西方拯救東方”范式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譚恩美的筆下也有了耐人尋味的比較。小說(shuō)第五章溫妮說(shuō)道:“我不知道為什么每個(gè)人都認(rèn)為孔子是個(gè)智者善人。他令所有人看不起另一些人,而女人是最被看不起的!”[27]儒家文化歷史悠久,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歷史、文化、思想和道德規(guī)范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仁、義、禮、智、信”的社會(huì)規(guī)范,構(gòu)成了儒學(xué)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但是三綱五常的社會(huì)規(guī)范對(duì)于在美國(guó)長(zhǎng)大的譚恩美來(lái)說(shuō)是不可思議的,認(rèn)為儒家文化是禁錮女性思想和行動(dòng)的枷鎖。所以她有著這樣的書(shū)寫(xiě):“我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從來(lái)不能批評(píng)男人還有男人統(tǒng)治的社會(huì),或者孔子,那個(gè)制造了如此社會(huì)的糟糕男人。”[28]溫妮的大嬸娘告訴她:“女孩子的眼睛從來(lái)不是用來(lái)讀書(shū)的,只能是做針線活。女孩子的耳朵從來(lái)不是用來(lái)聽(tīng)想法的,只是聽(tīng)命令。女孩子的嘴巴應(yīng)該小巧,幾乎不用,除了用來(lái)表達(dá)同意或者尋求同意。”[29]譚恩美的幾句話就對(duì)中國(guó)的儒家文化作了總結(jié)。固然儒家文化有其不可否認(rèn)的弊端,但是儒家文化又是何等的博大精深,豈能以一言蔽之。在這里作者不是客觀、實(shí)在地描述儒家文化,而是有選擇、有目的地“剪輯”、“拼貼”、“重構(gòu)”東方文化。此時(shí)的中國(guó)是沉默的,儒家文化是失語(yǔ)的。就如陳愛(ài)敏在其《認(rèn)同與疏離》一書(shū)中所言:“從文化的角度看,長(zhǎng)期以來(lái),東方一直處于西方強(qiáng)勢(shì)話語(yǔ)的包圍之中,東方不能言說(shuō)自己,處于失語(yǔ)的狀態(tài);東方處于被看的位置,聽(tīng)任西方去描繪、敘述和重構(gòu)。”[30]而重構(gòu)的中國(guó)必然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已經(jīng)被異化了的中國(guó)。賽義德認(rèn)為東方人連同被標(biāo)上那些諸如落后、墮落、不開(kāi)化名稱的民族一樣是在一個(gè)生物決定論和道德政治勸諭論的框架里被加以審視的。因此與西方權(quán)利話語(yǔ)和文化相比,東方文化具有強(qiáng)烈的異質(zhì)性。
相反,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小說(shuō)里被一再宣揚(yáng)和贊美。溫妮的第二任丈夫是個(gè)美籍華人,他風(fēng)趣、幽默、機(jī)智、謙遜,具有紳士風(fēng)度。他深受中國(guó)女子的歡迎和喜愛(ài),而他對(duì)溫妮的關(guān)照讓她受寵若驚。他風(fēng)度翩翩,在舞會(huì)上對(duì)于中國(guó)女子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尊重正是西方社會(huì)所崇尚的騎士精神的彰顯。“我不能說(shuō)我從一開(kāi)始就愛(ài)上了他,……但我得承認(rèn)我饒有興趣地觀察他,和他與美國(guó)人在一起時(shí)輕松自如。……而我當(dāng)時(shí)一定像個(gè)鄉(xiāng)下姑娘。這個(gè)美國(guó)人會(huì)怎么看我!”[31]我們可以看出江韋麗是自卑的,她被這個(gè)地地道道的、自信的美國(guó)人所深深吸引。其實(shí),東方主義最大的破壞力就在于它在被描述被重構(gòu)的靈魂中注入了一種自卑情結(jié),而這種自卑情結(jié)正是來(lái)自于本民族文化的“劣質(zhì)”或者“喪失”。儒家文化造就了江韋麗的順從、容忍、柔弱、謙卑的性格,也造就了她命運(yùn)的不幸。這是個(gè)體的不幸,也是其成長(zhǎng)文化的“劣質(zhì)”造成的。而從小就出生在美國(guó),受著基督教文化浸染的吉米則是自信自如的。
另一方面,吉米的優(yōu)雅風(fēng)度和文福的無(wú)知輕狂又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我看得出來(lái)他急于表現(xiàn)他的舞姿。但我很快就發(fā)現(xiàn)其實(shí)他對(duì)跳舞一無(wú)所知”。[32]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gè)東西方文化的二元對(duì)立:代表西方的吉米富有魅力、紳士風(fēng)度、有學(xué)識(shí)、尊敬女性;而代表東方的文福自私狹隘、性格暴虐、滿腹獸欲、毫無(wú)責(zé)任。文福帶給江韋麗的是無(wú)盡的災(zāi)難、痛苦、折磨,而吉米則拯救了溫妮,給了她幸福的生活、光明的未來(lái)。所有這些形成了一個(gè)冠冕堂皇的理由——讓西方來(lái)拯救東方。小說(shuō)塑造的東方男子不是像文福那樣性欲膨脹的厭女狂,就是被“閹割”了的性無(wú)能(例如胡蘭的第一任丈夫家國(guó))。正如美國(guó)媒體把東方女子描寫(xiě)成“輕浮,淫蕩,溫順”的定型人物一樣,他們也把華人男子描寫(xiě)成“是極其可愛(ài)的、充滿娘娘腔的民族……他們活著就是為了陪襯白人男子漢的英雄氣概”。[33]而東方女人與東方男人相比要“‘好的多’,她們對(duì)西方男人來(lái)說(shuō)至少是有吸引力的,這表現(xiàn)在她們‘具有異國(guó)情調(diào)’、‘柔弱’、‘溫順’,為了‘愛(ài)’甚至可以犧牲一切的‘高貴’品質(zhì)上。”[34]柔弱的、順從的江韋麗正完全符合西方讀者對(duì)于東方女性的期許——“她們通常是男性權(quán)利幻想的產(chǎn)物。她們代表著無(wú)休無(wú)止的欲望,她們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主要的是,她們甘愿犧牲”。[35]江韋麗在安靜的等待著白馬王子的解救。而“西方堅(jiān)信東方從內(nèi)心深處需要被征服——因?yàn)榕藳](méi)有能力思考問(wèn)題”。[36]
西方拯救東方不僅僅表現(xiàn)在基督教文化優(yōu)越于儒家文化,或者一個(gè)美國(guó)男子拯救江韋麗于水火給了她幸福的生活,而且表現(xiàn)在它高高在上救世主的姿態(tài)上。最有象征意義的莫過(guò)于吉米在舞會(huì)上給中國(guó)姑娘起名字。我想這是作者有意為之。“當(dāng)然,他非常英俊,但他不像文福那樣縱容她們的示愛(ài)。他受歡迎的原因是他能給姑娘們起美國(guó)名字。”[37]誰(shuí)具有不可爭(zhēng)議的命名權(quán)?當(dāng)然是屬上階層和權(quán)利話語(yǔ)。在中國(guó)給新生兒命名是多么重要和隆重的事情啊。而具有命名權(quán)的一般是德高望重的祖、父輩或者位高權(quán)重的人物。長(zhǎng)輩們會(huì)根據(jù)新生兒出生的時(shí)辰、命理、五行生克、陰陽(yáng)、生肖、姓名卦理、讀音、字音字形、民俗傳統(tǒng)、族譜等小心翼翼地為新生兒起名。中國(guó)人對(duì)于起名的珍視和隆重不言而喻。因?yàn)槊执碇谠S、命運(yùn)、社會(huì)傳統(tǒng)、文化、美德等。而重新命名則寓意新的生命、新的未來(lái)。至少對(duì)江韋麗來(lái)說(shuō)是這樣的,吉米給她的英文名字是Winnie,意思“win,win,win”。“我們將自己與名字認(rèn)同,因而也將就自己與自己所歸屬的這個(gè)共同體認(rèn)同”[38]。女主人公的名字從江韋麗改叫溫妮,是否意味著她對(duì)自己所屬的共同體新的選擇呢?是否意味著江韋麗戰(zhàn)勝父權(quán)統(tǒng)治的封建社會(huì),獲得新生呢?從更深遠(yuǎn)意義上,可以看成是西方拯救了東方,或者西方戰(zhàn)勝了東方范式的再現(xiàn)。
四、結(jié)語(yǔ)
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東方已經(jīng)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地理概念了,而變成了一個(gè)十足的社會(huì)學(xué)或政治學(xué)概念。它是用來(lái)指涉“與‘我們’(西方)不同的對(duì)象罷了”。其表現(xiàn)形式似乎更加隱蔽。譚恩美或許是受到了“隱蔽東方主義”的影響,但是其書(shū)寫(xiě)卻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顯在東方主義”的體現(xiàn)。譚恩美筆下的舊中國(guó)是西方讀者想象中的中國(guó)。為了再現(xiàn)西方讀者的想象,譚恩美不遺余力地書(shū)寫(xiě)了一個(gè)“他者”中國(guó)——落后、閉塞、愚昧、神秘、充滿謊言,與之形成對(duì)比的則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文明、進(jìn)步和理性。就這樣,“西方拯救東方”的范式再次成功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就書(shū)寫(xiě)東方的作家而言,他們總是受西方權(quán)利話語(yǔ)的東方主義的影響,來(lái)強(qiáng)化有關(guān)東方、東方人的固有的和帶有偏見(jiàn)的觀念。他們的差異表現(xiàn)在寫(xiě)作手法和風(fēng)格上,而極少表現(xiàn)在內(nèi)容上。
參考文獻(xiàn):
[1][2][3][6][14][15][16][17][18][19][20][21][22][23][24][27][28][29][31][32][37]Tan,Amy.TheKitchenGod’sWife.[M]New York: Ivy Books 1991. Book Review pages.289.124.285.300.283.284.284.118.118.329.254.123.325.121.388.384.388.
[4][30][35]陳愛(ài)敏.認(rèn)同與疏離-美國(guó)華裔流散文學(xué)的東方主義視野[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7.39.15.55.
[5]Tan, Amy. Salon Interview: Amy Tan, the Spirit within,SalonNovember 12, 1995.
[7]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yǔ)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第五版)[G].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1293.
[8]劉向.戰(zhàn)國(guó)策[M].賀偉,侯仰軍 點(diǎn)校.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2012.247.
[9]Gillespie, Elgy. Amy, Angst, and the Second Novel.Review of Amy Tan’s The Kitchen God’s Wife [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ne 16, 1991.34.
[10]Sau-lin Cynthia Wong, Sugar Sister: Situating the Amy Tan Phenomenon [C]. in David Palumbo-Liu ed.,The Ethnic Cannon: Histories, Institutions, and Interventions. Minnoapolis :Minno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148-149.
[12] Frank Chin,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C]. in Jeffery Paul Chan and al eds,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 Meridian, 1991.3.
[13] 陸薇.走向文化研究的華裔美國(guó)文學(xué)[M].北京 :中華書(shū)局,2007.120.
[25]Chow, Rey. 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 China as Crisis, Spectacle, and Women. [A]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 Mohanty , Russo, and Torres.[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81-100.
[26][34]愛(ài)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xué)[M].王宇根譯. 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47.264.
[33]趙建秀.唐人街女仔的意識(shí)[J].關(guān)注亞裔學(xué)者公報(bào),1972.66.
[36] 黃哲倫.蝴蝶君[M].紐約:美國(guó)新書(shū)圖館,1988.66.
[38] 王光林.錯(cuò)位與超越(前言) [M].天津:南開(kāi)大學(xué)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