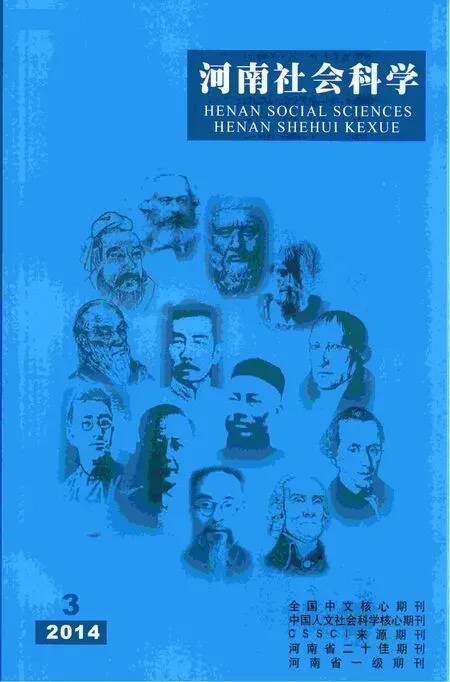強迫執行與制度設計:腐敗治理的一個二分理論
李 輝
(復旦大學 廉政與反腐敗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毋庸置疑,腐敗問題已經是長久以來困擾人類發展的一個巨大難題,針對這一問題人們已經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決辦法。如果在一些大型的社會科學英文數據庫中輸入“corruption”作為搜索關鍵詞,至少能找到4000多篇相關文獻。但是腐敗研究目前呈現出兩極化現狀:一是對策研究占主流,畢竟反腐敗是一個非常強的政策性問題;二是描述、檢驗和增添變量的定量研究占據另外一個高地。唯獨缺乏的是,能夠將對策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反腐敗理論研究。本文將抽取國家中心主義路徑中一個基本的二分理論——強迫與制度設計作為核心,進一步對這一二分法中的兩個概念進行定義,并發展出其類型學的理論意義。與強迫模式相比,雖然制度設計是腐敗治理的更高級也是更為科學的模式,但依然要清醒地認識到其弊端所在。因為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腐敗治理模式,同屬于“國家中心”式的反腐敗模式,其共同的弱點是過于對“橫向責任”的強調,忽略了“縱向責任”在腐敗治理上的巨大作用。
一、腐敗治理中的強迫:概念與表現形式
在腐敗治理理論中,有一個對治理策略的理想類型的二分法:強迫(enforcement)和制度設計(institutional design)。曼寧對反腐敗問題的研究中始終貫穿著這樣兩個基本類型的對立假設,但是她并沒有從理論化的路徑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說這是兩個理想類型,是因為實踐中的反腐敗都會多少包含兩種類型中的一部分策略,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那么,強迫與制度設計的一般定義是什么,在腐敗治理中的強迫與制度設計又指的是什么,作為理想類型的“強迫”與“制度設計”兩種治理腐敗的模式到底有什么區別?上述問題中,不僅幾乎無人涉及,而且也沒有從理論上得到很好的解決。
(一)強迫:定義與理論
“Enforcement”多用于法學著作中,這里我們姑且翻譯為“強迫”,但這一翻譯并不準確,它其實表達的是對法律或者制度的執行(多數帶有強迫的性質)。筆者認為,當學者們把“強迫”和“制度設計”作為一個二元對立的概念在腐敗治理理論中來使用的時候,強迫其實指的是腐敗治理的較為初級的形式,其主要內涵為:
只有很少量的法律和制度可以使用,且這些法律和制度主要作為懲罰的依據,而不是作為降低腐敗機會的預防手段而存在;在強迫的腐敗治理策略下,反腐敗機構的主要活動在于有選擇性地懲罰腐敗分子,而不是提供新的制度杜絕腐敗活動的再次發生;強迫是利用現有的有限資源,對已經發生的腐敗行為(經常是已經存在較長時間了)進行應急性的打擊,可以看作對政權合法性的緊急補救活動;在強迫模型的腐敗治理活動中,由于其注重不計成本的打擊,而不是一勞永逸地解決腐敗問題,其最差的情況是反腐敗機構過度卷入腐敗活動而完全失去作用,最好的情況也是只能把腐敗活動控制在合法性完全喪失的臨界值上,無法真正解決腐敗問題。
(二)腐敗治理中的“清理”:強迫執行的表現形式
如果對腐敗治理的文獻稍作了解的話,就會發現“Cleanup”(清理)一詞會經常出現,這里該詞帶有很強的“有機體論”性質的隱喻①,即把腐敗作為政治有機體所罹患的一種病癥來看待(如癌癥)。Gillespie和Okrunhlik比較了從1970年到1986年間2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腐敗清理行動,根據清理發生的不同情境,把這些清理現象分為以下幾種類型:政變后清理(Post-Coup Cleanups)、革命后清理(Post-Revolution Cleanups)、現任者清理(Incumbent Cleanups)、繼任后清理(Postsuccession Cleanups)和選舉后清理(Postelection Cleanups)②。Gillespie和Okrunhlik對清理的定義比較寬泛,即一種由政府宣布的抑制和清除腐敗的運動。
在他們看來,清理有這樣幾個特征:首先,清理在本質上是政治的,因此清理總是發生在某些政治情境變化的情況下,如政變、革命、選舉等。其次,清理是對內部或者外部刺激的一種回應,內部刺激包括國家首腦個人價值取向的變化,來自反對派精英的挑戰,以及由于社會經濟條件變化產生的普遍不滿情緒等,外部刺激可能來自其他國家發出的反對聲音。再次,清理可能用來達到這樣幾個目標:瓦解上任政權的合法性,清除異己分子,或者抑制腐敗以提高現存政權的合法性。李輝則結合中國的案例提出,腐敗清理也有可能產生于政權面臨某些急速的經濟社會情境的轉變(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所帶來的全新的腐敗問題,是在缺乏足夠的治理知識、資源、手段,以及專業化的機構與人員的條件下,所采取的權宜之計③。
二、腐敗治理中的制度設計:定義與理論
(一)定義制度設計
筆者認為,制度設計無法從靜態的視角來理解,而必須從制度的變遷和發展角度來理解。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在本文中把制度設計定義為:某些個人或集團有意識地改變制度安排,以達到對某種制度后果的預期。
從這個角度出發,制度設計可以看作制度變遷和形成模式中的一種。按照羅伯特·古丁(Robert E.Goodin)的說法,制度的變遷有三種基本模式:突發事件(accident)、演化(evolution)以及有意識地安排(intention)④。突發事件是指對于某個社會來說發生概率較小的意外事件,比如自然災害、大規模傳播的瘟疫以及一些沒有很強跡象產生的戰爭帶來的外部沖擊(external shocks)等,如中國在清朝末年遭到西方軍事勢力的突然襲擊,賦予了整個中國社會改變制度的巨大動力。
而演化是借鑒生物學的概念,比如在同一片地理區域內存在不同的幾種制度形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就是古希臘時期的城邦社會,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古希臘大大小小幾百個城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政體制度:君主制、僭主制、貴族制、寡頭制、民主制、暴民制等,這些政體之間會像生物一樣進行競爭,并且符合適者生存的基本法則,一些更為適應社會的制度就會生存下來,其余的將會轉變或者被淘汰。關于演化制度變遷理論,唐世平設計出一個更為綜合的社會進化的制度變遷理論模型:變異—選擇—遺傳模型⑤。
當然,制度也可以被人為地有意識地設計而加以改變。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美國建國的歷程,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開篇的一段話就是:“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⑥漢密爾頓這句話就包含了三種制度變遷的模式,機遇與前面提到的突發事件模式大體相當,而強力在某種程度上指的是演化模式,因為漢密爾頓這里“強力”的意思顯然是國家之間通過戰爭和其他競爭方式來淘汰不適應社會的制度模式,而漢密爾頓聯邦主義者這里“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的意思,就是通過人為地有意識地安排來改變制度,這其實表達的就是“制度設計”的觀念。
(二)制度設計背后的邏輯
既然制度的形成和變遷有著這么多基本的模式,那么為什么最后一種模式會在今天大行其道呢?筆者認為,強調制度設計重要性的觀點和理論,其實在背后有一些沒有被明確表達出來的理念和邏輯,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制度設計中的“制度”。在大多數制度設計主義者所強調的制度中,指的不是國家整體性的基礎制度,如民主/威權、計劃/市場、單一/聯邦等,這些制度的變遷模式非常復雜,常常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這些制度與腐敗之間沒有被證明有何種明確的關系,因此在他們的解決方案中,所謂制度設計中的“制度”,主要指的是與腐敗直接相關的制度,包括相對獨立的反腐敗機構的設立、反腐敗相關法律的出臺和有效實施、財產公開和財產申報制度等。這些局部性的和工具性的制度不會過度刺激決策者的神經,可以較為容易地得到推行。我們把這種局部性的、相對外圍的,但是又看起來與治理腐敗直接相關的制度稱為“次級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
制度設計強調的是制度變遷和形成中的設計者的主觀意愿。在目前制度主義研究領域中,理性選擇范式與組織社會學范式占據了絕對的主流地位,雖然二者在解釋制度形成問題上的邏輯大相徑庭,甚至是完全對立的,因為前者強調簡單的理性人假設支配了制度的形成,后者則強調文化與社會規范以及組織間的互動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但是總的來說它們都認為制度是一個游戲規則,制度過程就是人與制度之間的博弈過程。這種理解制度的方法,從根本上來說忽略了制度設計者的政治觀念(Ideas)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義者很少研究制度設計,而更多的是研究制度過程。
三、強迫執行與制度設計:基于腐敗治理的類型學劃分
在腐敗的治理模式中,與制度設計相對的治理模式是什么呢?曼寧認為是“強迫執行”(Enforcement),但是其并沒有更進一步地闡釋強迫執行這種治理模式背后的理論邏輯,以及這種二分法背后所暗示的含義。于是,在強迫執行與制度設計這兩種腐敗治理的理想類型下,筆者更進一步地從治理效果、治理范圍、治理時期、治理方式、行動邏輯假設和對腐敗的判斷上進行了劃分(見表1),希望可以將其進一步理論化。
語言的學習在最開始的階段,經常會通過歌謠的形式來讓學生更好地掌握語言。在我們小時候學習漢語時,也接觸到了很多的歌謠,這些歌謠朗朗上口,讓我們熟記于心,不知不覺就掌握了很多語言的語法內容。在英語的學習中也是如此,英語國家也有很多的歌謠,教師可以將這些歌謠融合到課堂教學中來。同時,為了更好地學習語法,教師也可以自己創編歌謠,通過一些韻律感強的歌,讓學生掌握語法的知識,起到更強的學習效果。所以,教師在平時要善于收集整理,將英語國家非常流行的一些英文歌謠,納入到自己的課程體系中來,并且對學生進行科學的講解,讓他們掌握這些歌謠的內涵,同時讓他們在課下的時間記憶和背誦,這樣就可以很好的提升教學的效果。

表1 兩種腐敗治理模式對照表
1.治理效果:治標與治本。從治理效果上來看,制度設計被認為是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的,而強迫執行則只能治理腐敗的表層現象。腐敗問題的發生,從理論上來說,被認為是有許多根本性原因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設計上的漏洞。按照理性選擇理論的假設,人都有在制度安排的游戲規則下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取向,那么當一個制度被行動者發現了其中可以被加以利用的漏洞,這個漏洞就很有可能會被用來謀取私利,這便是腐敗,并且被認為是腐敗的根源。那么要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很顯然,僅僅針對謀取私利的行動進行治理是不夠的,而是要從制度設計上堵塞漏洞。
2.治理范圍:局部性治理與整體性治理。在治理范圍上,強迫執行的方式只能針對具體的問題,如“小金庫”問題、公路亂收費問題、醫藥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土地使用權出讓腐敗問題、“豆腐渣”工程問題等。不可否認,強迫執行在一定范圍內也是可以起到打擊腐敗的作用的,但是要動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且要求強迫執行的部門內部不能有腐敗問題,因此其治理范圍只能是局部性的。但是制度設計的策略,強調的是把這些不同的腐敗問題看成是一個系統化的整體,針對這個整體從制度上加以改變,通過改變制度來改變人的行為選擇,從而達到治理腐敗的目的。
3.治理時限:短期治理與長期治理。在治理所持續的時間上,強迫執行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反映了一個政權面臨極為緊迫的腐敗問題,但又沒有足夠的治理資源來解決它,就需要動用其他方面的資源來集中力量加以解決,因此其只能持續有限的一段時間,如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嚴打”。而制度設計則是通過出臺制度的方式,將解決問題的辦法長期固定下來。同時,在上面對于制度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發現,制度一旦形成,會反過來塑造人的行為,也即將社會互動的模式結構化。腐敗如果是一種社會互動的模式的話,那么同樣,清廉也可以是一種社會互動的模式,至于哪種模式被塑造出來,主要看制度設計是否合理。
4.治理方式:運動式與常規化。強迫執行由于強調的是短時間快速解決問題,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運動式”(campaign style)的性質。這種運動式的治理方式,就類似于和腐敗打起了“游擊戰”,只能起到讓腐敗感覺到“疲勞”的效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它。與其相對的則是“常規化”治理,即和腐敗打“陣地戰”,建立完善的治理機構,設計合理的治理制度,把治理的程序和手段長期固定下來,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打擊腐敗。
5.行動邏輯的假設:私欲與理性選擇。采取強迫執行方式的治理策略,其背后對于腐敗者行為邏輯的假設是,這是由于腐敗者個人的道德問題造成的,是由于個人的私欲過度膨脹,因此在這種假設的背后,暗含的意思是,腐敗并不是一個結構化和制度化的問題,而是某些個人化的道德水準問題,只要加大打擊力度就可以得到改善。而制度設計的邏輯則是,腐敗可能是腐敗者在既定制度規則與社會環境(social settings)下的理性選擇,和個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沒有太強的相關性,因此如果要加以改變,首先要改變的不是個人,而是規則。
6.對腐敗問題的判斷:非嵌入性與嵌入性。在腐敗研究領域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們對腐敗的認識又更進了一步,不再把腐敗歸為簡單的不道德的違法行為,或者非正常的行為,而是開始用更加價值中立的眼光來看待腐敗問題。研究腐敗的范式也開始從道德論與功能論向嵌入論轉變⑦,約翰斯頓提出了“嵌入性腐敗”(entrenched corruption)的概念:“腐敗是根植于、嵌入于社會環境之中的,這種社會環境既是腐敗的結果又有助于維持這種腐敗。”⑧筆者認為,嵌入性的腐敗與非嵌入性的腐敗區別在于,腐敗所形成和賴以生存的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之間是否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共生關系,如果形成了這種共生關系,那么就是嵌入性腐敗,反之則是非嵌入性的。嵌入性的腐敗通過強迫執行的手段是無法有效治理的,因為強迫執行治理策略,既無法改變正式制度,更不用說改變非正式制度了。只有通過制度設計的方式,改變正式制度,同時改變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關系,才有可能解決腐敗問題。
因此強迫執行類型體現了決策者或者出于治理知識和技能的匱乏,或者出于對治理后果的忌憚,又抑或自身也卷入其中,而實行的一種短期效果取向的半心半意的反腐敗手段。而制度設計的治理類型則充分體現了制度設計者試圖長期抑制或者根除腐敗的意志和決心,雖然其可能依然受到治理知識和技能匱乏的困擾,但這一缺陷可以在今后長期的治理實踐中逐漸得到克服和改善,其不太忌憚治理的不良后果,自身也較少地卷入腐敗行為中,從而腐敗有更大的機會得到抑制。
論述到這里似乎本文的觀點已經非常明確了,即從強迫執行向制度設計的轉變,以及向理想類型的制度設計的無限接近是我們今后治理腐敗的正確方向。這里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觀點只具有部分的正確性,筆者認為:無論是強迫執行還是制度設計,都是國家中心主義式的腐敗治理模式。雖然這不是本文論述的核心,但這里依然要指出,國家中心主義式的治理模式有兩大弱點:一是對縱向責任的忽略;二是對公民權和公民身份建設的忽視。克利特加德曾經提出,腐敗等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權減去其責任性,即當政府不再擔心其需要為自身權力的行使而背負責任的時候,最容易發生權力濫用的情況。但是政府的責任性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橫向責任和縱向責任,橫向責任訴諸的是政府部門之間權力相互制約和監督,而縱向責任訴諸的是公民社會對國家的監督和制約。因此,國家中心主義式的治理模式,都在強調國家內部的橫向制約能力,而忽視了社會監督的作用。
注釋:
①Whitehead,Laurence:Democratization:Theory and Exper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Whitehead在書中提到,corruption一詞來自古希臘人生機論者借用來隱喻政治生活的詞語,把corruption作為形容城邦所罹患的一種病癥,后來這一詞語沿用至今。
②Gillespie,Kate&Gwenn Okruhlik(1991):“The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Corruption Cleanup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Controlling Corruption,Edited by Robert Williams and Alan Doig,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0。
③李輝:《當代中國腐敗治理策略中的“清理”行動:以H市紀檢監察機構為個案(1981—2004)》,《公共行政評論》,2010年第2期,第45—70頁。
④Goodin,Robert E.1996.“Institutions and Their Design”,i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esign,Edited by Robert E.Good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2。
⑤ Tang,Shiping.2011.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⑥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⑦參見李輝:《道德論、功能論與嵌入論——西方腐敗研究的范式轉換》,《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年第5期,第85—90頁。
⑧ Johnston,Michael,1998,“WhatCanBeDone about Entrenched Corruption?” ,in Boris Pleskovic(ed),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Economics 1997,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6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