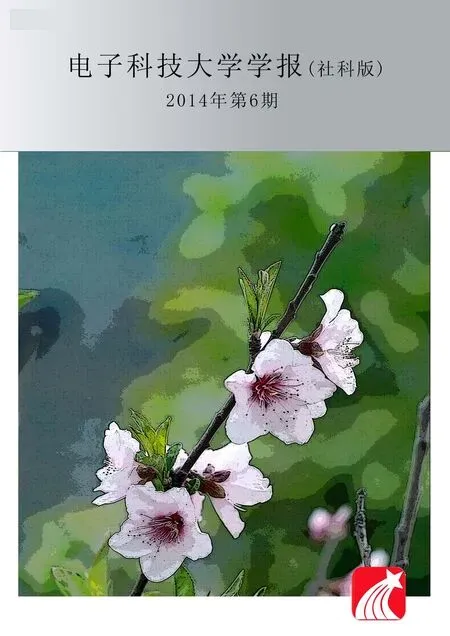論對失獨者“代孕”行為的法律保護
□王 鵬
[清華大學 北京 100084]
引言
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各類突發事件和災害對國家與家庭造成了較大的沖擊,影響了社會穩定。與其他國家相比,風險社會對家庭的影響在我國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主要是因為我國長期的“計劃生育”制度產生了大量獨生子女家庭,這些子女一旦因風險性事件或疾病去世,常常會破壞其家庭乃至整個家族的安定幸福,進而影響社會穩定。據統計,我國每年約產生數十萬個失獨家庭[1],這些家庭的養老和安置等問題業已成為政府和社會亟待解決的議題。
然而遺憾的是,當前對失獨者關注的中心主要是“制度性幫扶”,而對失獨者的“代孕”問題則研究不多。前者固然重要,但制度建設畢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政府的制度性幫扶與經濟狀況和財政收支有密切關聯,所以缺乏穩定性。況且這也無法解決此類家庭長久的精神與心理問題,對當前“以人為本”的社會理念造成了沖擊。與此相比,更好的解決辦法是給予失獨者以更多選擇權,即在從經濟上保障其生活與養老的同時,讓其擁有更寬泛的“生育權”,尤其是對于無法生育的失獨者而言,允許其代孕無疑是最好的出路,“給失獨者留下后代才是最好的慰藉[2]”。但可惜的是,盡管當前學界對代孕已進行了大量有意義的討論,但卻對我國特有的、因計劃生育而導致的大量失獨者的代孕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以“失獨”(或一孩,單核等類似詞匯)和“代孕”為關鍵詞檢索中國知網,僅能得到8個結果;以“代孕”為關鍵詞檢索,并在其檢索結果中以“失獨”等進行全文檢索,也僅能得到16個結果。從內容上看這些研究也基本上是把失獨者作為代孕的眾多研究對象之一對待,其解決方法也基本都是從改革代孕的整體法律制度入手。換句話說,這些研究方法的思路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捆綁式”“出售”代孕權,未能根據代孕人群的特殊性進行分類,對失獨者的特殊法律地位缺乏足夠的關注。
從當前我國規范體系看,失獨者相比其他特殊群體在代孕方面有更強的合法性,能夠更好地得到法律的支持與合法性的證成。而且與上述“捆綁式”的思路相比,首先使對代孕有迫切需求的失獨者的相關活動合法化,不僅能減少這一制度推行的阻力,也能為未來擴大該制度的適用人群提供一定的經驗借鑒。另外從實踐中看,使失獨者代孕行為合法化也有助于維護其合法權益。當前已有大量失獨者進行了“代孕”,但由于相關協議未能得到法律和司法支持,給其帶來了重大財產損失[3]。因此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現實看,失獨者的代孕行為都應合法化,其正當權益應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
一、失獨者的特殊法律地位
如上所訴,在代孕方面,失獨者與其他主體相比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法律地位是法律上“權利和義務的綜合”[4],公民享有的權利是法律地位的表現,據此,可從失獨者在法律上所應享有的權利來探討其法律地位。具體看來,失獨者與代孕有密切聯系的權利主要有再生育權、生存照顧權和繼承權三種。
(一)再生育權
再生育權是失獨者享有的首要權利。以“再生育”全文檢索北大法寶“中央法規”和“地方法規規章”數據庫,能得到六十部中央法律法規和一千余部地方規范性文件,這些規范對失獨者的再生育權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定。總體來看中央法律法規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行政管理角度對失獨者進行適當的照顧,如簡化再生育行政審批手續、為再生育提供資金支持以及進一步明確再生育的條件等;二是從醫療科技角度規定對失獨者進行技術支持,其中較為重要的有:《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7條規定公民有生育的權利,第五章“計劃生育技術服務”規定政府應提高相關技術水平;《人口與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政府應“保障公民獲得適宜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的權利”,《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的通知》第八章序言規定政府應“免費提供再生育技術服務”,該章第二節更是將“再生育技術服務”細化為再生育醫學檢查等技術。地方法規規章則多為與中央規定相對應的具體的執行規范和細化規則。
盡管沒有直接規定“代孕”二字,但這些規范在本質上包含了代孕這一行為,因為:首先從代孕的性質看,盡管其嚴格受制于國家,但根據公民“法無禁止即可行”的行政法基本原理,失獨者有委托他人代孕的權利。盡管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辦法》)第3條和第22條禁止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代孕技術,并規定了處罰措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校驗實施細則》禁止商業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但“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以及商業化等限制性詞匯反而為代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其次從立法目的和語義學角度看,上述法律是為了“優生優育”和科學管理人口,在此行政目標的涵攝下,“計劃生育技術”就不可能僅僅是避孕技術,而應是對出生嬰兒質量有利的人工受精、胚胎移植以及代孕等多項技術之和。總之,國家不能否定公民的再生育權利[5],而代孕是失獨者再生育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法律的內涵與要求。
(二)生存照顧權
根據我國《憲法》第14和第45條,任何公民都有權獲得“生存權或者說是生存照顧權的保護”[6],失獨者作為公民中的弱勢群體,其生存照顧權更是受到了法律的特別關照。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制度、全國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的試點和實施、相應的資金管理辦法、扶助對象具體條件的確認、失獨者醫保社保解決辦法等法律和制度規范均表明了國家對失獨者所履行的生存照顧義務。但相比其他弱勢群體,當前對失獨者的生存照顧義務還遠遠不夠,這不僅體現在物質上的補償條件過高與標準過低等缺陷方面(如《全國獨生子女傷殘死亡者扶助制度試點方案》的相關規定),還體現在失獨者的精神問題無法解決等問題上[7]。“‘失獨’作為重大的家庭生活事件”,“必然導致家庭功能受損”[8],即便是給予其充分的經濟補償,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合適的方式是明確失獨者享有代孕的權利,以重建家庭的基本功能。
(三)繼承權
從失獨者的繼承權來看,在實踐中,由于獨生子女父母往往在其存活時將房產等重要財物登記于其名下,在其離世后,失獨者往往會因離婚及子女配偶再婚等事由而對財產分配產生爭議,雖然對此可根據《民法通則》和《繼承法》等進行司法處理,但由于證據混亂、手續復雜及親情糾纏等原因,極易導致“夫妻反目”、“翁婿反目”等嚴重問題。此外,由于法律未能明確代孕的合法性,使代孕的工具,如胚胎等僅能作為法律上的“物”對待,忽視了其對失獨者的重大意義,導致司法中出現較多不利于失獨者利益、但形式上符合法律規定的判決出現。因此,失獨者的繼承權本身不僅是一項簡單的民事權利,而是被賦予了更多“人”的屬性,只有法律明確允許其為代孕之行為,才能從根本上定紛止爭。
我國規范體系所承認的失獨者上述權利的獨特內涵,決定了其特殊的法律地位,也使其代孕活動能為法律所保護。但由于法律法規畢竟沒有基于這些權利直接規定失獨者的代孕權,因此其權利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伸張。吊詭的是,同樣是“再生育技術”,與“代孕”有較多交叉的“人工授精”受到了《關于開展供精人工授精技術實施情況調查的通知》等部門規章和《關于夫妻離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確定的復函》等司法解釋的較為全面系統的保護,而代孕行為卻不為法律所提倡。這樣的規范體系還意味著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公民如果通過人工授精的方式代孕,其人工授精的過程和子女受到規范的保護,而代孕過程卻缺少立法和司法支持,這顯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
因此,無論是從法理還是從權利角度看,失獨者相比其他需要代孕的群體,有更強的合法性和緊迫性。對其代孕權的立法保護不僅有助于完善當前法律體系,填補規范的漏洞,而且有助于維護失獨者的基本權利。從實踐看,目前實現其該權利的主要阻力在于立法和司法方面[9]:立法上的規定較為模糊,缺乏可執行性,且《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等規范從反面“暗示”了代孕的“非法性”,地方規范性文件也因無上位法授權而無權保護代孕行為;司法上由于缺少相關司法解釋和成熟的做法,實踐中做出的判決常常引起當事人的激烈反對。為此,下文將著重探討破解這些困難的可行路徑。
二、立法的改進
由于規范體系的漏洞,使行政和司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往往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其無論作出何種行政或司法決定,都會引起較大爭議。因此首先需要從規范層面進行完善,以建立較為系統和可執行性強的規則體系,為后續的執法活動提供指引。
(一)明確法律內涵
首先應明確《婦女權益保障法》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相關規定的具體內涵。由于失獨者享有代孕權是再生育權的要求,而再生育權作為基本人權,應首先由法律對其進行保護。《憲法》第25和第49條明確規定了計劃生育制度,同時第37與第38條規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體現了對生育權(包括再生育權)保護和限制兩方面的含義。為此,我國制定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9、第38和第51條對婦女的生育權進行了保護,《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則主要是對其進行了限制。但遍觀兩法內容,其對何為生育權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解答,這種籠統的規定僅是“對國際社會關于生育權認識的尊重,但不意味著我國在立法上將生育權賦予任何有生育能力的公民。”[10]為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可通過立法解釋,對失獨者生育權的范圍做出更為清晰的說明,并且對實現該權利的技術手段做列舉性規定,明確代孕可作為失獨者實現其生育權的合法技術手段。這樣既能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又能滿足失獨者由于年齡增長、生殖能力喪失而對代孕的急迫需求。
(二)完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
在法律作出明確規定的前提下,代孕作為涉及到委托和親子關系等多重法律利益的行為[11],尚需中央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配合,對此可從規范的主體和內容兩方面展開。
在規范主體方面,國務院與其下屬行政部門應合理分配各自權限。當前我國規范代孕行為的主體主要是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衛計委),通過《辦法》等部門規章對相關行為進行管制。這造成了兩個問題:一方面,部門規章的層級較低,與法律銜接的權威性不夠;另一方面,難以有效處罰違法的代孕行為。因為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44條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77條,對違法代孕的處罰僅為責令停業、沒收非法所得及罰款等,威懾力度較小,而根據《行政處罰法》第9條和第12條,部門規章僅能在行政法規給予行政處罰的范圍內進行規定,這也就意味著衛計委難以有效管理代孕行為。因此在規制代孕過程中,必須重視國務院的作用,通過制定行政法規對失獨者代孕行為的指導原則、行政處罰范圍和監督等問題進行規定。
在規范內容方面,除應加強行政處罰力度外,還應規定具體的代孕審批辦法,并“明確規定禁止有償代孕[12]”。在代孕審批方面,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應就六個方面作出規定:失獨者的認定標準;代孕實施機構必須為符合相關技術標準的專門性醫院;代孕和醫療人員的資質;管理、監督和指導機關;違法代孕的法律責任;代孕糾紛的解決機制。此外,由于商業性代孕會產生難以解決的倫理問題和法律糾紛,故應明確禁止商業性代孕和有償代孕,取締相關代孕中介,以盡量減少失獨者在代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的倫理和法律阻力。
(三)革新地方規范性文件
在上述規范的基礎上,地方政府也應出臺對應的執行措施。上述規范由于其較高的層級,決定了不可能對失獨者代孕這一復雜的法律關系和行為作出過于詳細的規定,因此給地方政府預留了較大的立法空間。為此地方政府應出臺具體的執行標準和細則,并應進行法規清理,及時廢止之前出臺的大量禁止性規定。此外,地方政府還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根據當地經濟狀況,自行規定財政補貼等優惠措施,對確有困難但又有代孕意愿的失獨者進行經濟幫扶。
總之,應建立“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地方規范性文件”三級的立法保護,從而使失獨者代孕權系統地納入法律的范圍內。另外,由于失獨者僅是需要代孕群體的一部分,因此前兩個層級的立法僅需以法律解釋或更正個別條文的方式進行修改即可,以盡量保持法律的完整性。
三、司法的支持
在司法方面,實踐中當事人的爭議主要圍繞代孕合同的有效性展開,法官往往認為這類合同將代孕人與嬰兒作為“物”對待,據此依照《民法通則》第7條與《合同法》第7條,判決合同因違反“公序良俗”和社會公德而無效[13]。
然而,在失獨者語境中,代孕合同能夠通過公序良俗原則的檢驗,得到合法性的證成。有學者在總結德、法、日等國司法實踐后指出,公序良俗原則有危害家庭關系、違反人格尊嚴、違反性道德及暴利行為等十種內涵[14],當前學界和實踐中常將前兩者作為代孕合同無效的主要理由,然而從失獨者的特殊法定權利來看,其訂立的代孕合同沒有危害這兩者。就家庭關系來看,正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創造了“失獨者”這一特殊群體,預設了家庭關系破壞的可能性,失獨者履行了法律義務。但義務是與權利對應的,該法第1條還規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促進家庭幸福”,對失獨者來說,其代孕行為以及作為其手段的代孕合同都是恢復家庭關系的重要努力,理應得到國家的尊重,以實現權利和義務的對等。就人格尊嚴來看,實踐中的主要擔憂是代孕合同將代孕人和嬰兒作為“物”對待。但實際并非如此:從嬰兒看,失獨者代孕是其法律上再生育權和繼承權的體現,盡管嬰兒不是失獨者所生,但失獨者在法律上與嬰兒存在親權,這與收養關系是類似的;從代孕人看,由于法律禁止有償代孕行為,因此只要失獨者給予其的物質利益不明顯超過代孕所需的必要限度,則代孕人就可被看作是失獨者實現其再生育權的義務履行者,作為失獨者權利的相對方而存在。由此可見,在代孕合同非有償合同,且約定失獨者為胎兒父母的前提下,代孕合同是符合公序良俗原則的。
因此,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應肯定失獨者訂立代孕合同的效力,并進一步依照《合同法》和相關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對代孕合同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包括:合同委托方是否為失獨者;合同是否為有償合同、有無明示代孕者為子女父母、合同是否為要式合同,即以書面方式訂立的合同[15];合同履行方的資質;履行的方式是否恰當或有瑕疵等。此外,最高院也可以批復、專門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的方式,明確該類合同的審查標準,以為下級法院的判決提供指導和幫助。
[1]王小平.失獨者的精神撫慰與制度保障[N].光明日報,2013-10-6(06).
[2]楊國棟.給失獨者留下后代才是最好的慰藉[EB/OL].(2014-8-18).http://hlj.rednet.cn/c/2014/05/19/3352945.htm.
[3]失獨老人起訴爭奪冷凍胚胎 法院判決不能繼承[EB/OL].(2014-8-18).http://china.cnr.cn/yxw/201405/ t20140520_515554864.shtml.
[4]青井和夫.社會學原理[M].劉振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65.
[5]張榮芳.論生育權[J].福州大學學報,2001(4):36-38.
[6]劉麗.稅權的憲法控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
[7]宋強玲.失獨者養老問題及對策研究[J].人民論壇,2013(5):126-127.
[8]楊宏偉,汪聞濤.失獨者的缺失與重構[J].重慶社會科學,2012(11):21-26.
[9]任巍,王倩.我國代孕的合法化及其邊界研究[J].河北法學,2014(2):191-199.
[10]楊遂全.婚姻家庭法新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34-135.
[11]任汝平,唐華琳.“代孕”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7):161-165.
[12]王貴松.中國代孕規制的模式選擇[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4):118-127.
[13]吳亞東,楊長平.“代孕合同”有違公序良俗被判無效[N].法制日報,2012-11-1(08).
[14]梁慧星.市場經濟與公序良俗原則[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6):21-31.
[15]曹新明.現代生殖技術的民法學思考[J].法商研究,2003(4):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