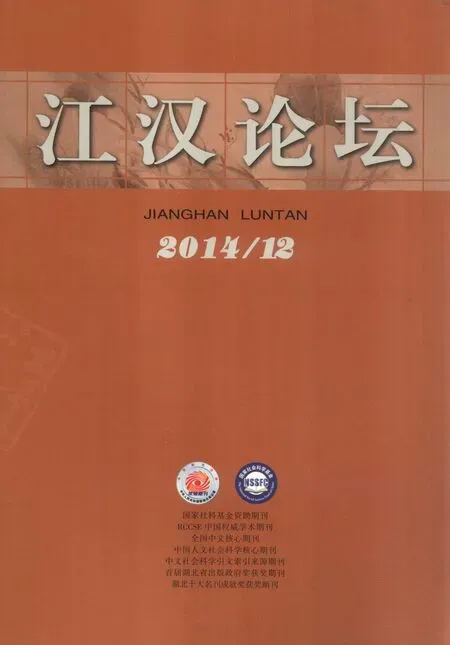信任視角下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行為選擇
張 明
一、問題的提出
1.留守兒童社會支持研究
有關社會支持的研究,國外最先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的精神病學,國內始于20世紀80年代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研究。就留守兒童而言,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進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范圍涉及不同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及利用,社會支持對留守兒童心理、行為及適應性的影響,社會支持模式及社會支持網絡 (體系)的構建,等等。
按不同標準,社會支持可分為正式支持與非正式支持,工具支持、情感支持與交往支持等。①學界普遍認為留守兒童在生活、學習、安全等諸多方面處于弱勢地位,易于產生心理及行為問題,并且這些問題僅靠家庭或學校的單方力量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因此,作為個體逆境中的保護性因子,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與完善顯得尤為必要。良好的社會支持不僅能緩解留守兒童抑郁、孤獨等情緒反應,提升幸福感、快樂感與心理彈性,從而保護其身心健康,還可減少問題行為的產生,促進兒童采取積極的方式解決問題。
然而,留守兒童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發揮不均衡,存在社會支持資源多元與效用有限,先賦性因素占主導而后生性支持系統薄弱等問題。因此,如何充分發揮留守兒童社會支持網絡的效用,成為人們亟需考慮的問題。部分學者研究發現,留守兒童既是社會支持的對象,又是社會支持網絡的參與者,其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存在性別、年齡、心理彈性等個體差異②,而這種主動參與意識和行為同時也影響著社會支持網絡功能的發揮。這是因為,“社會支持源的存在僅是一種潛在的支持,而積極求助行為不僅可以使潛在的幫助變成現實的社會支持,而且對幫助的滿意程度還將影響他們以后的求助行為”③。這為完善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提供了新思路,但相關研究只是對該現象進行了總體描述,未深入探討留守兒童決定是否求助以及選擇不同支持源的依據或原因。
2.信任概念的引入
社會支持不僅是一種源自外界的幫助和扶持,也涉及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互動關系④。既然是一種互動關系,那么,從雙方的信任關系著手探討不同信任程度下留守兒童的行為選擇,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其在社會支持體系中的自主性。
關于信任的內涵,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給予了不同的解釋。它既是一種對他人和社會的預期⑤和對他人未來可能行動的賭注⑥,也是降低環境與社會系統復雜性的簡化機制⑦和有助于社會經濟繁榮與發展的社會資本⑧。在本文中,留守兒童的信任被界定為對社會他人行為的一種社會期望與心理預判,有助于兒童適應復雜的社會環境與消除人際互動中的不確定性,留守兒童也將據此決定在什么情況下尋求社會支持以及向誰求助。
除特殊說明外,本文所用數據源于筆者2013年參加的湖北省農村留守兒童調研。該調研的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從農村流動到其他地區務工,自己留在戶籍所在地的農村地區,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6—18歲以下兒童。調研采取問卷調查與個案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共回收有效問卷1196份。
二、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二元分類法下留守兒童的行為選擇
盧曼從結構功能主義視角出發,將信任分為以互動中建立的情感聯系為基礎的人際信任和以規范制度、法律法規為基礎的系統信任。⑨巴伯爾將信任分為 “對人的一般性信任,勝任人際關系及社會制度角色的技能信任,及對被托付的責任及義務之徹底承擔的信任”,并提出了 “合理的不信任”這一概念。⑩在這些研究中,對中國社會的信任研究影響最廣的是 “特殊信任”與 “普遍信任”的提出。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最先用 “特殊主義”、“普遍主義”區分社會關系,并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是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韋伯將信任分為以血緣性社區為基礎的特殊信任與以信仰共同體為基礎的普遍信任,提出中國人的信任是以私人關系、家族和準家族關系為基礎的特殊信任,并且很難被普遍化。福山則著眼于經濟繁榮與信任文化的關系,以信任是否超越血親關系為標準將社會分為高信任社會與低信任社會,中國社會被其列入后者。這三位學者都從中西方比較的角度探討了中國社會的信任問題,且都將中國社會歸入低信任度的一類。
國內部分學者結合費孝通 “差序格局”的概念,認同中國鄉村關系結構具有特殊主義傾向,并承認 “差序格局”在其中的影響作用。如林聚任認為,村民認同自己對親屬有幫助義務、責任,而對于他人表現出一定的排外傾向;在社會交往中,行為因是否存在信任關系而不同。鄭也夫提出傳統中國人的信任是依靠血緣共同體的家族優勢和宗族優勢而形成、維持的特殊信任,對他人表現為普遍不信任。通過人際信任量表 (ITS)對留守兒童的有關實證調查表明,該群體人際信任表現出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的差異,并且其普遍信任低于特殊信任。
1.特殊信任下留守兒童的“類別化”求助行為選擇
留守兒童的特殊信任在社會支持行為選擇上表現為 “類別化”求助行為傾向,這既是外部環境影響的結果,也與個人選擇有關。一方面,傳統鄉村社會以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為基礎,為留守兒童在實際生活中構建起 “差序格局”式的社會照顧網絡。具體而言,留守兒童與有血緣關系的家庭成員間表現為以義務、感情為基礎的天然信任關系:親友感到對留守兒童有照顧義務,兒童認為親友是自己值得信任的求助對象。鄉鄰則是這一照顧網絡的重要補充:在鄉規民約的約束下,在留守兒童遇到困難時,他們會基于 “道義”給予幫助和照顧。這是一種留守兒童與鄉鄰之間彼此家庭基于地緣關系而形成的相對穩定、長期的 “還—報”式人際關系行為模式。對于幫助者而言,這不過是 “在已經建立個別關系的兩個個人或兩個家庭之間,一本由來已久的社會收支上加上一筆”,留守兒童也從過去的經驗中感受到,鄉鄰是能為其提供幫助的對象。 “遠親不如近鄰”、 “守望相助”等俗語以及現在和諧社區建設中對 “人際關系融洽”的提倡都是這種地緣性社會互助行為的體現與發展。
另一方面,留守兒童在日常交往中傾向于與家庭背景相近 (即同為留守家庭)的同學建立朋友關系,并向其尋求幫助。祖克爾分析了三種信任產生機制,即由聲譽產生信任,由社會相似性產生信任,由法制、社會規章制度產生信任。留守兒童小群體的形成即是其基于社會相似性產生的特殊信任及其行為表現。他們在生活中更愿意向群體內成員吐露心聲,征求意見。在留守兒童調查中,47.6%的被調查對象表示愿意與朋友說心里話,其次是父母 (40.3%)。同時,對社會支持源的心理距離排序發現,雖然朋友是留守兒童首選的交談對象,但在親密程度上,父母與臨時監護人被排在第一、二位,其后才是同學。
這種 “類別化”求助行為的結果是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網絡以血親為主,輔以同輩群體。當遇到問題時,他們更愿意首先尋求親人的幫助;在父母缺位的情況下,同輩群體是其主要的求助對象。同時,三類支持源各有分工:臨時監護人主要承擔日常照顧及部分情感支持職責,外出父母為孩子提供經濟支持,同輩群體主要為情感交流和困難協商者。
2.普遍信任下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及其行為選擇
當今鄉村關系雖然依舊帶有 “差序格局”的特點,但和過去相比已有所不同:情感、義務、守信等鄉村 “道義”面臨個人利益的考驗, “利益成為差序格局中影響人際關系親疏的重要因素”;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移造成的社會網絡斷裂削弱了社區照顧網絡的力量,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形成的空心村問題更是使傳統鄉村資源不斷萎縮;部分家庭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動搖了基于地緣關系的人際關系互助模式。留守兒童 “類別化”的求助行為已不能完全滿足其需要。另一方面,社會公眾對留守兒童的關注日益加大,并為改善其生活作出了積極努力。社會組織特別是NGO的介入和發展成為增強農村社區支持功能的有效力量。通過發動志愿者力量開展的社會項目能夠有效實現留守兒童生活質量改善、素質拓展、心理咨詢與危機介入,從而提升整個社區對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能力。留守兒童社會支持網絡的總體變化趨勢表現為從以家族為主的社區照顧網絡逐漸轉變為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的社會支持體系。
上述外部環境的變化使留守兒童的行為選擇更多地帶有了普遍信任的色彩。留守兒童社會支持源多元化,老師、社工、志愿者成為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后農村社會支持網絡力量的重要補充。調研顯示,在師生雙方信任程度高的情況下,老師排在同學之前,留守兒童更愿意主動求助老師,特別是在寄宿制學校的低年級階段,老師成為留守兒童重要的父母替代角色,發揮了父母情感支持的替代功能。馬良對溫州市義務教育階段留守兒童的實證研究同樣表明,留守兒童對社工、志愿者等現代社會支持網絡表現出開放和接納的心態:14.9%的留守兒童 “積極參加”假期內社區 (村)組織的各類公益性活動; “想參加但不知道”的占48.4%,兩者合計達63.3%。同時,留守兒童在遇到困難時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社會信任 “差序格局”: “110”公信力最強,其次是老師、鄰居和親戚、留守兒童自己、同輩群體,父母與社區干部被排在最后 (見表1)。這與通常認知的留守兒童 “類別化”的求助行為相比已有所變化。在該求助模式中,警察、老師這些無血緣關系的一般社會成員成為其遇到困難時的首選求助對象。
表1 留守兒童遇到困難時的行為選擇

表1 留守兒童遇到困難時的行為選擇
行為選擇 百分比“110”報警 29.9向老師求助 13.9向鄰居、親戚求助 13.7自己想辦法解決 13.5請同學、朋友幫忙 12.1打電話向父母求助 8.9向社區干部求助 8.0
三、特殊化、普遍化或情景化:留守兒童的信任類型與行為模式
1.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二元分類法的局限
將留守兒童信任類別分為普遍信任與特殊信任并以此探討其社會支持行為選擇,也許是最符合其所處鄉村文化環境的分類方法,也與留守兒童社會支持體系中先賦性因素占主導的特點相符,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具體情景下,留守兒童同樣對老師、社會愛心人士等所謂的 “外人”持信任態度,并將其作為求助對象之一。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似乎并非如韋伯、福山等人所說的是一個低信任社會。英格哈特1990年、1996年開展的 “世界價值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超過50%的中國人相信大多數人值得信任,中國屬于高信任度的人際信任社會。留守兒童社會支持源選擇的多樣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普遍信任與特殊信任同時存在于留守兒童身上,并影響了其行為選擇。我們怎么看待這一現象呢?
楊音宜在研究中國社會關系分類時,提出了“自己人∕外人”分類法,認為 “自己人”與 “外人”的邊界并不是僵硬的,而是具有伸縮性與通透性特點,即兩者依據不同情景可相互轉化,且作為這種親疏關系中心點的 “我們”概念具有 “情境化”屬性。翟學偉則在討論中國社會關系是特殊主義還是普遍主義時注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對國人思維的影響,提出了 “連續統”概念,即 “在兩極間存在一種過渡性,這種過渡使兩極間的差異和對立變得模糊,凸現了彼此間相通、相容的可能”,“國人試圖尋求兩事物間融合、轉化的可能, ‘差異’不是對立而是各有側重”。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對于多數國人來說,特殊信任或普遍信任、“自己人”或 “外人”間不是非此即彼的絕對對立,而是存在相互融合、共生一體的可能,以何為重取決于所處的情景。這是特殊信任行為與普遍信任行為不僅能共存于留守兒童身上,而且還能相互轉化的文化原因,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該二分法在分析留守兒童社會支持行為選擇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具體而言,依據特殊主義—普遍主義二分法,留守兒童與求助對象之間的關系可分為以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等無選擇性的先賦性因素為基礎的信任關系和以具有可選擇性的后生性因素為基礎的信任關系。前者涉及的社會支持主體包括父母、臨時監護人、親屬、鄉鄰,后者涉及的社會支持主體包括朋友、老師、社會志愿者、愛心人士、社區工作人員等,留守兒童與其關系的建立、發展或中斷可依據個人意愿自由選擇。綜觀留守兒童對社會支持源的行為選擇,其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行為之間并不是完全對立與中斷的,而是存在過渡轉化的可能性與中間地帶;在不同社會情景下,他們對同一支持源也可能采取求助或不求助兩種行為選擇。二分對立的劃分方法相對簡單,難以說明留守兒童在社會支持體系中的自主性。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此基礎上增添新維度對其信任行為模式進行細分與探討。
2.情景化:四元分類法下留守兒童的求助行為
黃光國依據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將人際關系分為情感性關系、混合性關系和工具性關系。楊中芳、彭泗清提出以義務為基礎的人際信任模式,依據人際關系中的既定成分、工具成分、感情成分將其分為三類。列維斯和維加爾特用認知—理性與感情—非理性兩個維度來分類討論各種不同信任類型,探討社會關系中的理性因素與情感因素對信任類型的影響。麥克阿利斯特將人際信任區分為認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綜上所述,在信任分類的維度選擇上,學者們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人際關系中情感因素與理性因素對信任關系和行為的影響。這同樣體現在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行為選擇傾向上。在留守兒童多種社會支持主體中,臨時監護人主要承擔日常照顧及情感支持職責,外出父母為孩子提供經濟支持,同輩群體、老師、社會愛心人士為其提供部分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兒童在選擇向誰求助問題上視具體情景而定,同時受情感與理性兩種因素的影響。
因此,在留守兒童信任分類的維度選擇上,除先賦性—后生性關系性質這一因素外,筆者試著引入情感—理智這一維度,即考慮留守兒童與社會支持主體互動時是否存在情感介入,并從留守兒童觀察視角出發,分析其眼中的不同信任類別及行為模式。在同等關系性質的前提下,情感介入下的留守兒童主要考慮的是雙方心理距離遠近、親密程度與熟悉度;在互動過程以理性思考為主的情況下,影響留守兒童求助行為的主要因素是求助的可得性、成功率、難易程度、獲助程度與效果等理性因素。其信任類別因不同信任程度可細化為四大類:天然信任、 “自己人”信任、鄉村道義信任、權威信任。 (見圖1)

圖1 留守兒童的信任類別
在天然信任模式下,留守兒童與助人方之間為以血緣關系、擬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先賦性關系,且雙方交往帶有強烈的情感性。最典型的求助對象為父母、臨時監護人、直系親屬。在留守兒童看來,自己與他們之間是一種天然情感聯結所形成的信任關系,從而也不需要任何事實來證明其可靠性與可依賴性。兒童通過家庭 (家族)內部支持體系的運轉來實現自身需求的滿足,彼此間行為互動以需求滿足為目的。這種需求滿足包括物質照顧、精神寄托等不同方面。盡管一些研究表明,由于家長缺位導致的父母榜樣作用削弱、親子關系疏離等家庭社會化問題減弱了留守兒童家庭的社會支持功能,其家庭支持存在情感支持空缺、學習輔導乏力、教育模式有待優化等不足,但對于許多留守兒童而言,血緣關系所帶來的情感聯結依然在他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父母、兄弟姐妹、爺爺奶奶等是最值得他們信任的人,與其心理距離最近。留守兒童向其求助無須考慮行為的社會風險與成本,是基于情感、義務的家庭成員之間的自助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特殊信任下的行為方式類似,但不同點在于留守兒童不向其求助卻帶有情感、理性雙重成分的考慮。在調研中,留守兒童表現出自強獨立、懂事的一面,如希望學習好,給父母爭光 (85.6%),希望父母在外平安、健康 (88.2%)。他們在電話聯系中報喜不報憂或問題簡單化的行為,一方面是怕父母擔心,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現實的考慮,即父母的空間缺位使他們愛莫能助,并不能及時給予幫助。
與此相對的權威信任則以后生性關系和理智介入為主。留守兒童與求助方之間關系的建立、中斷與發展具有自我選擇性,雙方行為遵循理性和社會法規所規范的角色權利、義務準則;影響留守兒童是否向其求助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兒童針對具體情景的理性思考,即中國人常說的情、理、法中的世理、國法;其信任具有選擇性和情景性。如在遇到危險時打 “110”報警求助,依據的是對警察這一身份及其社會行為規范的信任,這也是學校、社會法制宣傳教育和安全教育的結果。兒童求助于社區干部也是如此,是對社會服務網絡和社會幫扶系統的信任。遇到學習困難時希望得到老師的幫助,部分原因也是對老師專業知識的信任,是情感、現實兩相權衡下理性思考的結果。留守兒童對這些外部社會支持系統的求助更多是因為信任其身份所代表的法律、法規、政策及專業技術、技能,相信他們能夠解決自己所遇到的問題,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而這些社會支持源為留守兒童提供的主要為認知、物質層面的支持。
相較于前兩種信任模式, “自己人”信任與鄉村道義信任處于中間地帶,具有混合性。 “道義”即道德義理,是約束社會成員行為的一種社會規范。在鄉村道義信任模式下,雙方關系為無選擇性的地緣關系,遵循互惠原則;鄉規民約與人情法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促使求—助行為得以順利完成的主要因素。留守兒童認為對方基于鄉情和兩個家庭 (家族)間的交情,有提供幫助的道德義務,而人情法則保證了求助行為的可得性和成功性。兩個家庭 (家族)間的互惠性行為表現為鄉親出于鄉情認為自己有提供幫助的 “道義”,從而使留守兒童家庭欠下了自己的人情,或償還了自己以前的人情債。在這一報一還的過程中,兩個家族間的多次、重復的互惠性社會交往行為得以延續,彼此交情不斷加深,最終互動中的情感因素成分占主導,雙方通過擬血緣關系的方式使下一輩的求助行為從鄉村道義信任行為模式轉為天然信任行為模式。
“自己人”信任的產生條件與鄉村道義信任相反,互動雙方交往富有情感色彩,彼此關系為具有選擇性的后生性關系。在這種模式下,留守兒童求助的是他們認為值得相信的 “自己人”,包括被納入 “自己人”范疇的同學、老師、社會志愿者、義工等社會愛心人士。該信任模式與權威信任模式的相同之處在于互動雙方之間均為后生性關系,不同點是情感和理性因素哪個在互動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以及是否將對方納入 “自己人”范疇。楊音宜在提出 “情境化”的 “我們”概念及其形成機制、范圍的同時,指出了不同情境下的個體如何將他人轉化為 “自己人”。這種轉化機制同樣適用于留守兒童權威信任與 “自己人”信任行為模式的轉化。在 “關系化”的 “我們”概念中, “自己人”與“外人”的劃分不僅取決于先賦性因素,更需要考慮交往性因素的存在,即助人者通過情感互動拉近與留守兒童的心理距離,從而成為兒童心中的 “自己人”,并形成相應的 “自己人”信任行為模式。盧曼也指出,熟悉度是影響人際互動中信任產生的一個重要條件。在交往過程中,互動雙方從陌生到熟悉,再到產生信任, “以心換心,以情換情”的交往原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老師為例,對留守兒童社會支持源的心理距離排序顯示出老師的位置在留守兒童心中的游移性,是否將老師視為 “自己人”決定了不同的求助心理與行為。從師生間的依戀關系看,孩子年齡越小,越易對老師形成依戀心理,而依戀關系正是信任關系產生的基礎。特別是在寄宿制學校的低年級階段,老師成為留守兒童重要的父母替代角色,兒童愿意主動向老師尋求各種幫助和支持。與此相對的是,一些走讀學校的初三學生及高中學生并未將老師納入 “自己人”范圍,在行為上表現為被動等待老師幫助,并且不愿意與老師談及家庭、父母關系、同學關系等學習問題之外的內容。
“愛心媽媽”、 “代理家長”、 “陽光家園” 等社工服務站的社工與留守兒童的互動與此類似。接觸初期,留守兒童被動接受物質幫助的成分居多,然而隨著交往次數的增多,留守兒童從多次求助經驗中發現對方真心待己,自己的求助行為有用且能取得實效,模式化交往方式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情感色彩,助人者逐漸從 “外人”變成留守兒童心中的“自己人”。可以認為,伴隨互動中情感因素的增加,留守兒童將求助者納入 “自己人”范疇,彼此行為模式從權威信任模式轉化為 “自己人”信任模式。社工、志愿者等在拉近與留守兒童心理距離的同時,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留守兒童提供了技能、交往、輔導等不同層面的需求滿足,而兒童也愿意接受他們的幫助。
四、總結
農村傳統社會照顧網絡的式微和社會組織的發展 (特別是 NGO的介入),使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網絡總體呈現出從以家族為主的社區照顧網絡逐漸轉變為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的社會支持體系。同時,留守兒童在社會支持體系中并非被動接受者,其行為選擇具有自主性。信任是影響留守兒童選擇不同社會支持源的重要因素,不同信任模式下的留守兒童存在社會支持行為選擇差異。
特殊信任—普遍信任的二元劃分法在解釋留守兒童社會支持行為選擇時略顯不足,需要在關系形成基礎是先賦性或后生性因素的基礎上,引入情感—理智維度對其信任模式及其求助行為進行細致劃分與說明。依據不同信任程度,其信任類別可細化為天然信任、 “自己人”信任、鄉村道義信任、權威信任四大類。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行為選擇實際上是不同社會情景下情感與理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互動過程中理性思維占主導的情況下,求助的可得性、成功率、難易程度、獲助程度與效果等理性因素是影響留守兒童求助行為的主要因素;社會支持主體主要為留守兒童提供物質、認知層面的支持。在情感因素為主的求—助關系中,留守兒童主要考慮的是雙方心理距離遠近、親密程度與熟悉度;社會支持主體為留守兒童不僅提供工具性幫助,還提供精神、交往層面的支持,其支持更為全面與豐富,效果也更好。
注釋:
① 馬特·G·M·范德普爾:《個人支持網的概述》,肖鴻譯,《國外社會學》1994年第4期。
② 李志凱:《留守兒童心理彈性與社會支持的關系研究》,《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9年第4期;段玉香:《農村留守兒童社會支持狀況及其與應付方式的關系研究》,《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8年第4期;許松芽:《留守兒童心理彈性與社會支持關系的調查研究》,《集美大學學報》2011年第7期。
③ 劉廣珠:《理工科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關系的研究》,《心理學動態》1996年第1期。
④ 張克云、葉敬忠:《社會支持理論視角下的留守兒童干預措施評價》,《青年探索》2010年第2期。
⑤B.Barber,TheLogicandLimitsofTrust,New 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83,p.9.
⑥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程勝利譯,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3頁。
⑧ 費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3頁。